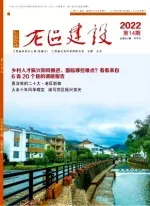基于CSCL的網絡教育模式研究
程艷 岳巍
隨著Internet的迅速發展和全球對終身教育的需求,以異步教育方式為主要特征的網絡教育正成為Internet上的一種重要應用[1]。
網絡教育是利用網絡技術實施遠程教育的一種現代教育形式。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現代教育技術的創新,終身教育觀的興起,令世界各國普遍重視網絡教育體系的構建和網絡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目前,世界各國對網絡教育的發展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據幾年前美國培訓與發展協會(ASTD)的預測,到2010年,雇員人數超過500的公司90%都將采用網絡培訓,在線學習正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正確抉擇。我國教育部于1998年12月24日制定、國務院1999年1月13日批轉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對遠程教育尤其是網絡教育的發展作了宏觀上的規劃,并給予了政策上的支持。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計算機支持的協作學習(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Learning,簡稱CSCL)逐漸成為網絡學習的一種重要形式。學會協作已經成為學習的一種重要策略和方式。計算機支持的協作學習(CSCL)正代表了協作學習與計算機網絡技術相結合的發展趨勢,基于CSCL的網絡教育模式在這種大的教育背景與環境中應運而生。
一、基于CSCL的網絡教育模式
結合網絡教育與網絡教育模式的概念,可以說,基于CSCL的網絡教育模式是在網絡教育活動中全新的教育模式,將基于CSCL的網絡教育模式應用于教育領域,將有利于傳統學與教的行為改變。區別于傳統的教育模式,它是在網絡環境下,以現代教育思想、教育理論和學習理論為指導,主要借助“多媒體”、“網絡”和“通信”三大技術支持,充分利用豐富的網絡教育資源,通過小組或團隊的形式組織學生學習,使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在討論、協作與交流的基礎上對一些共同任務與問題進行協作工作,以獲得最大化的個人與小組學習成果的教育方式。
這種教育模式下,學習者能夠進行合作學習,學習者以小組或團隊的形式組織學習,依靠多媒體、網絡和通信技術的支持,利用多種多樣的網絡教育資源,在協作與交流研討的基礎上對一些共同任務與問題進行協作工作,以獲得最大化的個人與小組學習成果。這種協作不僅體現在小組成員之間,也體現在小組與小組之間。學習者也可以在學習過程中相互支持相互關心,形成密切的協作學習關系,逐步培養學習者的團隊意識和合作精神。
二、CSCL與虛擬學習社區
基于CSCL的網絡教育的重點在于,能夠根據對學習者特征和學習需要的分析,創設一個合適的網絡協作學習環境,在這種情境下,能夠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原動力,在與小組成員交流合作中學到新的知識,逐步納入到自己已有的認知結構當中,將原有知識與新獲取的信息進行加工整理,重新建構。當然,在網絡協作學習情境中的各種學習交流活動都離不開基礎設施的作用— —網絡教育支撐平臺的支持,基于CSCL的網絡教育支撐平臺是支持這種教育模式下教學與學習活動的軟件系統。虛擬學習社區是一個通過信息通訊技術(ICT)在Internet上或者是在局域網內創建的學習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人們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進行平等的交流與合作。它是虛擬社區與學習范式的結合。因此結合CSCL的定義來看,虛擬學習社區是CSCL的一個應用實例。我國學者胡凡剛[2]將虛擬學習社區界定為:基于跨時空的、開放的、自由的網絡虛擬環境,社區成員(主要包括教師和學生)之間進行專題研修、交互協作、資源共享,從而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最終形成的具有共同社區文化心理的、生態式的社會關系共同體。虛擬學習社區首先是虛擬社區。虛擬社區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學習環境,網絡數字化學習與虛擬社區的結合構成的虛擬學習社區,從組織者和功能的不同,我們可以將虛擬學習社區分為兩類:一是正式教育類的學習社區。這類學習社區集中在遠程教育領域,其組織者是各個遠程教育機構、網絡學校和正規學校等。二是非正式教育類的學習社區。這類學習社區沒有明確的組織者和指導者,大多由一些專業網站或由一群專業愛好者建立。如全球linux技術愛好者建立的各種Linux社區。
三、虛擬學習社區的學習理論基礎
虛擬學習社區的發展與學習理論有著密切關系,要想探尋基于網絡環境下的新型合作學習模式,正確理解虛擬學習社區,首先必須了解與之有關的一些學習理論基礎。學習理論是指有關學習的實質、學習的過程、學習的規律以及制約學習的各種條件的理論、探討和解釋。學習理論是心理學中最古老的研究領域之一,也是教育心理學中最重要、最核心和最發達的研究領域。
(一)學習理論的三大流派
虛擬學習社區的發展與學習理論有著密切關系,學習理論的三個主要流派: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和建構主義。
1.行為主義學習理論
行為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觀點有巴甫洛夫的經典條件反射學說、華生的行為主義、桑代克的聯結主義和斯金納的操作性條件反射學說。行為主義心理學主張研究人的外顯行為,反對將意識和內部心理過程作為研究的對象。他們把個體行為歸結為個體適應外部環境的反應系統,即“刺激-反應”(S-R)系統。同樣,行為主義學習理論也是從人的外顯行為探究學習機制,認為學習是由經驗而引起的行為改變,學習過程是“刺激-反應”不斷積累的過程,認為學習與內部心理過程無關,只要控制外部刺激,就能控制和預測學習效果。行為主義學習理論的局限性表現為:反對對學生內部心理活動或認知結構進行了探討,只注重對學生掌握知識的外顯行為的考核,片面地強調外部刺激和外部反應的聯結。在行為主義理論支持下的教學,不考慮學習者的認知規律,教師是知識的傳授者,居于不可動搖的主體地位,其任務是提供外部刺激,向學生灌輸和傳遞知識,學生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因而容易使學生盲目相信書本和教師,顯然,這樣的教學壓抑和束縛了學生創新意識的萌發以及發散思維、逆向思維、批判思維和想象力的發展。
2.認知主義學習理論
由于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存在著不足,到了20世紀60年代,它的統治地位被認知主義心理學派所取代。認知主義學習理論從人的心理活動角度探求人的學習機制,強調人類學習或記憶新信息、新技能時的心理過程,認為人類的學習是經驗的重組,是外部知識及其結構內化為內部心理結構的過程,強調認知結構在學習中的重要性。在認知心理學領域最有影響的兩位學者是奧蘇伯爾和布魯納,他們兩人都重視學習內容結構的重要性,認為只有把知識內容結構好,才能使學習者更好地建構所學知識,但二者對于學習的觀點卻存在著分歧。認知主義支持下的教學為創新思維活動提供了可靠的知識基礎,但在培養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以及充分發展個性方面還存在著不足。
3.建構主義學習理論
建構主義是認知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當今的建構主義是在皮亞杰、維果茨基、布魯納等人思想基礎上的一次綜合與發展。建構主義認為,對于客觀世界的理解和賦予意義是由每個人自己決定的,學習是學習者主動建構內部心理表征的過程。意義建構不僅包括結構性的知識,而且還包括大量的非結構性的經驗背景。對新信息的理解是通過運用已有的經驗,超越所提供的新信息建構而成的,而且,記憶系統中所提取的信息本身,也要按具體情況進行建構。建構一方面是對新信息意義的建構,同時又包含著對原有經驗的改造和重組。另外,因為學習者是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對事物的理解,從而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的方面,因而不存在惟一標準的理解,學習者之間可以通過合作,更加豐富和更加全面地理解事物。
(二)學習共同體理論
在協作學習技術尤其是計算機網絡技術和通訊技術的支持下,社區參與者基于自身需要(掌握知識、獲得技能、情感交流等)或是為了完成特定的學習目標而在參與者之間形成的知識共享和交互學習的人際關系網絡,并在其中體現著一定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共識。通常將網絡中的學習群體稱之為虛擬學習共同體,簡稱學習共同體。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是基于虛擬學習社區學習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張建偉[3]指出,學習共同體是指一個由學習者及其助學者(包括教師、專家、輔導者等)共同構成的團體,他們彼此之間經常在學習過程中進行溝通、交流,分享各種學習資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學習任務,因而在成員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人際聯系。在傳統教學中,教師、學生同時在一個教室中參與教學活動,彼此之間可以很容易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定的學習共同體,比如一個學習小組,一個班級,乃至一個學校,都可能成為一個學習共同體。虛擬學習社區形成的基本要素:[4]
(1)共同的目的:這是人們參與到學習社區來的基本原因,也是學習社區存在的基本條件。比如共同的興趣和愛好需要一個共同的空間來進行分享,或者學習某一領域的知識需要彼此分享知識和經驗。
(2)共同的文化背景:對虛擬學習社區來說,文化背景可表現為一種集體身份。文化的內在的表現包括成員的價值觀、信念、態度、行為規則和人生經歷。文化的外在表現就是成員內在身份的表象,包括語言、行為、外觀、禮儀、傳統等。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的學習社區的成員具有共同的語言,容易進行交流和互動,較易形成密切的關系。如遠程教育的學生就易于形成虛擬學習社區。
(3)公共的空間:即學習社區的成員共享一個虛擬的空間進行互動。在這一虛擬空間中,有各種通訊工具供成員進行交流和討論。如論壇、聊天室、E-mail等;也有各種資源供學習者共享;還有學習者的私人空間,如文件夾、學習文檔和日記簿等。
(4)公共的時間:雖然學習社區里的互動可以是同步也可以是異步的,但也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時間段來保證學習者之間的互動,即要有一個參與的頻度。特別是對遠程教育的學習者來說,學習任務都有一個時間限制。成員參與的頻度越高,就越容易形成較強的社區歸屬感。
(5)自愿參與:虛擬學習社區都是基于人們的自愿而形成的,如參與者的學習動機促使他們參與到學習社區中去。在遠程教育中,雖然對學習者有一定的制度性要求,但也是基于其學習的目標和意愿的。
(6)共享知識/智慧:這是建立虛擬學習社區的主要目的之一。學習者共享他們的知識和經驗,共同解決問題,共同承擔學習任務,逐步形成可隨時訪問的共享的知識資源庫。在長期的相互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的認知能力得到提高,個體智慧和集體智慧得以形成和共享。
(7)共同實踐/行動:學習社區不僅僅是共享知識,更重要的是把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實踐中去,應用到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去。學習者通過參與共同的學習活動和項目,進行交流和合作,就會使學習更深入,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知識的共享和實踐的應用與反饋,可以形成很多的“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s),形成高質量的集體知識庫,同時使學習者的個體能力得到提高,學習的興趣和動機得到加強,也會形成強烈的社區歸屬感。
(8)共享愿景/共創未來:當學習社區的成員以上述方式行動,共同的學習愿景和學習文化就會形成,學習社區就會變得更有吸引力,成為一個良好運行的學習環境。
在網絡學習環境中,學習共同體的建立是以成員之間基于網絡的交互活動為基礎的。在學習共同體中,學習者彼此之間的交互活動會對其認知活動產生促進作用。Scardamalia和Bereiter研究表明,基于計算機的溝通交流可以促進知識的獲得和應用,可以深化學習者學習和反思活動的深度,增強他們的學習需要以及對學習活動的自我意識。計算機支持的合作學習在開放的時空環境,突破了傳統的學校教育的時空界限,使得學習、交流、合作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增強了學習的協作性。由于基于網絡的遠程學習環境中,學習者較少甚至是不能面對面接觸,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以及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交流往往是不同步和非實時的,因而形成學習共同體非常困難。
四、基于網絡的生態學習共同體
生態學是研究生物與生物及生物與環境之間關系的一門學科。學習生態觀用生態學的視角觀察學習,認為“是各種生命體與其所賴以生存的環境系統共同存在、協調進化,正如學習者和他所處的學習環境一樣。學習共同體可以看作一個學習生態系統”[5]。從結構上分析,學習生態系統是由學習共同體和學習環境構成的動態開放的功能整體。它具有開放性、多樣性、交互性和可持續發展性等特點[6]。學習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學習共同體主動參與學習環境,對其環境所能提供的給養進行調適。在這個生態圈中,學習生態系統中的學習環境包括資源環境、文化環境和交互協作環境,它和作為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的學習共同體,相互聯系、相互制約,通過相互作用達到生態平衡。
五、小結
學習者和助學者由共同的學習目標來凝聚,構成了學習共同體。學習目標是共同體建立的出發點和歸宿,體現了學習目標凝聚力和共同體的歸屬感。而學習活動需要工具、導航、規范和相關幫助的支持。基于網絡環境下的虛擬社區學習,共同體成員借助學習工具實現交流、協作以及知識的建構。助學者(包括教師、專家、輔導者)作為學習的實施者、促進者和學習者的伙伴、朋友,他們利用資源和工具創造學習情境,引導學習者自主選擇學習任務和與其他成員之間進行交流,為學習者建立新舊知識間的聯系,促進其對新知識的反思和遷移。助學者在參與學習的同時對整個系統的信息流動進行控制。維護系統的動態平衡,學習者和助學者的學習活動是系統運動的內動力,系統的功能就是促進他們的學習。
[1]趙國案,朱新梅.論網絡高等教育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J].中國遠程教育,2002,(5).
[2]胡凡剛.簡論虛擬學習社區 [J].電化教育研究,2005,(9).
[3]張偉建.試論基于網絡的學習共同體[J].中國遠程教育,2000(增刊).
[4]甘永成,王煒.虛擬學習社區多重內涵之解析與研究[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05,(5).
[5]張豪鋒,卜彩麗.略論學習生態系統[J].中國遠程教育,2007,(4).
[6]韓曉玲.網絡學習生態系統構建[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