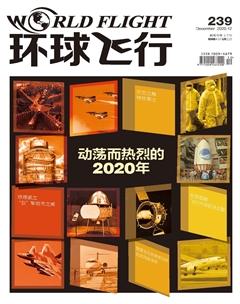全球首輛飛行汽車歐洲上路
許林宇

通過測試,帶著牌照上路
自今年2月以來,PAL-V公司設計研發的商業產品Liberty便陸續通過多個測試,包括嚴格的高速路上行駛、制動和排放測試以及噪聲污染測試等。如今終于可以帶著官方牌照在公共道路上行駛了,而這一突破意味著PAL-V距離飛行認證又近了一步。
PAL-V的試駕員漢斯·喬爾在描述首次乘駕的感受時依舊很激動:“當我第一次啟動PAL-V時,我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聽到車輛啟動的聲音真是太美妙了,駕駛感覺也很棒。它行使平穩,轉向靈敏,重量只有660公斤,加速性能非常好。 整體體驗就像一輛跑車,感覺棒極了。”

PAL-V首席技術官邁克·斯蒂克倫伯格介紹說:“帶著概念原型PAL-V One的飛行和駕駛測試記憶,我期待對Liberty進行測試。為了這一里程碑,我們多年來一直與路政部門開展合作。要讓一架‘折疊飛機通過所有道路通行測試極具挑戰性。”

他補充說:“對我來說,成功制造飛行汽車的訣竅,是確保設計符合航空及道路法規。我感受到了我們團隊的能量和動力,我們努力推進最后幾個關卡,還將使Liberty通過飛行認證。”
自2015年以來,PAL-V Liberty的設計已經通過了歐洲航空安全局(EASA)的航空認證,預計在2022年完成。在最后150小時的飛行測試開始之前,需要完成1200多份測試報告。在這之后,公司就可以開始向客戶交貨了。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PAL-V Liberty將在歐洲各地的公路上進行耐久性測試。
價格不菲,駕駛者必須持“雙照”
在最近的幾十年中,荷蘭因其在創新和產品設計上的飛躍而聞名世界。自2011年以來,總部位于荷蘭的PAL-V公司便一直在研究飛行汽車的概念。
PAL-V Liberty已經開發了十幾年,期間不斷改進完善,并于2012年4月首飛。采用基于Rotax電機的雙動力傳動系統,該車輛有兩個獨立的電動機,一個用于飛行,一個用于道路。
2017年2月13日,PAL-V公司在官網上正式啟動雙座混合動力飛行器PAL-V Liberty的銷售。從圖片上可以看出,這架飛行器看起來像是旋翼直升機和三輪摩托車的結合,可以像傳統汽車一樣在公路上行駛,或者用10到15分鐘的時間轉換成飛行模式后選擇起飛,起飛所需空間最小可為一塊長30米、寬20米左右的空曠場地。

PAL-V Liberty在陸地上可達到約160千米/小時的速度,而在空中則可達約180千米/小時,飛行高度可達約1220 米。PAL-V公司認為,與固定翼飛機相比,PAL-V的飛行速度非常慢,遇到的湍流更少,著陸所需的空間也更小。
想要駕駛PAL-V Liberty,用戶當然必須要有相應的執照,除了汽車駕照,飛機駕照也是必不可少。要獲得飛行員執照,用戶需要通過理論考試,并需要在旋翼飛機教練的指導下接受30至40個小時的培訓,或者直到具備“導航,儀器,氣象,空氣動力學和性能的一些基本知識”。除此以外,用戶還需要使用飛機跑道或其他合適的開放空間進行起降。考慮地面交通的復雜性,用戶肯定不能在公共道路的中間進行此操作。
除外以外,就算擁有飛行員執照,這個飛行汽車高額的價格恐怕也將成為一個影響其銷量的因素。官方網站上,基礎自由運動版售價39.9萬美元(約260萬元人民幣),而更具時尚感的先鋒版(Pioneer Edition)售價為59.9萬美元(約390萬元人民幣)。定購還需先付1萬美元的定金。
PAL-V表示,盡管價格不便宜,但PAL-V Liberty預訂量的增長“超出預期”,目前大約80%的預訂者是航空新手,他們中的部分人已經開始在PAL-V fly drive學院接受旋翼飛機飛行執照的培訓。
積極布局,中國并不落后
當前,隨著生產技術的迭代升級,所謂的“飛行汽車”已擺脫制造技術的束縛。而在人工智能和自動駕駛技術的賦能下,“飛行汽車”更是由最初的實驗性產品,發展為資本市場關注的熱點。
資料顯示,目前全球在研的“飛行汽車”項目已超200個,參與者既有大眾、豐田等頭部車企,也有谷歌、騰訊、英特爾等科技巨頭。
2017年,當PAL-V Liberty正式亮相銷售時,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羅伯特·丁格曼斯曾將這些車輛的推出稱為“航空和機動性歷史上的關鍵時刻”。此次PAL-V Liberty在歐洲通過上路測試,也許正為“飛行汽車”時代的來臨用力推動了一大步。
據國際投行摩根士丹利預測,到2030年,“飛行汽車”行業將創造3000億美元市場規模,最初會轉化部分地面交通、飛機和公共交通的市場份額,伴隨技術發展最終會開啟多個全新的商業領域,2040年可發展至1.5萬億美元市場。
摩根士丹利認為,中國、歐洲、美國將占主要市場,而新西蘭、新加坡、巴西、墨西哥等將有望成為最早采用“飛行出租車”的國家或地區。

日益壯大的中國作為汽車大國,在飛行汽車領域的布局并不落后。
國內車企巨頭吉利早在2017年就通過全資收購Terrafugia實現飛行技術與產品的落地。今年5月,Terrafugia啟動框架機地面調試和可靠性測試,目前該產品已開始接受預定,計劃于2023年正式上市。
2019年8月,廣州與全球城市空中交通領域第一家上市公司億航智能簽署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成為億航全球首個空中交通試點城市。當年,億航載人飛行器成功在廣州完成飛行。
今年9月的北京車展,由小鵬汽車CEO何小鵬和小鵬汽車共同投資、控股的航空科技公司小鵬匯天正式對外亮相,并帶來了旗下首款超低空飛行汽車“旅航者T1”。據了解,小鵬匯天正在研發第二代超低空飛行汽車,預計2021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