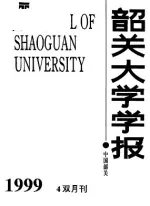黃宗羲與韋伯的反君主專制思想初探——《明夷待訪錄》與《儒教與道教》之比較
葉思冰
(華南師范大學(xué) 政治與行政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0631)
建立于1368年的明王朝把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自明太祖朱元璋宣布“永不立相”后,明朝實際上實現(xiàn)了君主一人的絕對統(tǒng)治。著名的愛國主義思想家黃宗羲,就如黑格爾口中的“迷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到來以后才起飛”。面對入關(guān)的清貴族用鐵蹄踏平中原,依靠野蠻的民族恐怖政策,加強中央集權(quán)統(tǒng)治,黃宗羲希望從流血政治斗爭的失敗中總結(jié)教訓(xùn),為未來的理想社會設(shè)計治理藍圖。他冷峻地思考,用犀利的筆觸,于1663年寫出了《明夷待訪錄》。
一、黃宗羲的君主觀
(一)君主不應(yīng)該奪民之利,君主的專橫造成生靈涂炭
在開篇的《原君》,黃宗羲討論君主是為公還是為私,他認為君主應(yīng)該是“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1]6。古之君——許由、務(wù)光、堯、舜、禹者正是這樣的君主,他們不在于為自己謀利,而要讓天下人享受利益,他們的存在滿足了天下百姓的需要。這才是真正的君主,是為民請命的大公。而后世的君主卻不是這樣的,他們居于至高無上的核心地位,“以為天下利害之權(quán)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天下之害盡歸于人”[1]8,這就是“大私” ;君主把天下看成了私產(chǎn),君主是最大的家長,“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chǎn)業(yè)”[1]8。
黃宗羲看到了皇帝權(quán)力無限、濫用權(quán)力帶來的惡果是“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1]8,黃宗羲憤然喊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1]8, 君主是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功”[1]8的獨夫民賊,他們即使推動了歷史的發(fā)展,歸根到底是為了“固為子孫創(chuàng)業(yè)也”。
(二)封建綱常的“君為臣綱”,應(yīng)由君臣來共同治理國家
黃宗羲在《原臣》論述道:“為民還是為君”,才是臣與不臣的標志。社會事務(wù)的紛繁復(fù)雜,需要君臣的分工,共同治理,黃宗羲認為群臣的職責(zé)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1]14,應(yīng)該對人民負責(zé),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情懷的發(fā)展。對于君臣關(guān)系,黃宗羲持這樣的觀點:君與臣沒有什么不同,君臣之間是“共曳木之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臣應(yīng)該是“君之師友”而非“君之仆妾”。唯命是從和奴顏婢膝是不可取的,但是“三代”之后,臣只是為君效力,是君主權(quán)力擴張的幫兇和爪牙,只有君主才是社會唯一的主人。
(二)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強調(diào)監(jiān)督君權(quán)
黃宗羲指責(zé)“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在《原法》中,他開宗明義地指出“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1]21,對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三代以后,君權(quán)凌駕于法律之上,這種王法沒有為天下之心,它的本質(zhì)是帝王個人意志的體現(xiàn),其作用只能是維護王權(quán),因此“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因此,黃宗羲提出要有“治法人而后有治人”[1]25,要先訂立天下之法,由君主、宰相、大臣共同掌握立法、司法權(quán)利,還建議學(xué)校不僅要“養(yǎng)士”還要“公其非是”,監(jiān)督輔佐朝政,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
《明夷待訪錄》的《原君》、《原臣》、《原法》三篇集中反映了黃宗羲抨擊君主專制制度。經(jīng)歷了南明王朝的茍延殘喘、清王朝的穩(wěn)定、再到明王朝的覆滅,黃宗羲痛定思痛,著書講學(xué),對歷史進行深刻的探索和反思。此時他不再以反清復(fù)明的民族主義者的政治態(tài)度,而是用一個民主啟蒙主義的思想家的獨特視角,把朝代的沒落的根本原因歸結(jié)于“君主專制”,無情地撕下了封建王權(quán)的神圣外衣,這種批判是空前的、尖銳的、激烈的,可謂批判君主專制制度的檄文[2]。
二、韋伯的君主觀
對比同致力于通過文化類型來研究東方專制主義的社會學(xué)家韋伯,又一個新的角度認識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韋伯用社會學(xué)的構(gòu)造性功能來分析君主專制存在的原因,顯示出強大的說理性,這給我們認識中國的君主專制、理解黃宗羲的民主啟蒙思想提供全新的視角。
在韋伯的研究中,中國是典型的家產(chǎn)制社會。“家產(chǎn)制”的概念出現(xiàn)在韋伯探討統(tǒng)治合法性的來源時,韋伯認為歷史上的一切統(tǒng)治形式是由三種理想類型(卡里斯馬型、傳統(tǒng)型和法理性)所混合或修正而成。而“家產(chǎn)制”則是傳統(tǒng)型的一個變種,由家長制變異而來,這里的“家長制”是一種純粹類型的傳統(tǒng)統(tǒng)治。
(一)中國“家產(chǎn)制”特點凸顯
一是統(tǒng)治側(cè)重中國的傳統(tǒng)。中國的“家產(chǎn)制”堪稱從秦始皇統(tǒng)一到晚清時期的中國社會“最恒久的特征之一”,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一方面,中國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威,既有著家長制的“專斷”的共性,又側(cè)重于中國的傳統(tǒng)。受儒家思想、中國科舉制度、士人階層的共同影響,皇帝不僅是政治經(jīng)濟的統(tǒng)治者,還是傳統(tǒng)思想的宣揚者,強化祖先崇拜。君主具有祭司的壟斷權(quán),神性賦予皇權(quán)合法性,“皇帝不僅是一個大領(lǐng)主,而且是一個最高祭司”,因此世俗的權(quán)威和神靈的權(quán)威統(tǒng)一于皇帝一人之手。此外,巫術(shù)和農(nóng)耕等儀式為皇帝披上神圣的外衣,讓世人相信:皇帝是神授的君主,是上天派來統(tǒng)治他們的。如果對皇帝發(fā)動戰(zhàn)爭,一定意義上是對儀式的褻瀆,要遭致不可思議的惡果。這樣就把皇權(quán)神化,既保證了皇權(quán)的至高,又使其變得肆無忌憚。
二是皇權(quán)具有專斷性和隨意性。皇權(quán)的專斷性和隨意性是中國“家產(chǎn)制”的重要特點。“家產(chǎn)制”由家長制變異而來的,一家之主獨享的權(quán)威隨之延伸到最高統(tǒng)治者手中;此外,人們將對家長的孝順與神圣傳統(tǒng)約束權(quán)力(如上文提及的“人們對神權(quán)的崇敬”)結(jié)合起來。這些不僅為皇權(quán)提供了合法性基礎(chǔ),而且讓皇權(quán)失去了外部的制約,皇權(quán)因此形成專斷性和隨意性。在皇權(quán)被傳統(tǒng)不斷強化的前提下,中國的法也是“依賴于皇帝的個體化和恣意專斷”。皇帝根據(jù)個人的性格、習(xí)慣等因素制定法律,因此這種法律與皇帝個人非理性因素密切聯(lián)系。與其說這樣的法律是“國家之法”不如說是“一人之法”、“一家之法”,這也剛好吻合黃宗羲說的“三代以下無法”。皇帝的“一人之法”因個人主觀隨意、專斷性強,制造了許多沒有公私之分、重實際輕形式的法律,這些法律的貫徹實施只是代表了天子觀念,違背了“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完全沒有“天下之人”的理念,最終使“天下之亂”。
另一方面,君主的實力來源于臣民的徭役,為了服徭役,許多家庭流離失散,深受苦徭役的毒害:妻子因缺少丈夫而不幸,子女無人撫養(yǎng)。正如黃宗羲所言:“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chǎn)業(yè)”[1]8。
(二)在經(jīng)濟上,中國君主掌握著土地、經(jīng)濟大權(quán);在政治倫理核心上,由“孝順”發(fā)展而來的“忠誠”塑造了臣民的奴性,強化了君臣的主奴關(guān)系
在韋伯的筆下,中國君主是最大的家長。在經(jīng)濟上,中國君主掌握著土地、經(jīng)濟大權(quán)。自夏“家天下”開始,中國的君主們將天下視為一己之私產(chǎn),視“天下人民為人君囊中私物”,進而把人民創(chuàng)造的財富看成自己的私產(chǎn),最后“視天下為莫大之產(chǎn)業(yè)”[1]8。為了發(fā)展“產(chǎn)業(yè)”,實行井田制的田地耕作方式,因水利工程而擴大徭役,這些導(dǎo)致一再出現(xiàn)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jīng)濟壟斷思想。
在政治倫理核心上,由“孝順”發(fā)展而來的“忠誠”塑造了臣民的奴性,強化了君臣的主奴關(guān)系。按照韋伯的說法:“家產(chǎn)制”帝國的政治倫理核心是孝順。孝悌實際上就鞏固了君權(quán),家產(chǎn)制以孝順為基本美德,領(lǐng)主與仆人、官吏的隸屬性基于孝順。”[3]165-166一方面,儒學(xué)家利用孝順衍生出儒家倫理道德規(guī)范,“三綱五常”就是核心代表,包含于“三綱五常”的“君為臣綱”自然也就植根于孝順,將子對父的孝順轉(zhuǎn)化為臣對君的忠誠。這就強調(diào)了上對下的權(quán)威性和下對上的順從性,臣民把在家對長輩的“孝敬順從”與對君主的“忠誠”結(jié)合為“忠孝”。于是,出現(xiàn)了:“孝是對履行官僚體制的最重要的義務(wù),當(dāng)種種德行之間發(fā)生沖突,孝先于一切,從孝當(dāng)中衍生出無條件的紀律,對于紀律的無限信仰,正保證了君主權(quán)力的穩(wěn)固。”[3]這讓我們更深入理解黃宗羲的論斷:大臣只是服務(wù)于君主的專制而奴役人民。
三、黃宗羲與韋伯的君主觀比較
(一)黃宗羲與韋伯的君主觀相同之處
黃宗羲所言的“一人之法”產(chǎn)生于皇帝對權(quán)力具有壟斷性。君主“不僅是一個大領(lǐng)主,而且是一個最高祭司”。巫術(shù)等儀式為皇帝披上神圣的外衣,讓世人相信:皇帝是神授的君主,是上天派來統(tǒng)治他們的。如果對皇帝發(fā)動戰(zhàn)爭,一定意義上是對儀式的褻瀆,要遭致不可思議的惡果。這樣就把皇權(quán)神化,世俗的權(quán)威和神靈的權(quán)威統(tǒng)一于皇帝一身。既保證了皇權(quán)的至高,又使其變得肆無忌憚,超越法律。
皇權(quán)的專斷性和隨意性是中國“家產(chǎn)制”國家的重要特點。“家產(chǎn)制”由家長制變異而來的,一家之主獨享的權(quán)威隨之延伸到最高統(tǒng)治者手中[4],這些不僅為皇權(quán)提供了合法性基礎(chǔ),而且讓皇權(quán)失去了外部的制約,皇權(quán)因此形成專斷性和隨意性。在皇權(quán)被傳統(tǒng)不斷強化的前提下,中國的法“依賴于皇帝的個體化和恣意專斷”。與其說這樣的法律是“國家之法”不如說是“一人之法”、“一家之法”,這也剛好吻合黃宗羲說的 “三代以下無法”。皇帝的“一人之法”因個人主觀隨意、專斷性強,完全沒有“天下之人”的理念,最終使“天下之亂”。
(二)黃宗羲與韋伯對于“君主專制”不同之處
根據(jù)艾森斯塔得的理論,專制時期的中國屬于典型的歷史官僚帝國政治體系,它以相當(dāng)程度的社會分化為條件,因此存在一定水平的普遍化權(quán)力,即宗族等勢力的發(fā)展,但這種分化又不能超出統(tǒng)治者的傳統(tǒng)合法性所能容許的限度。宋元以后,當(dāng)然這就包括了黃宗羲所在的明代,宗族的勢力更加弱小,而專制政權(quán)的自主性趨向更為明顯,到了宋以后,特別是黃宗羲所在的明清之際,君權(quán)成為社會發(fā)展的絆腳石。“明代是最典型的君主集權(quán)國家,以君權(quán)為綱,加上神權(quán)、族權(quán)、夫權(quán),編織起一整套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網(wǎng)絡(luò)體系。”[5]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讓君權(quán)走到極端,為了防止相權(quán)太重而廢除宰相制度,缺少機制制約的皇帝個人權(quán)力得到強化,他集政軍財各種大權(quán)于一身,實現(xiàn)了“朕即國家”的“理想”。社會的興衰完全維系在皇帝身上,高度集中的權(quán)力在面對危機時,就徹底地崩潰。
明朝后期的著名學(xué)者黃宗羲,作為對中國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深入思考的第一人,他把矛頭直接指向君主專制制度,批判中國君主權(quán)力無限、濫用權(quán)力、缺乏監(jiān)督,最終導(dǎo)致王朝的“天崩瓦解”。黃宗羲彰顯的是處在風(fēng)云變幻的社會中產(chǎn)生的一種民族意識、政治思想,因此“黃宗羲的政治思想既不可與西方近代的民主啟蒙思想相提并論,也不能簡單的歸為儒家民本論。宗羲言必稱‘三代圣王’,強調(diào)禮樂、圣王和賢能之治”[6]。 出自《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告訴我們,在這個大同世界,天下太平,人與人永遠的和睦相處,人人為公,沒有私欲,所以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一部“天下之法”,代表天下人的利益。但是現(xiàn)實中,只要人有私欲,人的利益就有沖突,就沒有可以代表全天下人的“天下之法”,而且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wù)的,這也說明了法律是不可能代表“天下”利益的。因此,黃宗羲的觀點存在一定的空想性。
而韋伯從學(xué)術(shù)的角度,以中國是“家產(chǎn)制”帝國為立足點,從“家產(chǎn)制”帝國中“皇權(quán)的專斷性和隨意性”“皇帝的祭司地位”和“政治倫理核心”等主要特點來分析“君主專制”在中國存在的內(nèi)在基礎(chǔ),展示出說理、論證的嚴密邏輯性。
綜觀黃宗羲與韋伯的論述,相得益彰,給我們認識、探討“君主專制”提供中西兩種不同的思維視野。
:
[1]黃宗羲.明夷待訪錄[M].段志強,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2]斯邁,桂興沅.黃宗羲反對君主專制思想的再評價《明夷待訪錄》論綱之一[J].寧波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黃宗羲研究專輯,1986(S1):19-27.
[3]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M].洪天富,譯.南京:江蘇出版社,2010.
[4]丁莉婷.家產(chǎn)制與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命運—馬克斯·韋伯筆下的中國“家產(chǎn)制”淺析[J].河北科技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8(2):124-128.
[5]季學(xué)源,桂興沅.明夷待訪錄導(dǎo)讀[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8:15.
[6]魯敏,連鵬曉.黃宗羲反君主專制思想解讀[J].邢臺學(xué)院學(xué)報,2008(1):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