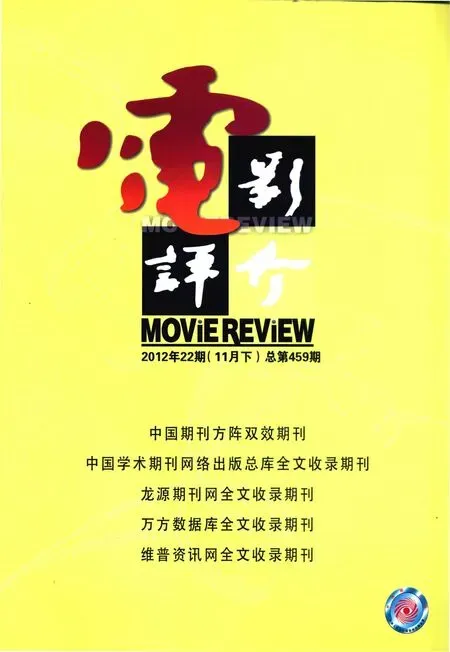論第六代導演的真實美學藝術
一、 真實美學的引入
安德烈·巴贊〔1918—1958〕是法國新浪潮電影的理論旗手,是世界電影三大流派之一——現實主義流派的主將。1945年他發表的《攝影影像的本體論》是電影本體論的基石。他認為,文中的核心命題“影像”與客觀現實中的“被拍攝物”都具有本體論的意義。因此,電影美學的基本原則就是電影再現事物原貌的獨特本性。基于影像本體論,巴贊總結了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美學的特點,提出“真實美學”的概念。
中國電影對真實美學的追求從第四代導演手中開始,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影響和巴贊的紀實美學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暗合了第四代電影導演要求電影回歸現實的迫切愿望,因而他們自覺地、有意識地選擇并實踐了真實美學,并在20世紀80年代創作出了一批帶有鮮明真實美學風格的優秀影片。如張暖忻的《沙鷗》,《青春祭》等。90年代以來,第六代電影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第六代導演在一定范圍內延續了真實美學的創作特征,并將這種創作趨勢個風格進行了中國化實踐。
二、第六代導演的美學實踐
中國第六代電影導演群體如北影89屆畢業生王小帥、婁燁、張元、路學長等人以及后來的賈樟柯等于20世紀90年代初登上影壇,90年代中期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他們作品中的青春眷戀和城市空間與第五代電影歷史情懷和鄉土影像構成主題對照:第五代選擇的是歷史的邊緣,第六代選擇的是現實的邊緣;第五代破壞了意識形態神話,第六代破壞了集體神話;第五代呈現農業中國,第六代呈現城市中國;第五代是集體啟蒙敘事,第六代是個人自由敘事”[1]。雖然在敘事策略上跟觀眾心理期望值要求還有一定距離,但由于他們追求講事實的風格,也注重生活化的元素,所以作品具備了真實和自然的兩大特征。[2]
第六代導演的電影借鑒了巴贊真實美學并深受影響,他們主張用鏡頭來直接的反映生活,反映社會的本來面目,具有很強的寫實主義,堅持了對真實的審美,力求反映現實,表現現實,他們的探究和實踐使巴贊的真實美學有了中國社會和電影的自身特色。
(1)城市邊緣人——深切的人文關懷
真實美學力求將鏡頭對準普通人的生活,追求現實性主題。第六代導演的電影主題無疑契合了這一點。選擇題材方面他們摒棄第五代導演較為沉重的主題和宏偉的敘事結構,多為關注當下社會現實,關注小人物的悲喜和城市邊緣人的生存困境和遭遇,在他們的影片里,小偷、妓女、無業青年這些邊緣人會成為主角。日常瑣碎的生活本真,庸常平實的生活狀態以及對這些狀態的客觀呈現構成了他們的影片風格。
賈樟柯的《小武》就是很好的例證。賈樟柯在這部影片的導演自述中這樣說:“我在拍《小武》之前,看了無數的中國電影,應該說幾乎所有的中國新電影我都看到了。我有非常不滿足的地方。我從這些影像里面,看不到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態,也看不到當下中國社會的狀態,幾乎所有的人都回避這個問題,對當下社會的狀況、人的處境視而不見。”[3]影片刻畫了改革開放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處于社會底層的小偷小武的形象,主人公小武是一代中國農村娃的代表,落后的文化,貧窮的家庭,走上偷竊為生的道路,影片講述了在別人的唾棄與排斥中的邊緣人三段感情的喪失,親情的冷漠,愛情的拋棄,友情的決裂。像汾陽這樣的小城中國有千千萬萬,像小武這樣的邊緣人中國也有萬萬千千,他們固守原有的生活模式,在時代劇變前或頹然麻木或固步自封,陷入激流的巨浪中而不可自拔。賈樟柯把鏡頭對準他們,真實刻畫了他們的生活狀態。他們也許貧賤也許卑微,卻也有著和普通人一樣的喜怒哀愁。“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個平淡生命的喜悅和沉重。”電影《小武》正是用紀實的手法,表現出以小武為代表的社會邊緣人的日常生活、喜怒哀樂、生老病死,表達他們青春的焦慮和迷茫,表達他們人生的無奈和悲涼。
(2)長鏡頭的表現——真實再現生活本真
在表選形式上,第六代導演除了選用更多的選用實景拍攝,跟鏡頭等手法更多的是長鏡頭。
巴贊強調“攝影的美學特性在于揭示真實”[4]而長鏡頭的運用讓現實生活第一次那么有質感地出現在銀幕上,真實的表現了生活的本真,這在賈樟柯、王小帥、婁燁等人的影片中表現得同樣十分明顯。
像《十七歲的單車》用長鏡頭表現清晨的北京胡同,《扁擔姑娘》中阮紅回到自己的住所,通過一個長鏡頭表現出黑暗的房間和她無助、孤寂的內心等,都是非常好的運用。
(3)非職業演員和方言——本色演出直指人心
安德烈·巴贊在《什么是電影》一書中對非職業演員的出演做過這樣的評價:“固然,這種物色演員的方法違背電影常規,但是畢竟不是一種全新的方法。相反,可以說自路易·盧米埃爾起,各種‘現實主義’的電影流派就不斷采用過這種方法,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條真正的電影規律,意大利流派只是充分肯定了這條規律并且為它提供了可靠的依據。過去,我們對蘇聯電影采用非職業演員,讓他們在銀幕上扮演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角色的做法也倍加贊賞”[5]
第六代導演多使用非職業演員,以賈樟柯電影《小武》為例,大量非職業化的演員真實自然的表現角色內涵,梁小武父母的出演者就是賈樟柯在圍觀的群眾中選出的,他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表演,而這種真實自然的本性演出反而是整部影片的一個亮點,完全把一個北方老漢的日常生活習慣、習慣動作以及語言特色表現出來了。除此之外賈樟柯的影片《站臺》、《世界》中大部分都是非職業演員。《安陽嬰兒》、《巫山云雨》等也都采用非職業演員。
方言的使用能給影片帶來了濃濃的生活氣息。方言是一個地區文化的承載,是地方特色的體現,具有文化真實和生活真實,在影片中使用方言仿佛給觀眾還原了影片講述的真實場景。除《世界》以外,賈樟柯的“故鄉三部曲”和《三峽好人》中的主人公都是操著一口山西口音,這不僅表現出導演所要表現出的鄉土氣息,還能使觀眾更好的理解片中角色的思想性格以及命運遭遇,能把人放在他所處的那個大環境中去理解他感受他。
(4)開放性的敘事——碎片化及情緒化的真實傳達
在敘事上,第六代導演做打破時空結構來取代時空的統一性,大多數“第六代”影片中,導演對故事的發展基本上放棄了控制,打破了常規的敘事結構,敘事結構甚至是由幾個零碎的片段組合而成,這打破了傳統電影情節敘事的系統性和連貫性,呈現個人化情緒化抑或不確定化的敘事方式,追求碎片化的形象,刻意模糊敘事線索和淡化敘事,來還原真實的生活狀態。
如張元的《北京雜種》在敘事結構上就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時空順序結構。為了排練四處尋找場地的地下搖滾青年;尋找懷孕卻又失蹤的女友的酒吧老板;被畫商騙錢的自由畫家……直到影片的最后,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都還在各自的尋找當中。影片中插入了許多搖滾樂隊演出的場面,以此來打破故事的完整性。這種打破了情節流的敘事模式不斷穿插幾個主要人物的一連串零碎場面,相互交替切換造成整個影像紊亂龐雜。而這并不是要表現某一個故事情節,只是要單純的真實反應這群年輕人的迷茫與焦躁的生活狀態,讓觀眾在觀影的時候能感同身受。
三、對第六代導演的反思
第六代導演成長于中國社會轉型的新時期,他們將鏡頭對準了社會里的邊緣人,用客觀的鏡頭語言去紀錄真實、展現真實,通過對邊緣人的真實來反映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社會問題和這些問題之下的國民的生活狀態。他們重新扛起了真實美學的大旗,深層表達都市意象,深切關懷社會邊緣人,主題寫實敘述寫意,這不僅豐富了社會轉型后國人的審美體驗,更豐富了我國電影的美學體驗。他們通過集體的努力,取得了積極的美學成果。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第六代導演的電影定將結出更豐碩的果實,第六代導演的電影也將成為世界關注中國,了解中國的一面鏡子。
注釋
[1]楊遠嬰: 《百年六代影像中國——關于中國電影導演的代際譜系研尋》,《當代電影》,2001第6期, 99—105頁。
[2]樸宰亨:《論“第六代”導演的電影創作》[D],上海:復旦大學,2009
[3]黃佼:《賈樟柯電影的美學風格研究》[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06
[4]安德烈 巴贊(法):電影是什么[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5]安德烈 巴贊(法):電影是什么[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