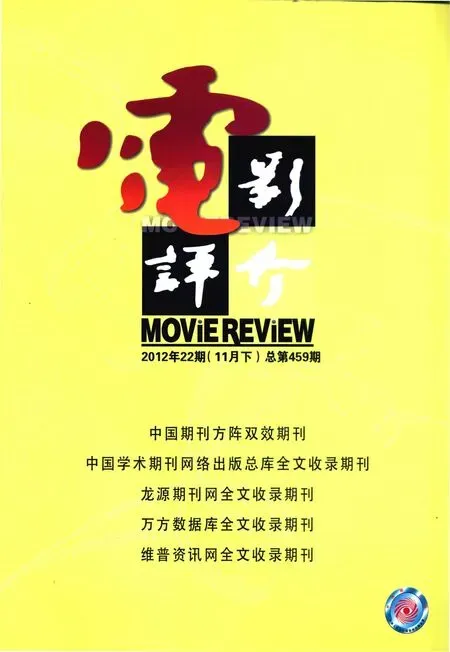時間只記住精品:趙明舞蹈作品的時代意義
自1986年的舞蹈作品《囚歌》問世以來,如果還涵蓋趙明更早期的創作作品,他的舞蹈創作生涯就已有三十年。這期間有若干次個人舞蹈專場作品晚會的舉辦,針對他的舞蹈作品展開的研討會,以及舞劇的無數次被邀上演。三十年里,他的作品也在近二十年中國當代舞蹈的每一次變革中留下了痕跡。作為一名軍旅舞蹈家,他始終走在軍旅舞蹈創作的前沿,成為軍旅舞蹈創作最優秀的總舵手之一;作為一名舞劇導演,他秉承著創作民族化的理念,堅持走中國傳統文化的道路,成為中國主流舞蹈家的中流砥柱之一,而他的作品同時也為舞蹈界帶來啟示。
一、對舞蹈表演的啟示
上個世紀還不時興編舞的八十年代初期,趙明作為舞蹈演員的同時也開始了他自編自跳的舞蹈創作生涯,例如早期的《青春》,還有1986年榮獲第二屆全國舞蹈比賽表演、創作一等獎的《囚歌》等。他將前沿的創作理念與自身扎實的基本功底、強烈的表演意識和清晰的舞臺概念融合,成功地做到從演員向編導的轉換,并站在“演”的角度來創作、調整作為“導”的思路,而非權威地將“導”架空于“演”的層面之上。基于這一點,趙明深有感慨:“在排練中,因為我是演員出身,所以我覺得只有自己將角色的感覺做出來,才能傳達給演員,自己對角色的感覺是最準確的。”因此,年輕的舞蹈演員同樣應多接觸不同舞種,不能以專精單一的舞種來占據舞臺的一生,因為掌握舞蹈語匯的多寡決定著演員在表演上不論是對動作的支配還是情感表達的方式是否能夠豐富多彩、嫻熟自如的基礎。作為一名由演員轉型的編導,趙明最突出的優勢在于駕馭動作的能力。他的動作往往不僅變化多但富有層次感,柔韌細膩而不失流暢,還注重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環境的空間感。
二、對舞蹈創作的啟示
至今為止,趙明的舞蹈作品屢獲大獎,并由于長期的積累贏得了固定的觀眾群。他之所以能夠于21世紀在導演群中脫穎而出,本文從三個角度進行分析。
(1)接受美學角度
接受美學是一種注重觀眾審美接受和審美經驗的方法論,強調觀眾的接受主體性。“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曾說過“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以法國哲學家薩特的話即為“世界萬物只是因為有人的存在,有人的見證,有人的喚醒,才顯示為一個統一的風景。因為有了人,這顆滅寂了幾千年的星,這一彎新月和這條陰沉的河流才得以在一個統一的風景中顯示出來。”[1]而一部文藝作品的價值的確立同樣如此,其最終完成是在“三度創作”——觀眾欣賞之后。作品務必得“經過‘人’的不斷體驗和闡釋,它的意蘊,它的美,也就不斷有新的方面(或更深的層次)被照亮、被揭示。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作品的‘意蘊’和美,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歷史的顯現的過程,也就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生成的過程,”[2]然而,“這個風景,如果我們棄之不顧,它就失去了見證者,而停滯在永恒的默默無聞狀態之中。”[3]正如作品失去了觀看者,就不能被稱為“藝術品”,而僅是編導自己實驗的一項未完成方案。
趙明作品的成功源于他突破了長久以來編導站在自身立場看問題的慣性,以審美者的心態和眼光去捕捉能將日常生活素材轉換為舞臺藝術的在表達方式方面的亮點,并通過舞蹈藝術能符合人類心理審美時空的“超越性”(“在審美心理時空中,主體可以超越和突破客觀時空的束縛,‘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4])、“有機性”(“審美心理時空則是可由記憶、聯想、想象、情緒、情感以及無意識欲望等心理因素介入的復合時空表象。形成一種有機(富有生命的)的‘時空意象’,從而達到‘萬物皆備于我’的境界。”[5])和“互滲性”(“在審美心理時空的統一結構中,空間感向時間感的生成或是時間感向空間感的轉換等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特點。”[6])等優勢,把自己的作品一次次解構成超越觀眾審美意象與愿望的結果。編導趙明將自己對審美心理的認知融入進舞蹈創作手法當中,例如《紅樓夢》賈府沒落的表現形式既是真實敘述了這一事實,又仿佛僅是寶玉絕望之境的一場夢魘,編導在此將舞臺敘事的空間感向時間感凝聚,以帶入觀眾的審美心理時空向主體的心靈縱深方向沉淀,從而提升作品所具備的審美高度。“如果藝術是享受的話,它不是對事物的享受,而是對形式的享受。形式不可能只是被印到我們的心靈上,我們必須創造它們才能感受到它們的美。”[7]趙明舞蹈作品所表現的內容往往是平凡而生活化的事跡(或是耳熟能詳的經典文學題材),“在英雄主義中增添常人之心和近人之情、在備戰狀態下演繹新的故事、在‘愛’的意識中灌注人類意識,”[8]只有當“表現動機的制高點自然上升,才有可能俯瞰到更真實、更復雜、更幽深的人類情感世界的狀態。”[9]因為觀眾今天對于審美“更追求重重交織、‘欲說還休’式的矛盾情感,追求意味深長的、百感交集的體驗。”[10]正是他這種復合的情感體驗讓觀眾獲得審美愉悅,起到了恢復觀眾對舞蹈欣賞對象的藝術感覺以及對本我自性重塑的作用。可以說,觀眾所認可的趙明舞蹈作品之“美”是因為它符合了“美是歷史的范疇”這一原則,審美者把這些所欣賞的“美”的作品“作為一種本真話語,是對存在顯現的本真的領悟,是穿透人的歷史的詩性啟悟,更是通過藝術家而敞開圓融的生命,在意義匱乏中尋找拯救語言的救贖之途,最終把自我帶入存在的澄明之境的一個真正宗教式的對話與超升。”[11]趙明作為當代舞壇主流的中堅力量之一,對比同類型編導,他有著勝于張繼剛作品動作上的飄逸感和流動性,勝于蘇時進作品形象上的親民感和現時性。逐漸引領著審美方向。從而在這個時代建立起極具個人藝術風格的審美坐標。
(2)市場經營角度
古人云,民族、社稷,以舞見興衰。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是舞蹈事業發展的前提條件。相較于中國當代藝術現狀,香港“進念二十面體”劇團導演胡恩威認為,“西方文化體制有分工,藝術、商業、學術這個三角形是互動的。藝術就像一個試驗探索,不需要市場功能,它的目的是為藝術而藝術,但其中有一些可能變成商業,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來決定市場是怎么樣的,而學術就是研究藝術的現象來得出一些分析和批評。這個三角是西方文化體制最基本的概念,為什么西方文化越來越強,就是因為這個三角形長久以來的良性互動。”[12]自市場經濟時代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在受到西方國家強烈沖擊的同時,許多領域在自身還沒有完全定型的情況下又被這股洪流沖擊得人云亦云,在藝術的市場方面,各國的“文藝生活究其存在方式而言已經較大程度地顯現為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這意味著我們與文藝的基本存在關系已經事實上發生了改變,因而文藝在人類生活中的存在方式、存在形式、存在價值乃至存在過程也就相一致地要發生改變,”[13]而這種改變導致了包括舞蹈在內的一切藝術行為都與商業市場接軌。就舞蹈藝術而言,形成了舞蹈創作向舞蹈生產、舞蹈欣賞向舞蹈消費、舞蹈作品向舞蹈產品化的三種轉變,將曾經用以提升人類自性的藝術文化逐漸導向具有商業功利性目的的娛樂產業,而國內又缺少國外那種可以相互牽制的“良性互動”機制。
在當代藝術市場發展現狀下,趙明選擇“既不顛覆,也不重復”,既不放棄市場去絕對關注自我,也不完全以市場的喜好為軸心來大力改變自己的創作方式和理念。由于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而民俗文化占據著整個國家主流文化的絕大部分,對于這一點,趙明表示每次導演一場大型晚會(例如“世博會開幕式”、“春節聯歡晚會”等)都要融入到俗文化的環境中。但矛盾的是,舞蹈事業又是如此神圣高雅的藝術,因此處于這種“夾縫”中如要保持編導的獨立性與純粹性,就要努力去尋求其妥協、遵循的方式,盡力達到不失自己所追求的藝術的本質。不僅是針對舞蹈藝術,做任何一件事情同樣如此,但難度也就在此。因為實際上,超前感的藝術和現時性的市場是絕對矛盾的。在進入創作的階段,趙明往往會給自己劃定一個審美界限,而在創作的過程中則會完全專注自己的意識了。
趙明的作品能夠符合市場的運行機制,與他本人來說有三個主要因素:首先,他關注編導心靈的“純”度,要求編導應以完整的生命投入和生存體驗的姿態融入創作的情境和過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說過:“藝術家的真摯的程度對藝術感染力的大小的影響比什么都大。觀眾、聽眾和讀者一旦感覺到藝術家自己也被自己的作品所感染,他的寫作、歌唱和演奏是為了他自己,而不單是為了影響別人,那么藝術家的這種心情也就感染了感受者。”[14]趙明對于舞蹈藝術品質的追求,強調除了平時對生活的細致觀察外,更務必要擁有一定的境界才能用舞蹈的形式呈現出來,升華之。其次,他關注欣賞之于藝術作品的重要意義,“在整個人類的文藝生活中,欣賞乃是最美妙也最富于人類普遍意義的精神活動,欣賞過程中的詩性領悟、神話性想象和審美性體驗使得個人生活充實而且升華。”[15]趙明以作品中的“詩意”無聲地抵制著因消費需求變化而引起藝術創作方式變化所造成的舞蹈藝術在人類生存中的功能和價值所發生的改變,并且獲得了極大的贊同。第三,他關注編導自身對藝術本質的認識程度和對創作上獨立精神的堅持,“藝術品之所以會有特別的本體論地位,是因為在作品存在情境中文藝的詩性、神話性和審美性構成對人類精神生活的獨特吸引,這種吸引往往具有超越意識形態、地緣文化、時代境遇和個人身份的精神力量,從而形成與人類的終極關系存在關系。”[16]從趙明的作品了解,舞蹈創作離不開本體,更不能局限于本體,不論是創作歷史題材還是當代題材的作品,既要以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去解構作品,又要擇取適合于中西舞蹈文化的“大審美”眼光,但由于演繹的是中國文化題材,因此就還要落實到中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古雅的精神及氣質上。趙明作為一名編導,在純藝術向藝術生產、藝術消費轉變的今天,他針對舞蹈創作本體的認識和定位原則實際上是維護著藝術應于“創作”與“欣賞”而非“生產”與“消費”的本質。對他來說,舞蹈是自己熱愛和尊敬的事業,同時更是一種現實世界的隱喻,一種言說的方式。他將舞蹈與自己的生活融為一體,不斷地了解國際舞蹈的最新信息,不斷充電,以保證自己的作品與觀眾的審美發展對位,與國際潮流接軌,實現真正讓中國的舞蹈具有很強的文化感和時代氣息。自《囚歌》、《走 跑跳》等經典作品問世以來,我們不無啟示,身為編導不僅要具有高度的藝術創新眼光,同時還要具有遠瞻藝術發展前景的眼光。“軍隊文化是新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在信息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軍隊舞蹈也在不斷地擁有發展自身文化體系、軍旅舞蹈美學的可能性,在這樣的一個起點上,誰先深入思考體驗生活,誰先占領藝術創作領域的先機,實際上也就占領了這個藝術創作領域的話語權與原始股。”[17]
(3)生命美學觀角度
蘇珊·朗格在《情感與形式》一書中說到:“舞蹈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幻想,一個‘各種力’的王國,在那里,發散著生命力的純想象的人們,正通過有吸引力的身、心活動,創造了一個動態形式的整體世界。”[18]編導趙明就是通過“各種力”的動態形式建立了自己的舞蹈王國,他對作品動作設計的細微把握從動作屬性、動作質感、動作情感乃至動作的本體之美層面,完全實現了融“身體美學”—“實踐美學”—“生態美學”三種美學形態于一體的生命美學觀。不論是軍旅題材還是歷史、文學題材改編,趙明的舞蹈作品始終向觀眾傳達了一個共通理念——“舞蹈懂得靈魂的公正,它運用為‘詩’服務的藝術鑒賞力,而不是將雜技誤認為是藝術。”[19]
趙明通過作品向人們展示舞蹈藝術對于人類生命自由表現的意義,以自身的感性生命為出發點,以舞臺角色的整個人生乃至現實世界中的生命元素為宏大的敘事場,教導年輕的編導如何在舞蹈的國度中“自由地實現自由”(馬克思語)。更確切地說,其作品所體現的生命美學觀是“弱化了物質性存在的力,超越了感性生命力,它以精神生態力潛入肌體和靈魂結構中,融合、組合人的內在的、多樣存在的生命機能,從而形成內外機能的生態關聯。”[20]而這種透過作品所反饋的信息,我們稱之為人文力。因此,從他的作品當中能夠體會到他所關注的人內在心靈的和諧,遵循生命美學的原則,藝術還應該是“導入平和境界的窗口,而不應勾起人心靈的欲望,引導人心靈的不安、競爭、角逐,這些機心都從趙明的舞蹈創作中悄然蕩去。”[21]綜上所述,縱觀趙明的創作歷程,其“如詩如畫的藝術生態審美之途,也是演替著生命節奏的邏輯之途。”[22]而他的作品也將順著這道“邏輯之途”上升為對生命共同體的審美觀照,必然獲得大眾的推崇,形成一種炙手可熱的現象。
社會經濟的發展未必與藝術的步伐時刻同步,現代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下的快節奏生活,造成人們一切尊崇“效率”的行事風格,讓人很難心無旁騖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當中。對于藝術創作者同樣如此,多數人已逐漸將創作當成一門職業和技術,而非事業和藝術。如今,舞蹈界賽事每年不斷,作品如潮,但佳作難求,社會的影響力仍舊較小。“雖然舞蹈界也有自己所謂的‘精英’,但舞蹈編導一直很難以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的形象確立身份認同,這應該是舞蹈編導們嚴肅思考的文化觀念的問題。”[23]當趙明的舞蹈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時,說明該現象既定位又指明了當代舞壇主流的價值取向——反映我國舞蹈界和廣大群眾“比任何時期更渴求人性的回歸和精神滋養,”[24]同時也反映了趙明作為編導,他對時代走向的總體把握和藝術發展趨向的敏感性。21世紀的今天,社會“倡導個性的自覺性、反思性、超越性,時代向我們每個舞蹈創作個體追問自己言說和表達的意義。”[25]年輕的職業舞蹈編導更應澄明心境,“感應時代變遷而生發的對國家命運、個人命運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命運三者關系的思考、探索和實踐,”[26]承擔起維系和發揚各自國家民族文化的重任。
結語
愛默生說過:“人的性格是比智慧更高一級的,思想是一種機能,而生活卻是產生機能的母體。”生活的經歷是任何一位藝術工作者進行創作的基石,這些經歷可能很平常,也可能很戲劇化——成為人生歷程中的新起點。當普通人可以掠過事物表面僅享受“現成之美”時,藝術工作者卻“一定要具備洞察力:要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同時還必須是個魔術師:能夠讓別人看見自己不用看,但確實看到的東西。”[27]趙明的舞蹈作品在當下深受年輕學子的喜愛或被列為高校舞蹈專業學生排練的劇目,他的藝術理念和為人更對年輕人產生一定影響,而這些成果所帶來的影響對舞蹈表演、舞蹈創作領域產生了啟示的作用(尤其是后者),而這些啟示是具有時代意義的。
注釋
[1][2][3]葉朗.美在意象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P248。
[4]童慶炳,程正民.現代心理美學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P572。
[5]同 上,P575。
[6]同 上,P578。
[7]童慶炳,程正民.現代心理美學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P141 轉自于卡西爾.人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P203。
[8][9][10]胡博.當前軍隊舞蹈發展現狀分析[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6,(4):116-123。
【11】丁亞萍.藝術文化學 [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
【12】楊傳敏.胡恩威:既有娛樂又有先鋒——香港回歸10周年[J/OL].http://nf.nfdaily.cn/nanfangdaily/zt/hk10/yuan/200706280069.asp,2007-06-28。
[13]王列生.文藝人類學 [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14][俄]列夫·托爾斯泰.什么是藝術[M].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1990,P285 轉自于伍蠡甫.西方文論選(下) [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P440。
[15][16]王列生.文藝人類學 [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P285。
[17]李玉.結合趙明成才經歷論舞蹈精英人才的培養 [J/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146c30100eyc5.html,2009-08-29。[18]蘇珊·朗格(著),劉大基,傅志強(譯).情感與形式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P209。
[19]劉青弋.西方現代舞史綱 [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
[20]蓋光.文藝生態審美論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P416。
[21]金浩.論當代舞創作中的文化機杼——兼談趙明舞蹈作品的藝術特色 [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0,(2):1-6。
[22]蓋光.文藝生態審美論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P438。
[23]慕羽.中國當代舞蹈創作與研究 [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9,P294。
[24]韓蕎冰.舞蹈編導的責任:執著的警醒,冷靜的創新——兼談趙明成長經歷之啟示
[25]慕羽.中國當代舞蹈創作與研究 [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9,P294。
[26][27]韓蕎冰.舞蹈編導的責任:執著的警醒,冷靜的創新——兼談趙明成長經歷之啟示 [J/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146c30100eybw.html,2009-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