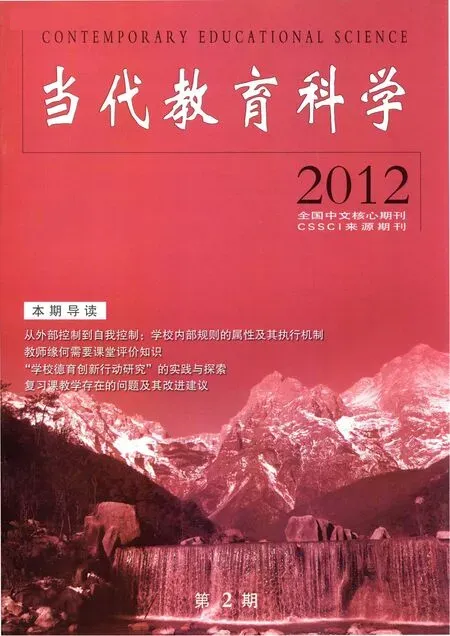以自傳研究促進學校教育改革
● 陳雨亭
以自傳研究促進學校教育改革
● 陳雨亭
自傳研究既可以指面向人內在世界的反思意識,也可以指研究人的內部世界的方法和策略,它旨在自我轉變并借用或創造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逐步逼近或“透視”教師們自己在黑箱中的思維模式從而觸動教師質疑、反思自己在長期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結構,從而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專業自覺和自信,同時自傳研究還為教育提供了一種描繪無法量化的復雜經驗并進而尋找經驗之意義與解放途徑的方法。
自傳研究方法;教師專業發展;新課程改革
在當前的教育改革中,我們經常發現這樣一種有趣的現象:很多人都說自己之所以采取當前的實踐方式,是因為受制約于環境,是因為環境中的其他人沒有改變,所以個人不可能有所作為。還有人說,盡管自己做了很多努力,可就是無法超越自己,努力一段時間之后,回頭一看,幾乎還是在原地踏步。其實,自我轉變是個體內在自我與外在環境有效互動的結果,其中內在自我的狀態最為重要。如果個體的內在自我是流動、開放的,那么它就容易保持內在與外在的及時互動,就會在紛繁復雜的日常教育實踐中,不斷接近教育的真諦,進行他力所能及的堅持與改變。教育自傳能夠促進內在自我的流動與開放。
一、教師轉變需要從自我入手
個體教師選擇的教育立場和方法,都是他自己經歷的結果:在漫長的受教育過程中,一直耳濡目染的他自己把教師們的教育形象已經深深地印在腦海里,小的時候父母與他的互動方式也已經刻畫在骨髓里。這是最為徹底的染缸浸泡式教育與成長方式,個體與他的環境密不可分,是環境的有機組成部分。盡管個體偶爾也會感到窒息,但是他卻很難進行真正的轉變,因為就像咸菜一樣,在咸菜缸里浸泡越久,就越沒有了它本真的味道,也就越難改變成其它味道。
非洲有個諺語說:“除非你知道從哪里來,否則你不可能知道到哪里去。”我從哪里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很容易,也可以很難。說出一個地理名稱是容易的,但是理解這個地理名稱所蘊含著的深刻內涵卻極度困難:我的性格與這個地方有什么關聯?這個地方給了我什么樣的童年生活?我成長中的“關鍵他人”給了我怎樣的影響?……這樣的追問就是自傳研究的開始。
自傳研究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概念,既可以指面向人內在世界的反思意識,也可以指研究人的內部世界的方法和策略。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的有些教育研究人員在存在主義、現象學、意識流文學、精神分析等學科的影響下,開始尋找能夠研究人的內部狀態的方法。威廉·派納構建的存在體驗課程(Currere)就是其中的一種方法,它旨在理解個體在學校中的生活本質和學校在一個人生活中的作用。存在體驗課程是課程(Curriculum)的拉丁詞根,意指沿著跑道奔跑。派納認為它首先是一種自傳的研究方法,“通過它,研究者、教師和學生以能夠引起自我轉變的方式來研究學校知識、生活史和主觀意義之間的關系。”[1]我國自新課程改革以來興起的教師敘事研究以及教學反思撰寫與分享,都可以看做是教師們開始有了進行自傳研究的意識。但是,能夠真正引起自我轉變的自傳研究卻并非十分簡單。
在課堂教學改革中,一直以來我們都有一個難題,那就是盡管老師們進行了很多教學反思研究,但是轉變課堂教學的面貌卻仍然十分艱難。甚至有的學校發明了一些簡單易操作的教學模式,也仍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課堂教學文化。這是因為僅僅聚焦于方法設計得失的反思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什么。
香港學者鄭燕祥曾經提出了學校行動學習循環,如下圖。

本圖中的思維模式是指以前的經驗知識累積而成的認知模式。行動指教師在與環境交往中有意圖的行為。監察是指分析自身的行動意圖是否與后果錯配的過程,通過監察可得出錯配或吻合的主觀判斷。反思是指通過探討自身思維模式來解釋錯配的過程,反思能導致行動設計或思維模式的改變,當遇到類似的或新的情境時,便能做出更“明知”或“有效”的行動。思維模式或行動設計的改變也代表著學習已經發生。[3]
新課程改革以后,老師們盡管經常參加教研活動,也經常參加聽課評課活動,但是為什么課堂教學改革依然十分艱難?從上述行動學習循環圖中,我們可以找到答案。我們的多數聽課、評課、集體備課活動,或者教師的教后反思活動,都屬于單圈學習。就是說,反思活動只是聚焦在行動的方案設計上,然后根據修改了的行動方案,再付諸行動。我們都知道,行動方案的設計是受特定思維模式影響的結果,反思的時候,如果不觸及思維模式,僅僅就事論事,聚焦方案設計的優劣得失,那么再次設計的方案也仍然只是這種特定思維模式的結果,和先前不甚理想的設計屬于同一類型。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不觸及思維模式的反思,只適合處理具體的方案設計問題,而不適合處理轉型問題。
雙圈學習中的“思維模式”,是個體的成長經歷和受教育經歷綜合作用的結果,是潛移默化之間形成的,因此個體很難清醒地意識到它的存在,更不用說對之進行改造了。自傳研究的意義就在這里——旨在自我轉變并借用或創造一些特定的研究方法,逐步逼近或“透視”自己在黑箱中的思維模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自傳研究有助于提升教師們進行思維模式反思的質量。
自我反思與自我理解從來沒有變得像今天這樣重要。在新課程改革以來的十多年里,從課程、教材設計到教師校本專業發展,我們進行了很多嘗試。目前我們遇到的問題已經主要不是外部設計的問題,而是每一個教育相關者自己的“思維模式”如何轉變的問題。威廉·派納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已經指出:“在通過集中注意于外部來理解教育本質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走得足夠遠了。并不是公共世界——課程材料、教學技巧、政策指示——變得不再重要;而是說為了進一步理解它們在教育過程中的作用,我們必須把目光從它們身上轉移開一段時間,開始漫長的、系統的對內部經驗的搜尋。”[4]
二、個人的就是集體的
我們很多關于教師的知識都是匿名的,都是假定某個群體的教師具有某些特征,應該進行某些特定內容和特定形式的學習。這種匿名的知識生產和消費方式使得知識外在于人,難以產生真正的解放作用。
對教師群體特征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對個體教師活生生的經驗的探究。我們教育者眼中的自我、自己視野中的教師和學生形象,都與我們的認知透鏡有關。我們所見世界的色彩取決于我們自己所佩戴的“眼鏡”的色彩。這恰如馬克斯·韋伯所說:“每個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5]或者如愛因斯坦所說:“你能不能觀察到眼前的現象取決于你運用什么樣的理論,理論決定著你到底能夠觀察到什么。”[6]對這些“眼鏡”的研究是個體自我探究的重要部分,但這并不是說這種研究沒有集體的意義。每一個個體都是一個自足的整體,生活在一個群體中的個體由于生活環境、文化遺傳等原因而使得他們共同分享一些榮格所謂的“集體無意識”。默里·斯坦因在論述個體變形的問題時說過:“我們把個體看作是不可或缺的統一整體,而不是一架巨大機器上的齒輪,或共同人性之沙灘上的沙礫。進一步講,在個體變形和集體變化進程之間可以找到重要的類似之處。一旦將個體的進程弄清楚,審視集體進程的模型也就可以建立起來。”[7]
就如當我們在閱讀文學自傳時所發現的,同一代人的內心生活趨于類似:從一部文本到另一部文本,我們感到好像在說同一種東西。同時出生并且經常生活于類似環境中的人面對的完全是相同的問題:很多自傳作者,如盧梭,意識到他們不是“個別情況”,而是具有代表性的個體,他們通過自己的故事,講述的是同代人和他們所屬的社會團體的故事。通過對自傳作品加以比較,可以透過各自的差別發現一種重要的共同本質,尤其在童年和少年敘事之中:看似只與作者相關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組成一種典型敘事。[8]因此,由自傳研究方法獲得的知識一旦超越了個體化的細節,就能為我們提供超越傳記的審視集體狀況的經驗。因為雖然個體的自傳知識表面上看起來非常不同,但是至少在一個群體中其根源是相同的,也就是說“可能存在著基本的結構和過程。這些可能會是人文學科的教育過程的基本結構和過程。”[9]
以促進教師反思與轉變為主要目的的自傳研究,使得教師們能夠“對自身專業生活現狀、教學慣例保持一種批判反省的態度,不斷澄清、質疑自身教學慣例行為背后的預設,信念、思維模式,開啟新的視野,傾聽內在的心聲,引發對教學生活意義的追尋與感悟,努力擺脫‘已成的我’,獲得內在的啟蒙和解決的力量,即哈貝馬斯所說的‘批判反思性的知識’、‘解放的知識’。”[10]自傳研究可以通過講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來進行,但是,講述自己的傳記故事卻未必一定能達成這種期望,因為正如派納所說“如果‘講述我的故事’僅僅是重新刻劃那個已經被別人歡呼存在過(hail into existence)的自我,這樣的話重建就不可能發生。”[11]在這里,他指的是教師們所講過的故事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層次,沒有進入到能引起反思、反省以至到達被忽視、被壓制的經驗層次。我們在很多教師的“教育自傳”中可以發現,講述自己的故事同樣可以像無奈地進行概念式或者經驗總結式研究一樣是為了完成“任務”,同樣可以不觸動自己的內心世界。
在肯定“教育自傳”作為中小學教師的一種研究方法的同時,研究者應該在與教師們進行合作研究或者提供科研的智力支持,引導教師的自傳研究向深層次發展。說到底,如果自傳研究不能觸動教師質疑、反思自己在長期經驗基礎上形成的結構,就沒有太大的意義。教師的自傳敘事不是去敘述那些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別人都司空見慣的故事,而是“要在看似無問題的地方中發現問題,揭示慣常行為背后潛藏著的認知圖式、預定的假設、心照不宣的東西、‘集體無意識’、‘緘默的知識’等等,進而擺脫傳統的禁錮,獲得一種內在的啟蒙和解放的力量,打開新的思考維度和新的探詢方向,增強實踐能力和自我超越的能力。”[12]這樣的研究過程是“過去的我”、“現在的我”以及“想象中的我”之間的對話交流,然后,在“回憶”和“盼望”的過程中,逐漸摧毀堅殼一樣的習慣,獲得新生。
三、自傳研究具有解放的意義
觸動了思維方式的自傳研究,能夠幫助教師們逐漸理解自己,同時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專業自覺和自信,從而可以幫助我們培養這樣一種能力:“在一個有缺陷的社會里,在我們居住的街道上,在我們的學校里,來創造什么應該是、什么可能是的視野。”米勒認為質疑一個“真實的”、穩定的和連貫的自我以及這個自我的文化印跡(cultural scripts),可能是把自傳作為教育探究的一種形式的唯一原因。[13]如果不關注我們自己的意識,不質疑我們自己的文化印跡,我們“就會湮沒在社會表層,我們所看到的就是我們能得到的。 ”[14]
早在20世紀初,杜威曾批評過這樣一種現象:即人們往往毫無思考地拋棄一種技術,輕易地接受另一種技術。要改變這種現象,杜威認為,惟一的辦法就是教師要學會用自己的思想和理智去行動。他強調教師反思自己的實踐并將自己的觀察溶入新的教育理論的重要性。[15]“學會用自己的思想和理智去行動”的過程就是進行自傳研究、獲得解放的過程。
但是自傳研究可能會受到一些主張“實證”研究的學者的批評,其中最嚴厲的是批評這種研究缺乏規范性。其實,自傳研究只是課程研究領域的“復雜的會話”中的一種話語,它與其它話語一起構成了課程研究領域的合唱。派納曾經指出,“我們課程學者為自由創造所付出的代價是高水平的過度思索。也許,這是一種必要的付出。與教育心理學的規范以及它的科學地位和享有的相當威望相比,我們更喜歡探究那些不僅沒有解決而且也沒有描述清楚的智慧表現領域,包括思維領域。”[16]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自傳研究為教育提供了一種描繪無法量化的復雜經驗并進而尋找經驗之意義與解放途徑的方法。
[1]陳雨亭.如何研究學校教育情境中的自我[J].全球教育展望,2009,(5).
[2][3]鄭燕祥.教育領導與改革新范式[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33.
[4]Pinar,William F.(1994).Autobiography,politics and sexuality:Essays in curriculum theory 1972-1992.New York:Peter Lang.16-17.
[5][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M].劉精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3.
[6]轉孟慶茂.教育科學研究方法[M].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1.162.
[7]默里·斯坦因.變形:自性的顯現[M].喻陽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15.
[8][法]菲利浦·勒熱訥.自傳契約[M].楊國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40-41.
[9]Pinar,William (2000).Currere:Toward Reconceptualization.In William Pinar(ed).Curriculum Studies:The Reconceptualization.New York: Educator’s International Press.411.
[10]柳夕浪.建構積極的“教學自我”——教師研究的價值取向[J].教育研究與實驗,2003,(3).
[11][13]Pinar,William(2005).Preface:What Should Be and What Might Be.In Janet Miller.Sounds of Silence Breaking:Women,Autobiography,Curriculum.New York:Peter Lang.XⅢ.Ⅳ
[12]柳夕浪.教師需要什么樣的教育研究[M].教育研究與實驗,2001,(3).
[14]Pinar,William(2004).What is Curriculum TheoryMah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57-258.
[15]陳振華.關于教師研究及其方法論問題[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4,(1).
[16][美]威廉·F·派納等.理解課程[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881.
陳雨亭/天津教育科學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學博士
(責任編輯:曾慶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