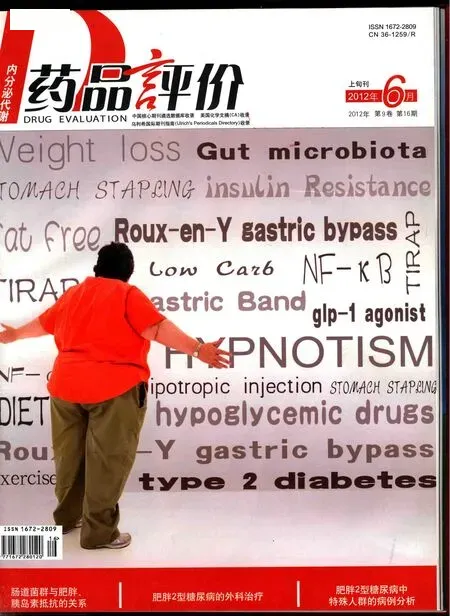腸道菌群與肥胖、胰島素抵抗的關系
中山大學附屬二院內分泌科 李焱 梁綺君
肥胖以及2型糖尿病已成為當今世界重要的社會和健康問題。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發生與多種遺傳和環境因素有關,其中人體腸道菌群與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發生有著密切的關系。
腸道菌群(gut microbiota)為定植在人體消化道內的微生物,數量眾多,種類復雜。正常成人的腸道菌群總重量約1~2kg,數量至少達1014個,是人體細胞的10倍,包含的基因數量是人類基因數量的150倍。主要位于大腸。根據細菌16S rRNA序列分類,含有細菌500~1000種,主要包括9個門,即厚壁菌門(Firmicutes)、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放線菌門(Actinobacteria)、梭桿菌門(Fusobacteria)、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疣微菌門(Verrucomicrobia)、藍藻菌門(Cyanobacteria)、螺旋體門(Spirochaeates)、VadinBE97菌門和另外一種古菌——史氏甲烷短桿菌(Methanobrevibacter smithii)。其中大部分屬于擬桿菌門(G-菌)或厚壁菌門(G+菌)(共約占90%)。
腸道菌群與能量代謝
與正常小鼠相比,完全清除腸道菌群后的小鼠攝食量增多,但體內脂含量卻明顯減少;植入正常小鼠腸道菌群后,攝食量減少,體脂含量卻明顯增加。由于無菌小鼠的耗氧率明顯減少,提示體脂的減少并不是由于能量的消耗增加所致,而是因為能量攝入減少。腸道菌群可通過多種機制參與宿主的能量代謝:①大腸中的腸道菌群能將不被小腸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如膳食纖維、抗性淀粉等)發酵,使其降解成短鏈脂肪酸,為宿主提供能量。人類從膳食中獲取的能量有10%可歸因于腸道菌群的這種作用。②腸道菌群的產物(如甲烷、短鏈脂肪酸)能減慢腸道的蠕動,延長腸道的通過時間,使腸道營養更充分地吸收。③腸道菌群通過上調肝臟碳水化合物反應元件結合蛋白(carbohydrate responsiv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hREBP)和固醇調節元件結合蛋白-1(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1,SREBP-1)mRNA的表達,誘導脂肪合成的關鍵酶乙酰COA羧化酶(acetyl-CoA carboxylase,ACC)和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FAS),促進肝臟甘油三酯的合成。④腸道菌群下調腸上皮細胞產生的禁食誘導脂肪細胞因子(fasting-induced adipose factor,FIAF)的表達。FIAF是脂蛋白酯酶(lipoprotein lipase,LPL)的抑制因子,LPL能催化脂肪酸從脂蛋白上釋放進入脂肪組織中進行甘油三酯的合成。因此,腸道菌群作為重要的環境因素參與宿主脂肪存儲的調控,腸道細菌的失調可能是促進肥胖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
腸道菌群與肥胖的發生
與正常小鼠相比,肥胖小鼠腸道中擬桿菌門細菌的含量下降,而厚壁菌門細菌的比例相對升高。與正常人相比,肥胖者糞便中擬桿菌門細菌的比例明顯減少,厚壁菌門細菌比例增高。經過52周節食減肥后,隨著體重的減輕,腸道群菌結構趨向接近于非肥胖者的腸道菌群結構,即擬桿菌門細菌的比例較前升高,厚壁菌門細菌比例較前下降,而且體重的減輕與腸道擬桿菌門細菌比例的變化呈正相關。但并非所有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結論。
此外,動物及人體實驗均顯示肥胖者腸道菌群表達更多有利于攝取能量的基因,如感受和降解膳食纖維的基因、轉運單糖和多糖的基因、單糖和多糖細胞內代謝的相關基因等。例如肥胖小鼠發酵膳食纖維的能力更強,腸道中能產生更多的單鏈脂肪酸。
向無菌小鼠分別植入肥胖小鼠和非肥胖小鼠的腸道菌群,發現植入肥胖小鼠腸道菌群的小鼠體脂含量較植入非肥胖小鼠腸道菌群的小鼠明顯升高。提示腸道菌群的變化可能參與了肥胖的發生。與正常體重兒童相比,超重/肥胖兒童在嬰兒期就存在著腸道菌群結構的差異,說明腸道菌群的不同出現在體重變化之前。
腸道菌群在機體出生時便開始形成,隨后幾天中逐步完善。最先定植的細菌能夠調節宿主腸道上皮細胞基因的表達,創造一個有利于它們定植的環境,同時抑制隨后進入這一環境的細菌生長。因此,最初定植的菌群與宿主成年后的穩定菌群模式密切相關。嬰兒的腸道菌群受母體的胃腸道、陰道、皮膚的菌群影響。母乳中含有豐富的雙歧桿菌,母乳喂養的嬰兒日后發生超重和肥胖的機率減少13%~22%,母乳喂養的時間與超重的發生率成負相關。此外,飲食結構是影響腸道菌群的重要因素,長期高脂飲食可減少腸道中的雙歧桿菌以及一些擬桿菌門細菌。
綜上所述,腸道菌群參與了宿主的能量代謝;肥胖者與非肥胖者的腸道菌群存在差異;腸道菌群可能參與了肥胖的發生。但不同的腸道菌群是如何參與肥胖的發生,其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腸道菌群與胰島素抵抗
慢性炎癥是胰島素抵抗的一個重要的發病機制,炎癥過程產生的炎癥因子影響胰島素的信號通路,引起胰島素抵抗。長期高脂飲食導致能量過剩引起肥胖,脂肪組織分泌多種炎癥因子引起低度炎癥;高脂飲食引起游離脂肪酸水平升高,增加炎癥因子的表達增多;近年的研究發現高脂飲食可能與腸道菌群相互作用導致炎癥,進而引起胰島素抵抗。
1.腸道菌群變化增加腸道LPS吸收,誘導慢性炎癥
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是存在于革蘭陰性細菌(G-菌)外膜的一種內毒素,細菌破解后被釋放,是G-菌感染時激活機體固有免疫系統,啟動炎癥反應的主要成分。LPS進入血循環后,LPS結合蛋白(LBP)促進LPS解聚成單體,并將其轉運到單核巨噬細胞膜上,促使LPS與CD14結合。CD14再協助將LPS轉運至其識別受體——Toll樣受體4(TLR4)/髓樣分化蛋白-2(MD-2)復合物(TLR4/MD-2),隨即激活TLR4。通過Toll/IL-1受體(TIR)結構域招募含TIR結構域的銜接蛋白(TIRAP),激活髓樣分化分子88(MyD88)依賴途徑,以及招募TRIF(含TIR區域誘導的干擾素活化子)-相關接頭分子(TRAM),激活MyD88非依賴途徑。最終引起一系列的炎癥過程:①激活IκB激酶(IκB kinases,IKKs),使IκB磷酸化而被降解,NF-κB得以活化;②激活三條MAPK途徑——ERK、JNK/SAPK、p38MAPK,在下游可激活另一轉錄因子——激活蛋白-1(AP-1);③磷酸化干擾素調節因子3(IRF3)使其活化。轉錄因子NF-κB、AP-1和IRF3被激活后,進入細胞核內與DNA結合,啟動了1型干擾素(IFN-α和IFN-β)、促炎癥細胞因子如TNF-α、IL-1、IL-6、IL-12等的表達,引起機體局部或全身的一系列非特異性炎癥反應。
除單核巨噬細胞外,肝細胞、脂肪細胞和骨骼肌細胞也表達LPS的受體。LPS可通過激活這些細胞中的IKK,誘導IκB磷酸化,進而促進NF-κB活化,上調TNF-α、IL-6等炎癥因子的表達,抑制IR、IRS的酪氨酸磷酸化,干擾胰島素信號傳導,引起胰島素抵抗。
2.高脂飲食改變腸道菌群,增加LPS吸收
人體腸道中含有大量的G-菌,共可產生超過1g的LPS,是非感染狀態下血中LPS的主要來源,對于維持機體的非特異性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健康人在一次進食富含飽和脂肪酸的食物30min后,其血漿LPS水平即開始升高。長期高脂飲食后血中的LPS水平明顯升高。這種由高脂飲食引起升高的內毒素水平遠低于感染性休克時的內毒素水平(約為十到五十分之一),所以也被稱為代謝性內毒素血癥(metabolic endotoxemia)。但這種長期低水平的LPS足以增加肝臟、骨髂肌、內臟脂肪和皮下脂肪炎癥因子的表達,以及引起胰島素抵抗。
高脂飲食引起LPS水平升高的機制,尚不完全明確。高脂飲食可能通過以下機制起作用:①高脂飲食改變了腸道菌群的結構,使G+/G-菌的比例降低,G-菌比例相對升高;②高脂飲食后腸內的雙歧桿菌明顯減少,而雙歧桿菌有降低腸內內毒素水平和保護腸道黏膜屏障的作用;③高脂飲食能抑制腸道上皮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增加了腸道的通透性,促進LPS的吸收;④高脂飲食使腸上皮細胞合成的乳糜顆粒增多,促進LPS的吸收和運轉到靶組織。
因此,高脂飲食可能通過腸道菌群引起代謝性內毒素血癥,進而引起低度炎癥反應和胰島素抵抗。
腸道細菌未來可能成為肥胖和胰島素抵抗的治療靶點
益生菌(probiotics)是指改善宿主微生態平衡而發揮有益作用,達到提高宿主健康水平和健康狀態的活菌制劑及其代謝產物,如乳酸菌、雙歧桿菌等。益生元(prebiotics)是指能夠選擇性地刺激腸內一種或幾種有益菌生長繁殖,而且不被宿主消化的物質,如雙歧因子、一些寡聚糖等。動物實驗已顯示某些益生菌、益生元能降低體內LPS水平、降低炎癥水平、改善葡萄糖耐量。小樣本量的人體研究也提示服用益生元、益生菌可降低炎癥水平。糾正異常的腸道細菌未來可能成為預防或治療肥胖和胰島素抵抗的靶點。
小 結
腸道菌群參與能量物質和非特異性免疫功能的調節,長期高脂飲食是改變腸道菌群的重要因素;腸道菌群失調增加LPS吸收,參與肥胖和胰島素抵抗的發生;糾正異常的腸道菌群可能成為預防和治療肥胖和胰島素抵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