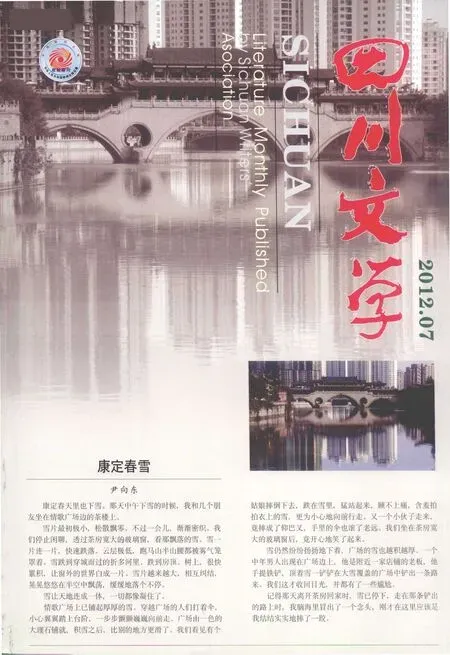風流總被風吹雨打去
□陳魯民
當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流傳著這樣幾句名言:“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據說是錢鐘書說的,這也確實符合他恃才傲物的性格,看看他在《圍城》里刻畫的那些人物,刻薄形象而又一針見血,就不難想象,這是典型的錢氏語言。后來,楊絳先生出來辟謠,說此論的版權非錢鐘書所有。其實這已無關緊要,無論出自誰口,這幾句話當時在西南聯大的流行看來是不爭事實。
葉公超太懶
先說這“葉公超太懶”,也實在算不上冤枉他,他的懶,有目共睹,“鐵證”如山,他自己不否認,學生、同事的回憶也都印證了這一點。
作為教授,他上課極懶。他的學生趙蘿蕤回憶葉公超上課:“作為老師,我猜他不怎么備課,他只是憑自己的才學信口開河,說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藝理論知識多得很,用十輛卡車也裝不完的。”學生季羨林回憶說:葉公超講英文,幾乎從不講解,一上堂,就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他就讓學生依次朗讀下去,一直到下課。有人偶爾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就斷喝一聲:“查字典去!”學生溫梓川回憶說:他“喜歡打牌,如果打了一夜牌,則上課照例不講書,只叫同學口試,或聽同學讀一章節。”他上課經常遲到,有時遲達十五分鐘之多。所以,學生楊振寧對他印象不佳:他對學生不感興趣,教授的英文極枯燥,有時甚至要作弄我們,“我不記得從他那里學到什么。”
他還是系主任,恐怕是西南聯大最懶的系主任。他的同事柳無忌說:“這時的西南聯大尚在草創階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錯綜復雜,但我們的外文系卻相安無事,那是由于系主任公超的讓教授各自為學,無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記憶我們是否開過系務會議。”學生許淵沖記,我去外文系選課時,系主任葉先生坐在那里,吳宓先生站在他旁邊,替他審查學生的選課單,他卻動也不動,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簽一個,只是蓋個圖章而已,真是夠懶的了。吳宓也經常在日記中記,今日“陪(助、偕)超”干某某事,因為葉公超的公事私事、瑣事要事,都支使吳宓去干。
懶得動筆,是他的又一特色。他肚子里的貨色其實不少,畢竟留學多年,師從不少名家,但他卻沒有好好總結挖掘,可惜了那么多學問。胡適曾要他和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合譯《莎士比亞全集》,結果他一個字也沒有翻,卻讓英語遠不如他的梁實秋一個人譯完了。他也從不記筆記,不愛照相,還常宣傳一個觀點:一個人如果有成就,別人當然不會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著收集照片、記日記了。本人雖不寫歷史,但愿意創造歷史。話雖這么說,他還是寫了《介紹中國》、《中國古代文化生活》、《英國文學中之社會原動力》、《葉公超散文集》等著作,說他懶,是說以他的學問和素養,本可寫出更多有價值的東西來。
他后來棄教從政,當了幾年國民黨的外交部長,仍積習難改,以懶著稱。他曾一本正經地對部下說:“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來了。”外交官考試,他是典試委員,復審時不看考卷,只給及格者都加一分,不及格者減一分。他的邏輯是這樣干脆,拉大距離,便于取舍。他不喜開會,懶得出席各種應酬,逢年過節也不去走動,為此得罪過不少國民黨大佬。他當外交部長那幾年,國民黨的外交形勢江河日下,四面楚歌,這固然是大勢所趨,其中也多少與他這個外交部長的懶散不作為有關。
葉公超去世后,好友葉明勛說:提起李白,除了詩忘不掉他的酒;提起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愛情;提起葉公超,除了他的風流豐采,忘不掉他的脾氣。這脾氣就包括傲、怪、擰、懶。不過他的英語確實好,典雅、純正、自然、唯美,國內無人可及。上世紀50年代,有人問自視甚高的朱光潛,國人里誰英文最好?朱光潛不假思索說:“葉公超。”能取得這樣成就,如非勤奮,那即天才。天才懶一點,即便上帝也會原諒他。
吳宓太笨
說“吳宓太笨”,不妨先看看同是他學生的楊絳筆下的形象吧:“我對吳宓先生崇敬的同時,覺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師。我聽到同學說他‘傻得可愛’,我只覺得他老實得可憐。當時吳先生剛出版了他的《詩集》,同班同學借口研究典故,追問每一首詩的本事。有的他樂意說,有的不愿說。可是他像個不設防城市,一攻就倒,問什么,說什么,連他意中人的小名兒都說出來。吳宓先生有個滑稽的表情。他自覺失言,就像頑童自知干了壞事那樣,惶恐地伸伸舌頭。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馴,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別人知道的。吳先生說了出來,立即惶恐地伸伸舌頭。吳宓先生成了眾口談笑的話柄——他早已是眾口談笑的話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剝削,上當受騙。”(《吳宓先生與錢鍾書》)作為堂堂名牌大學教授,被學生“戲弄”成這個樣子,尊嚴全無,還有比這更笨的嗎?
即便錢鐘書沒說過“吳宓太笨”,但在他眼里的吳宓比笨也強不到哪里去,他這樣描述老師:“吳宓從來就是一位喜歡不惜筆墨、吐盡肝腸的自傳體作家。他不斷地鞭撻自己,當眾洗臟衣服,對讀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顆血淋淋的心。然而,觀眾未必領他的情,大都報之以譏笑。所以,他實際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不遺余力地表演,卻被觀眾譏笑,不是笨又當何解?
“笨”,有時也是老實的代名詞。據歷史學家錢穆回憶,在南岳時,宿舍緊張,吳宓、沈有鼎、聞一多、錢穆四人同住一室。每天晚上,吳宓都為明日上課抄寫筆記寫綱要,逐條寫,又合并,有增加,寫好后,用紅筆加以勾勒。次日,吳宓一早最先起床,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中,拿出昨晚備課所寫條目,反復誦讀。而當時有些聰明瀟灑的教授,從不備課,想到哪里講到哪里,反正肚子里有貨,吳宓曾在日記里痛批他們“不務正業”,服役于各種社會機關,“惟多得金錢之為務”,講課卻潦草敷衍,不接見學生,不審閱作業,甚至連評閱新生考卷都不到場。像吳宓這樣已經是名教授了,又逢戰亂,備課還這樣下笨功夫的,委實不多。因而吳宓給學生們留下的印象是“認真、負責、一絲不茍,學術嚴謹”,“上課像劃船的奴隸那樣賣勁”。
日常生活中的隨意,缺乏算計,接人待物中的不設防,沒有城府,也會被人視為笨,吳宓便是此中人物。他經常借錢給人,卻往往忘記索還,偶爾記在日記里,也不好意思去要。他心血來潮,在美國花大價錢買了一套《莎士比亞研究文集》,結果發現用處不大,且搬運麻煩,最后幾當廢品處理。一女教師給她織了一雙襪子,他一激動給了100元錢,按市價可買一箱子襪子。“文革”后期,他補發大筆工資,有人眼紅,就偷他的書和日記,又反過來高價賣給他,他越買,偷的人就越多,未幾,工資便所剩無幾。她的妹妹接他回陜西老家時,搜遍全屋,只發現席子下幾元錢。
當然,大伙最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在婚姻戀愛上的笨不可及。他曾狂熱地追求時髦女性毛彥文,煞費苦心,癡情不改,鬧得全國都知道,但卻因為優柔寡斷,瞻前顧后,患得患失,屢失戰機,以至于每每碰壁,是情場上典型的笨伯。最后,33歲的毛彥文寧肯選擇66歲高齡的過氣政治家熊希齡,也不選擇年輕而當齡的教授吳宓,因為她太清楚這位“闖進瓷器店的笨驢”的德性和本事了。毛彥文結婚之日,吳宓深陷絕望悲苦之中,作詩《吳宓先生之煩惱》,以排遣內心的隱痛和惆悵:“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離婚不畏圣賢譏,金錢名譽何足云。”詩文傳開,又成世人笑柄。
陳福田太俗
陳福田,外國語言學家、西洋小說史專家。1897年出生于夏威夷,哈佛大學教育學碩士。曾任美國檀香山明倫學校教師,美國波士頓中華青年會干事。1923年起執教于清華大學。曾任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主任、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主任。1948年離開中國移居夏威夷,1956年病逝。
“陳福田太俗”,主要表現在著述和講課上。他的外語很好,是童子功,這沒有話說,可是他著作不算多,影響也不大,計有《西洋小說》、《大一英文》幾種。其講課水平也不敢恭維,講課平鋪直敘,照本宣科,中規中矩,用當年他的學生許國璋的話來說:陳福田上課缺乏感染力,而錢鐘書雖然年輕,還是副教授,但講課一點不比葉公超、吳宓、陳福田這些資深教授遜色。的確,錢鐘書講課,繪聲繪色,語言幽默,旁征博引,天馬行空,很受學生歡迎,因而他說“陳福田太俗”也不是沒有道理。
錢鐘書瞧不上陳福田,其實早在他讀清華大學時就有過“前科”。1933年,錢鐘書自清華外文系畢業,當時清華研究院剛成立不久,校長親自告訴他要破格錄取他留校,陳福田、吳宓等教授也想挽留他,都去做他的工作,但均未成功。后來,陳福田說:“在清華,我們都希望錢鐘書進研究院,繼續研究英國文學,為我們新成立的西洋文學研究所增加幾分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絕了。他對人家說:‘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這話未免有點過分了。”
“陳福田太俗”的話傳到陳福田的耳朵里,他自然很不高興,也反唇相譏說:“錢的學問還欠火候,只能當副教授”。據吳宓日記載:陳福田還和葉公超一起對校長建議,不聘錢鐘書。對后起之秀不夠寬容,多少有些嫉賢妒能,也是他“俗”的一面。而吳宓則要豁達、厚道得多,雖然錢鐘書對他也頗不恭,但他卻對年輕的錢鐘書頗為期許,對他的自負盛氣也最能原諒。他對錢鐘書拒絕進入清華研究院并沒有什么不高興,他說:“學問和學位的修取是兩回事。以錢鐘書的才華,他根本不需要碩士學位。當然,他還年輕,瞧不起清華大學的現有西洋文學教授也未嘗不可。”
“陳福田太俗”,還有一層意思,在一心鉆研學問,幾乎沒有別的愛好的錢鐘書眼里,陳福田的愛好豐富,多才多藝,也是一種俗。陳福田喜歡音樂,常參加校、系的文藝演出。1926年5月10日,在清華大禮堂舉行音樂大會,清華教職員歌唱團也參加了演出,他和徐國祥教授等四人的小合唱,就頗見水平,很受歡迎。
他還會拍電影。l946年聯大學生復員,10月初的一個星期日,師生們一起乘著幾輛大卡車回到清華園,在清華園的牌坊前舉行了抗戰勝利后的返校儀式,當時的紀錄片就是陳福田拍的。
他還是體育愛好者,身體健壯,在國外讀書時,他就是校壘球隊主力。在清華和西南聯大期間,他曾擔任校男壘、女壘隊的教練,多次率隊外出比賽,捧過不少獎杯。
可能沒人想到,他還會種菜。在西南聯大時期,他和陳岱孫、金岳霖、李繼侗等教授,開辟了一個菜園子,陳福田寫信給檀香山的美國親屬,從美國郵寄來菜子。課余閑暇,幾個教授一起澆水、施肥、除蟲、拔草。
俗就俗吧,只要自己活得高興,大雅大俗的陳福田并不在意錢鐘書的譏諷,依然在清華外語系兢兢業業任教25年,桃李滿天下,譽滿教育界,這人生也夠輝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