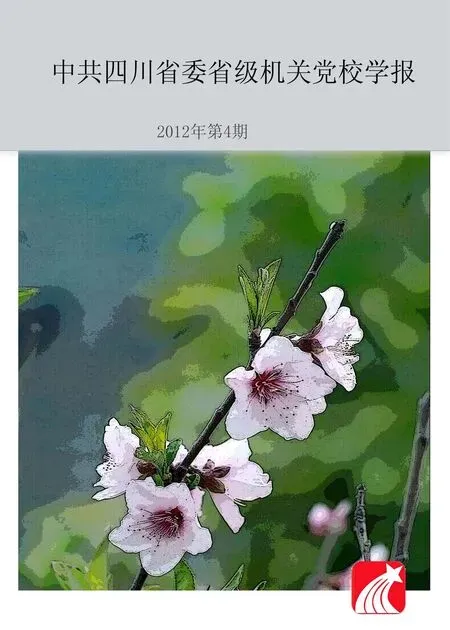比較視野下的“國民”概念
——兼議近代國民形成的條件
田雪梅
比較視野下的“國民”概念
——兼議近代國民形成的條件
田雪梅
“臣民”、“公民”、“市民”和“國民”這樣的語言體系,是與一定政治形態相適應的人的存在形態,是對政治現實的典型反映。“臣民”既無權利意識又無國家意識,是與君主專制制度以及絕對主義國家相適應的國家成員資格。“市民”是以自由貿易和經濟利益為根本、掌握了大量財富并最終與國家主權相結合的群體。公民是與近代國民國家建立后民主制度發展、與公民權、參與公共生活相聯系的范疇,統合了市民、臣民和選民的三種角色,是在參與治理過程中具有政治權利的政治成員資格。國民是與民族、國家相聯系的范疇,具有對統一主權國家的認同,具有公民權。國民權利、國家歸屬和國家認同構成近代國民的三大支柱,同時具備民族特質和公民特質,則是國民的內在屬性。衡量近代國民形成的標志,最重要的是兩個條件,一是“去地域化”,二是“去奴仆化”。
國民權利;國家歸屬;國家認同;民族特質;公民特質;臣民;公民;市民;國民
“臣民”、“公民”、“市民”和“國民”這樣的語言體系,是對政治現實的典型反映,是與一定政治形態相適應的人的存在形態。由于近年來現代國家理論的興起,一些研究在“臣民”、“市民”和“國民”等詞的使用上涵義較為混亂,從而導致了一些認識上的誤解。對這些概念進行相關界定和比較,既是理解政治體系變遷的鑰匙,也是澄清目前研究中混亂的需要。
一、“既無國家意識又無權利意識”的“臣民”
何為“臣民”?鄧恩曾借用查理一世的話說,“臣民與主權者是完全不同的存在”〔1〕。在國家產生前的部落時代,每個人是部落民,或稱“族民”。國家產生之后,血緣關系退居次要位置,社會共同體轉變為地域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與君主專制制度以及絕對主義國家相適應的國家成員稱為“臣民”,又稱“子民”或“庶民”。
臣民的首要特征是君臣關系的不平等。“臣”即“臣服”、“臣屬”,意味著被動地服從和受統治,“草民”、“蟻民”等蔑稱即顯此意。臣民社會本質上是君臣關系的共同體,是君的絕對權力和臣民的絕對從屬與服從,是君的高高在上和臣民的屈辱地位。臣民沒有獨立地位和自主權利,只有納稅、供養官家的義務,只能服從和效忠于君主和朝廷。青年馬克思曾尖銳地批判過封建專制制度的“非人”性質,指出其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即使在最開明的統治下,臣民仍然是純粹的被統治者,沒有平等身份,必須聽命于專制君主的意志。
臣民的第二個特征是沒有主動性。對臣民而言,國家權力表現為外在權力。第一,國家權力不屬于他們,對國家事務無權參與;第二,國家權力服務于統治集團的利益,他們總是犧牲者、被壓迫者、被剝奪者。因此,臣民對國家必然是疏遠、冷漠的心態。歷來的朝代更迭,于己而言,只有主子殘暴與賢明的區別,臣民的身份是不變的。王朝的興衰沉浮,只是百姓茶余飯后的談資,與自己的生存狀態沒有多大聯系。他們只關心自己,不關心國家,只會消極服從,不會積極參與。他們所忠誠的對象,只是自己所服從的主子,所認同的,只是自己所居住的狹隘的宗族共同體。
在“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專制時代,臣民的這種地位也被普遍內化為臣民意識,即將專制統治者對臣民的蔑視和侮辱內化為民眾自己的觀念,使他們認同這種不平等,安于被壓迫的屈辱地位,習慣于單方面的服從和效忠。沒有獨立意識,沒有平等要求,“寧做太平犬,不做亂離人”,這是臣民心態的寫照。順從、忠誠、忍耐是臣民的美德。消極被動、逆來順受、怯懦畏縮、謹言慎行,不知尊嚴為何物,是臣民性格的特征。*本概念借用了叢日云“從臣民到公民”的諸多思想。叢日云.中國公民讀本〔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臣民意識、臣民性格和臣民道德共同構成了臣民文化。用阿爾蒙德的解釋來說,就是政治體系的成員對政治體系的角色、結構、權威、規范以及自己在體系輸出方面的責任等有較明確的認知、情感和價值取向,而對于政治體系輸出方面的取向以及社會成員作為政治參與者的自我取向卻非常低,集權型政治體系中彌漫的都是這種臣屬性政治文化〔2〕。這是一種具有明顯奴性特征的政治文化,它往往是集權政治的心理基礎。
二、“以利益為根本并最終與國家主權相結合”的“市民”
市民在中國原是一個中性概念,并不包含價值判斷的因素。但在歐洲,“市民”是一個很復雜的學術概念,它和以后的“公民”等是一組吊詭的概念,包含了社會歷史演變所累積的多層意義。早期的市民身份包括:過城市集體生活并依賴于商品交換的人;為了擺脫奴役和迫害而進入城市自治的自由人;在社會中平等相處的人;為了爭取經濟權利而不惜暴力的人。〔3〕緣于城市,一切為了自身的商業資本、經濟利益和交往自由是市民行動的本質內容。所以“市民”概念與“資產階級”相關。多數情況下,城市市民用金錢向封建領主贖買城市的自由,并通過同封建領主訂立“憲章”或特許狀等形式加以鞏固。因此,市民階級本身不僅僅是在城市發展中掌握巨大財富的階層,還包含有政治權利的意義。城市市民通過集體斗爭獲取城市自治權力的行為實踐,增強了市民個體對城市公共權威的認同,這種對抽象的公共權威的順服,為國民國家形成奠定了重要歷史前提。這種理性主義政治文化的發展,也從理論上規定了近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思想框架。〔4〕
市民遵循自由主義和經濟交往的邏輯,把國家視為保障自由市場有效運行的工具。對于市民來講,個人自由是本源性價值,國家是保障性工具,憲政的任務是限制國家權力的擴張。黑格爾說,市民“都把本身利益當作自己的目的”〔5〕。一旦國家無法保障個人自由或者個人自由無須國家這種工具來保障,市民必將毅然棄之。這樣,市民的物質利益與公共權力結合起來,財產保障成為政治參與的先決條件,這兩點成為市民階層進入并支持國家的基礎。產生國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大量的直接向國家納稅,同時又有參與國家事務愿望的那種人,就是納稅的第三等級。……民主的動力的確應該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國家的納稅者。〔6〕藉此,擁有財產但又服從國家統治的市民角色逐漸轉變為“公民”,“公民”概念(英文citizen既是“市民”又是“公民”)開始成為18世紀后期的統一使用詞匯。
綜上所述,所謂市民,是在12世紀后西歐城市復蘇、商業發展后出現的以自由貿易和經濟利益為根本、掌握了大量財富并最終與國家主權相結合的群體。佐伯啟思說,由私人權利出發,追求自由、民主主義及博愛和平的民眾,我想稱他們為“市民”(civil)……由于“civil”是指追求個人權利、個人利益的近代“市民”,又可稱其為“私民”。“市民意識”(civil mind)提倡近代的個人權利,他們常常與國家產生對立,正如“civil”一詞,它意味著禮貌和格調。〔7〕以利己之心為行動原理,“追求個人權利和個人利益”、保持與“國家的對立”,這便是政治學意義上的市民。他們按照自由主義原則進入到最弱意義上的政治國家,形成理性選擇的公民性格。從這個意義上講,市民是公民的前身,為公民產生做了最充分的準備。
當下媒體廣泛使用的市民一詞,已與歷史變遷后之概念相去甚遠。不如說又回歸到其最初的本義——“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一個沒有價值色彩的中性詞語。
三、“與公民權相聯系參與公共生活”的“公民”
古希臘強調公民的選民特權、古羅馬強調臣民和市民服從法律構成古典公民的基本雛形,雖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但這種角色的意蘊在漫長的中世紀被完整地封存起來,經過中世紀末期之后幾百年的實踐以及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觀念萌動,公民獲得了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全部資源支持,在法國大革命后以法律形式完全確立了現代公民的角色形態。
17世紀中葉英國平等派向議會提交的《人民公約》,是歷史上最早以公民資格作為政治綱領的文件,要求凡是不依賴于別人生存的人都應有選舉權。此后,發揮選民角色功能作為政治權利提升的標志。法國大革命中《人與公民權利宣言》中的公民成為一個承載著政治和法律的概念,不僅是作為積極參與代議選舉的選民,而且是指人在法律上所指稱的地位。普選權成為衡量公民資格的重要指標。選民成為現代公民角色的主要承擔者和表達方式,參與選舉和投票是公民權利和義務的集中體現。公民概念由此具有了普遍的自由、平等、獨立、尊嚴和尊重等多重意義。公民就是“一個在人民參與自我治理的過程中具有政治權利的人”〔8〕,其中最主要的政治權利是作為選民平等參與選舉和投票的權利。法國大革命后,各國憲法確立了公民角色和公民資格,形成了公民-國家的權利義務模式。18世紀中后期,公民角色開始走下特權的神圣殿堂,逐漸泛化為普通民眾受到尊重和捍衛尊嚴的代稱。普通民眾通過斗爭獲得平等參與政治的合法權利,將自身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平等高度。公民成為西方近代最有活力的社會角色。在這個過程中,公民統合了市民、臣民和選民的三種角色,自由主義原則、國家主權原則、民主共和原則以及主權在民的觀念都整合為國民國家的基本原則,公民就是與這種國家形態相適應的身份存在。它強調了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公民是與近代國民國家建立后民主制度發展相聯系的范疇,具有個人的獨立和尊嚴。這種身份取得是無條件的,與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無關,代表一種平等的政治地位。
第二,公民是與公民權相聯系的范疇,公民權制度,是現代國家的一項基本制度,國家是所有具有公民權的人的聯合。這些權利,18世紀主要是諸如財產、個人自由和正義的必要權利;19世紀主要是政治權利,包括參與政治權力運作的權利;20世紀還包括強調經濟與社會保障的公民權利。〔9〕
第三,公民是與參與公共生活相聯系的范疇。公民既是治理者也是被治理者,這要求公民具有自立、裁決和忠誠的素質,責任感和參與意識是衡量公民的重要因素。佐伯啟思將“civic”視為追求共同體中公共事業和共同利益發展的人,他們不把國家與私生活視為對立的兩面。這種對公共事業與國家事業懷有義務的觀念,重視勇氣與名譽的古老美德被他稱為“市民精神”(civic sprit)。
第四,公民還是與多樣性、異質性相聯系的范疇,意味著對異質性的容納和包容而非排斥。阿倫特認為,公共性要求人們思維的多樣性:“正是因為每個人站在不同的立場進行思考,才認為每個人的看法、想法具有意義。這才是真正的公共生活(pubil life)。”〔10〕根據這個觀點,在只有一種觀點橫行的時候,已找不到公共的空間。這樣空間下的人的生存狀態,當然不是公民。阿爾蒙德也指出,公民文化的主體是公民,與臣民文化相比較,公民文化更強調公民廣泛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感、能力和主體性地位等。強調政治輸入程序里的個體參與,是對高效政府工作的最好支持,也是最好的監督。
日語中的公民,原指“律令制國家之民”。作為“citoyen”的譯語,本可以在國民的意義上使用公民一詞。但在明治憲法第二章“臣民權利義務”中,一般國民被規定為“臣民”,公民一詞就主要使用于地方自治體方面了。比如二戰前就規定公民一詞的使用情況,“在地方居住兩年以上者叫公民,擁有選舉權”,“公民可以在地方公職上就業”。1931年,中學設立的“公民科目”,講授的是憲政自治的基礎素養。地方居民從此開始被冠以帶有國民含義的公民涵義。
四、“既有國家意識又有權利意識”的“國民”
霍布斯鮑姆曾感嘆道,假若不對“民族”這個單詞及其衍生的有關詞匯有所了解,我們幾乎無法對近兩個世紀的人類歷史做出解釋。
“國民”(nation)是與“國家”、“民族”相關的概念。在歐洲,作為近代現象出現的nation,既是民族,又是國民;nation state,既是民族國家,又是國民國家。但是,國民并不等于民族。*關于“國民”和“民族”的區別和關系,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已經有眾多學術成果問世。這里只做最簡單的區分,重點闡述“國民”的含義。民族原本只有自然的文化的屬性,按照黑格爾的說法,“nation”來自于nasci(出身)的拉丁文natio。最初概念指的是與擁有公民權的“羅馬人”相區別的帝國內部眾多的“種族”或者“部落”,以及居住在羅馬周邊、尚未擁有作為共同體價值體現的國家(civitas)未開化的人群,其含義大致與英語“人種”(race)的含義相近。中世紀的“natio”一詞表示因出身地不同而相互區別的大學生團體,或者宗教公會成員的地域歸屬,“nation”原本的意義已不復存在。
當革命埋葬了專制主義、建立起近代國家的時候,為了擯棄專制君主家產的私人特性,強化作為統治機構內涵中的公共性與共同體性質,“國民”(nation)的概念被人們發掘出來。自發的“民族”當她走向自覺,追逐各自經濟利益、文化利益并企圖以國家形式來表現和維護自己利益時,它就不能不涂上政治色彩,成為政治的實體。第一輪民族運動過程中,作為運動主體的民族從自在實現了自覺,也實現了從純粹文化意義上的民族(ethnos)向政治意義上的民族(nation),即“國民”的轉變。〔11〕此時的“國民”已經斷絕了與古希臘羅馬“natio”、“gens”和“ethnos”等諸概念的關系,獲得了近代意義,指的是作為一種公共領域的政治社會的成員資格,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使用的“polital”和“cives” 的近代版本的國民概念。
英文中的“nation”有兩層含義,一是在特定地域上生活并根據自己意愿結成統一的政治共同體的全體人民,這個意義上的“nation”,漢語譯為“國民”,具有政治的屬性,也即是前述的“政治意義上的民族”。二是歷史上形成的族裔文化共同體或人口集團,即英文的“people”,或“ethnic group”,即漢語的“族”,具有自然的人種的屬性。兩種含義互相混淆糾纏,都具有族裔和文化內涵,使人很容易把歷史上形成族裔文化共同體與構成國民國家的民族混為一談,從而增加理解問題的難度。為更好地說明民族和國家,國內學術界現在對這些概念的區別是,英文“nation”譯為“國民”或“國族”,*許寶強、羅永生編譯的《解殖與民族主義》(2004年)中,就把nation 譯為“國族”,把民族主義翻譯成為“國族主義”,以彰顯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區別。另外,馬戎在《民族與社會發展》中區分了族群、民族和國家的概念,辨析了其間的邏輯聯系,認為現代漢語中的民族應做“族群”(ethnic group)解釋(2001年);寧騷在《民族與國家》(1995年)中也試圖厘清國家、國族、民族和族體的概念,認為族類共同體的歷史發展脈絡,是從部落到部族、從部族到民族,再由民族鍛造出國族的過程。因此,民族的概念只有在“族類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才能把握。“民族”則專指與英文“peoples”相對應的歷史上的族裔文化共同體,英文“ethnic group”則譯作“族群”,即多民族社會中具有自己種族文化特征的人口集團。〔12〕
這樣,在國家形成過程中,國民這種成員資格就意味著:
第一,國民具有族屬身份,具有對統一主權國家的認同。這是衡量國民國家形成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所謂“認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信念上與他人聯結為一體的心理過程。白魯恂曾提出,后進的現代化國家在政治發展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國家認同的六個危機中,最首位和最基本的就是民族國家的認同危機。“一個新國家的人民需要逐漸將他們國家的領土確認為自己真正的家園,應當感覺到他們的個人認同部分地是與他們成為一體的有明確疆域的國家來界定的。”*其他危機包括合法性危機、政府權力滲透危機、參與危機、整合危機、分配危機。Lucian W. 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 Analytic Study ,Little Brown amp; Company,1966.p.63。“民族國家認同是民族與國家之間的一種關系,它是那個民族的人民認同他們國家的時候成立的。……它是派生于兩者之間互相統一的概念,我們把這種統一性看作是其最基本的特征”。〔13〕除了最
基本的法律的政治認同之外,這種認同還需要共同的語言、傳統、文化和歷史為支撐。“屬于國家”究竟是如何產生的?福澤諭吉如此說明:“共有世代沿革,同抱回顧之情”——共有歷史就會是國民。〔14〕國家作為想像的共同體被創造出來正是建立在共有歷史的基礎之上。
第二,國民是具有公民權的人,國家是公民的聯合。國民同時作為公民存在,享有國家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和自由。公民權提供了一種新的政治聯系,一種比種族聯系和地域聯系更加廣泛的聯系,也創造了一種新的認同,將共同體成員的政治紐帶從親族認同轉向地域認同,政治-地域上休戚與共的團結意識之出現,又使這種認同從地域上升到對國家整體的認同,國民由此具有公民特質。
但國民一詞更突出以下意蘊:強調民眾的均質性,即沒有差異;強調主權和國籍,即有國家的疆域意識;強調國家共有文化和歷史,即有強烈的認同意識,這又使國民具有了民族特質。這樣,國民權利、國家歸屬和國家認同構成近代國民的三大支柱,同時具備民族特質和公民特質,是國民的內在屬性。既有權利意識又有國家意識,這便是國民。
如果說,公民強調的是“人之所以成為人”所應由國家保障的權利及義務,那么,國民則強調的是“人之所以成為國家的人”所應具備的條件。公民的形成,更多地來自于幾個世紀以來成員自身的不斷抗爭以及與國家妥協的結果;國民的形成,則更多體現的是國家主動的有意識行為的產物。臣民體現的是“無我”,市民體現的是“私我”,公民體現的是建立在“私我”基礎上的“公的我”,而國民在融合這種“私我”和“公我”基礎上強調“有歸屬的我”。這樣的“歸屬感”,既指國籍,又指主權,更指文化和歷史的認同。當我們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一個社會成員的政治資格的時候,這便是國民。當每一個人已經自覺地將國家的事情作為自己的事情去考慮和對待,當這樣的人還同時具有平等意識和權利意識的時候,他們就成為了國民,也就具有了國民意識。
由于內涵的部分重合,現代社會中,公民一詞往往和國民混同使用。“國民國家”往往被“公民國家”、“國民制度”被“公民制度”、“國民權利”被“公民權”所替代。在一個已經完成國民國家建設的社會,這樣的替代并無不妥。作為該社會成員,具有既是公民又是國民的雙重屬性。每個政治成員在公共政治領域出現的是國民或公民的身份,在私的和文化的領域則是民族的身份,這樣的狀態,避免了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利害沖突。但在談論國民國家形成過程中人的政治存在狀態時,國民一詞具有公民無法取代的特定內涵。在抽象的國民概念中,各民族的差異和多樣性被消除,國家的統一得以實現,國民國家得以成立。
通過概念的區分可知,市民的存在為現代公民的興起奠定了基礎,是早期自由主義的成員資格。即使近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建立以后,公民仍然在很長一段時間繼續維系著市民的特性——以財產權為核心,對國家權力進行制約。市民是發展到公民或國民的過渡概念,而國民與公民概念之間在內容上有較大重合,但側重不同。在這四組概念中,具有鮮明對抗性色彩的是臣民和國民。臣民既無權利觀念,也無國家觀念,而國民既要有權利觀念也要有國家觀念。前資本主義時代與國民國家時代,等級社會與平等社會、地方分裂的封建經濟和可以自由進入的市場經濟、孤立的原子式的個人與作為共有歷史和文化的統一的國家成員,兩種不同政治成員的存在形態,是完全不同體制的產物。二者不容共存,處于永恒的矛盾之中。身為臣民,他就不可能是國民,要想成為國民,必須首先要擺脫臣民狀態。
五、近代國民形成的條件
國民國家建構有制度和民眾兩方面的要求。前者涉及國家體制和國家形態的變革,后者則要求所統治國度的民眾從傳統的“臣民”轉變為近代“國民”。那么,近代國民需要具備什么條件呢?從國民國家產生后的實際狀態來看,衡量近代國民形成的標志,最重要的是以下兩個條件:
(一)“去地域化”——打破地區割據,達成對國家的共同認同,形成具有一體感的統一民族特質
去地域化的要求之一是來自于商品經濟發展和統一國內市場的要求。國民應該摒棄狹隘地域主義和族群觀念,具備對統一國民國家的認同,具有與國家命運共生的連帶感,將對地域的忠誠轉變為對國家的忠誠。這是國民“成為現代公民的先決條件,也是所有民族國家的政治體制得以生存的前提。”〔15〕這需要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化價值和共同的心理取向。建構近代國民的過程,正是在具有不同歷史文化和種族聯系的人口中創造出統一性和凝聚力的過程。國家應該為政治共同體成員的這種轉變提供渠道和方式,并使之制度化。
第一,領土的統一和主權的確立。國家的獨立和統一確立了明晰的生存范圍、利益范圍和統一的歸屬對象,是近代國民形成的最基礎環境。近代國民通過領土聚合在一起,“一般說來,自由制度的必要前提是政治疆域與民族活動區域的大致重合”〔16〕。黑格爾曾講:“民族不是為了產生國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國家創造的。”〔17〕
第二,國家統一文化的形成。國民是由具有不同種族和文化的人口集團組成的。在對峙的國際關系中,國家疆域的確定性和疆域內人口的非均質性,急需要國家對內部成員進行文化整合,通過頌揚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和民族自豪感,強調民族感情的神圣性和民族文化的同質性等形式,培育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識。這種意識的形成,只有政治地域的整合遠遠不夠,僅僅通過國家也無法在其成員之間建立起一種自覺的聯系。只有歷史記憶以及對“祖先的崇拜”,才能發揮這樣的作用。英國哲學家休謨早在18世紀就指出國家及其政策對統一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人類學家格羅斯強調,歐洲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統一即單一的文化,往往是國家強加的。〔18〕通過捏造歷史、發明傳統和“意識形態的虛構”等活動,在原本具有人種、語言、宗教、文化、地位和身份等各種價值差異的人群中逐步產生了內聚力,并形成了共同文化。*從這個角度看,作為國家基礎的“國民”不過是為達成民眾的同質性而將各種價值差異整合而編織出來的虛構觀念。國家這一事物,從象征意義上講就是虛構。但一個重要的不容否認的事實是,虛構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19世紀以來,靠著維持這種虛構而產生了國民國家,經過了這些階段,各地區創造出了虛構的國家,以此為單位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它具有無可懷疑的作為社會政治框架的實體性和現實性。而在虛構未能成功的地方往往淪為殖民地。“嘗試通過現在理解和解釋過去,通過過去來理解現在,那些創造歷史遺產的世世代代由此而聯系在一起,休戚與共、息息相關。于是,我們便具有了凝聚力和同情心。”〔19〕
哪些因素對于近代國民意識的形成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呢?
其一,共有“我們的歷史”。密爾指出共有國民史是產生國體感情的最強有力原因。其結果是形成記憶的共同體,大家具有共同的驕傲和羞恥、歡喜與悔悟,過去的事件將其相互聯結在一起。〔20〕共有象征、信仰、傳說和苦樂與共的歷史經歷,區分了“我族”與“他族”的區別,催生了共同利益和歷史連帶感,推動了國民意識的形成。
其二,形成共同語言。共同體語言促成了成員之間頻繁的無阻礙的交往和溝通,喚起了共同的民族意識。
其三,共同的宗教成為聯結政治共同體成員感情的重要紐帶。
從中世紀后期開始,歐洲的王權國家便逐步推行了統一的文化政策。如通過立法和行政的手段實現語言的統一;通過制定政策,實行教育體系的統一,建立覆蓋全國的通信和大眾傳播網絡,實行宗教改革,驅逐異教徒等方式,竭力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員形成統一的政治認同。這種政治文化的核心內容就是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對國家的命運、利益和尊嚴懷有神圣的情感。這為近代國民國家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二) “去奴仆化”——打破身份制度,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取代等級制的屬民身份,以形成“公民”特質
近代國民的建構是對舊的權力結構和社會體系的挑戰,在觀念上需要重新調整個人與法律、政治與社會的關系。政治前提的一致是維系國民情感的重要因素。將全體成員結合在同一個共同體中的政治前提是,民眾有權選擇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共同體形式,有權知道自己在共同體中擁有多大范圍的行為自由,有權決定管理該共同體的政府形式。作為國民,首先必須是具有平等政治、社會和經濟、文化權利的個體,具備有追求個人權利、反抗強權的獨立和自主的意識,具備參與國家公議、承擔社會責任的意識。坂本多加雄強調,國民是自覺的存在,指的是參與國家這一組織體其中的意思。地域聯系和生活在共同地域上的人民之間的聯系和交往,是公民權制度的歷史根源。沒有地區利益和地區政府,沒有地方水平上的公民參與,任何民主制度都不可能存在。〔21〕國家成員逐漸自覺到自身的義務和權利的情況,這就是“國民”。〔22〕作為國家,要為政治成員這種意識的培育和權利的獲得提供文化和制度的保障。
第一,通過“去身份制”,實現政治共同體成員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權利。
第二,通過建立代議制為核心的憲政體制,
將人民主權觀念、法治思想等落實到制度層面,轉換為人們共同遵守和執行的法律制度,并使之成為人們共同接受的行為規則和價值觀念。
第三,有效劃分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地方分權和自治制度是造就這樣素質國民的最有效試驗地和訓練場。
第四,鼓勵地域性非政府組織和團體的發展,發展市民社會。市民社會與國民國家相互依存,互相補充。
第五,不斷推進憲政改革,不斷完善福利保障制度,進一步保障公民權。
國民國家通過公民權的擴大,為新的社會力量提供了政治表達的渠道,創造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從而創造出民眾對國家的政治歸屬感,增強了它們對國家權威的認同,并使其能夠為捍衛國家的獨立自由和爭取國家的最大利益而戰,鑄就了國民不同于臣民的最本質特征。
上述條件中,對于后發展國家,第一個條件是非常核心的指標。“去地域化”是近代國民建構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條件,民族-國家由此得以體現。“去奴仆化”是國民最本質的特征,如盧梭所言:“沒有自由,便沒有祖國”,民主-國家因此而得到保證。兩個指標缺一不可,“去地域化”的民族特質的形成和發展,必然要求具備“去奴仆化”的公民特質,公民特質對權利和參與的要求,是民族特質發展的結果,反過來又有效提供了統一民族特質形成的重要保證,臣民向近代國民的轉化由此完成。
〔1〕 J.Dunn,WesternPoliticalTheoryintheFaceoftheFuture(M).Cambridge,1979,p.3.
〔2〕 〔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尼·弗巴.公民文化〔M〕.新澤西: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63.17-18.
〔3〕 〔8〕〔9〕巴特.范.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條件〔M〕.郭臺輝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譯者序3,56,105-106.
〔4〕 朱耀輝.城市文明與西歐民族國家的興起〔D〕.上海:復旦大學,2003.
〔5〕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啟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201.
〔6〕 秦暉.作為“民主條件”的中產階級:一個徹頭徹尾的假問題〔J〕.綠葉,2009,(12).
〔7〕 佐伯啟思.市民是誰?〔M〕. PHP研究所,1997.154-156.
〔10〕 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M〕.志水速雄譯.筑摩學藝書庫,1994.85-86.
〔11〕 王希恩.民族過程與國家〔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8.179.
〔12〕 王建娥、陳建樾.族際政治與現代民族國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56.
〔13〕白魯恂.認同與政治文化〔A〕.Leonard Binder,Crises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C〕,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p.6,p.13.
〔14〕佐佐木毅,金泰昌.國家·人·公共性〔M〕.金熙德,唐永亮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
〔15〕〔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490.
〔16〕J.S.密爾.代議制政府〔M〕.汪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轉引自林開強.共和主義視野中的自主自治〔J〕.社會科學研究,2008,(1).
〔17〕 轉引自王緝思.民族與民族主義〔J〕.歐洲,1993,(5).
〔18〕〔21〕菲利克斯·格羅斯.公民與國家:民族、部族和族屬身份〔M〕.王建娥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194,199、210-211.
〔19〕王建娥,陳建樾,等.族際政治與現代民族國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61.
〔20〕密爾.功利主義論〔A〕.世界的名著(38)〔C〕.中央公論社,1967.
〔22〕 佐佐木毅,金泰昌.日本的公與私〔M〕.劉雨珍,韓立紅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
【責任編輯:劉明】
D032
A
1008-9187-(2012)04-0066-07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資助項目
田雪梅,西南交通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博士,四川 成都 61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