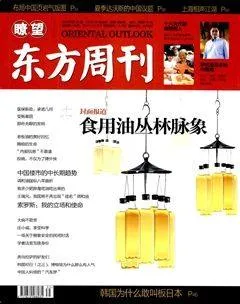醫保新政:承諾幾何
對這些職能部門而言,在微觀層面上增加監管投入的邊際收益基本為零,只要不出現大規模、系統性的糾紛與抗議,它們沒有動機去落實大病醫保政策所需的對醫療活動的監管
8月30日,國家發改委、衛生部、財政部、人社部、民政部、保監會正式公布《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9月3日,上述部委在北京聯合召開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貫徹落實文件精神,啟動和部署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
《意見》最引人注目的亮點是,城鄉居民享有大病醫保,又不額外增加民眾的繳費負擔。近年來全民基本醫保體系已經初步搭建并覆蓋城鄉,但民眾看得起病卻看不起大病的現象仍然突出,大病救濟基本靠非制度性的行政資源和社會資源支撐,因大病致貧、因大病返貧的問題和風險尚未排除。
新的大病保障制度,是基于政府加大財政投入民生的思路,把基本醫保與商業保險結合起來。通過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的對接,由政府、個人和保險機構共同分擔大病風險。這一思路,是醫改良政的普惠改革,是頂層設計的民生承諾。
《意見》原則上為增進社會安全與和諧提供了保障,給人民群眾減緩或解除“大病恐懼”帶來了希望,體現了“使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德政關懷。而立意高尚的德政舉措,其實際效果能否發揮出來,則需要理順大病醫保涉及的各方利益關系。
按照《意見》,大病醫保的第一責任主體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負責當地大病醫保的具體方案、統籌范圍與層次、保障范圍、就醫結算管理等基本政策,并且要負責招標確定承辦大病保險的商業保險機構。一經國務院同意發布,則成為對地方政府政務的具體要求,并將成為地方政務績效考核的科目之一,地方政府有責任和動機認真落實和完成。
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面臨一系列約束。
資金來源就是主要的約束條件之一。為了盡量不增加民眾當前的保費負擔,大病醫保基金從城鎮居民醫保基金、新農合基金中按一定比例或額度劃出。這一規定顯然是基于當前多數地區醫保結余基本可以覆蓋大病保險所需金額而作出的。
為了應對個別地區覆蓋不足的情況,《意見》規定結余不足或沒有結余的地區,在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年度提高籌資時統籌解決資金來源,逐步完善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多渠道籌資機制。但這些規定是基于以往的情況作出的。一旦大病保險建立之后,短時間內可能有醫療需求的爆發式增長,結余就可能出現明顯不足。
大幅提高年度籌資顯然與不增加民眾負擔的初衷不符,按照一些地方的做法,還是要由地方財政來兜底或補貼保險公司的收入。而這一財政支出無疑會擠占地方政府原定其他的財政支出,從而可能影響政府的績效考核。如果地方政府認為后者的影響更不可接受,那么大病醫保的實施效果是否會被打折扣?
保證大病醫保可持續性的另一關鍵是抑制過度的不合理的醫療需求爆發式增長,逮涉及商業保險機構和醫院兩大利益主體。從商業保險機構的角度來看,能夠分享大病醫保總的來說是一件好事,能夠獲得免征營業稅的保費收入,擴大可利用資產的規模。但《意見》對商業保險機構的規定也存在不夠一致之處,一方面規定“商業保險機構自愿參加投標,中標后以保險合同形式承辦大病保險,承擔經營風險,自負盈虧”,另一方面又規定要遵循保本微利的原則。前者是要求遵循市場規律,后者是要調動保險公司積極性,放到—起,可能會產生一定的模糊性。
實際上,商業保險機構的重要作用就是甄別合適的醫療機構和醫療手段,避免過度醫療。《意見》還特地規定了“配備醫學等專業背景的專職工作人員”等保險機構準入條件。但是,配備專職人員并落實其監督職責是有成本的,而且這個成本可能不低,如果沒有嚴格的“自負盈虧”的限定而由財政保證其“保本微利”,有可能出現保險機構寧愿不支付這個成本而放任過度醫療的現象。
如此,監管的壓力不但沒有分散到擁有更多經營性資源的保險機構身上,反倒更集中到衛生部門等政府機構頭上。而對這些職能部門而言,在微觀層面上增加監管投入的邊際收益基本為零,只要不出現大規模、系統性的糾紛與抗議,它們沒有動機去落實大病醫保政策所需的對醫療活動的監管。
目標非常清晰,承諾進入倒計時。具體怎么辦,還需要各地實踐的檢驗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