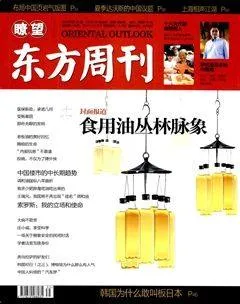上海相聲江湖
把握尺度非常重要,曉阻的處理方式是“以我的困惑去討好觀眾的困惑”,把他對社會的困惑表達出來,點到為此。
下午2點,海上相聲大會開演。
12點30分,最早的一名觀眾已到場,挑了一個好位。
樓梯間是演員們的后臺。
魔術師毛毛捧著塑料盒吃便利店買來的壽司,說評書的陳傳奇在轉扇子,說相聲的陸銘俊抱著椅背思考人生……
“班主”曉陽趁機來給他們上課:“練聲就要背上出汗,脖子上起金線”,“一天不練,自己知道;兩天不練,同行知道;三天不練,觀眾知道,”“不要讓觀眾拿耳朵湊你,要把字送到他耳朵里去,哪怕下面的人在嗡嗡講話”。
毛毛一邊咽著盒飯壽司,一邊聽班主繼續說;“我請你吃紅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三鮮丸子、氽丸子、鮮蝦丸子、魚脯丸子……”
“要尊重老百姓傻樂的權利”
曉陽滿臉掛笑地登場,他的開場白有一個固定的項目:教觀眾叫好,正確的叫法類似于趕驢的長腔“壹——”曉陽問:“加倍叫好呢?”觀眾無師自通:“貳——”
氣氛即刻被調動起來。
“你覺得你的文化生活豐富了嗎?”曉陽接著問臺下。
一名對文本很講究的文化研究者在欣賞了整場演出之后,自己沒怎么笑,但是看到觀眾笑得前仰后合,若有所思:“要尊重老百姓傻樂的權利。”
觀眾中很大一部分是尋求減壓的白領,曉陽們要把相聲的“胡同味兒”,說出“咖啡味兒”、“電腦味兒”、“打印機味兒”。
觀眾席的設計就是要解除正襟危坐,桌上擺著一個個盛瓜子殼的塑料筐,嗑瓜子聲和笑聲一樣被鼓勵。
觀賞相聲就好像一場愉快的催眠之旅,曉陽自比為催眠師,開場前先用10分鐘左右跟觀眾聊天,叫做墊話,如同好的按摩師,不是上來就按穴位,而是先捋一捋。
觀眾“給耳朵”是臺上演員時刻關注的,“所有的眼神都跟著你走,那就沒掉線,你塞什么都會有”。發現下面的注意力渙散了,有人開始上廁所了,馬上甩出包袱。“我們在臺上使活的快慢,哪些炸響了,哪些癟掉了,心里清楚得很,現場不斷修正。一個包袱沒打響的話,類似的包袱絕對不會再用了。”陳傳奇說。
“把點開活”是臺上臺下互動的重要形式。
一個不能忽略的“點”是觀眾對于時事的興趣,每當講到這里,臺下的眼睛總是睜得最圓。這是人的通性。就像海峽對岸以“解悶救臺灣”為己任的《全民大悶鍋》總是收視飄紅。
把握尺度非常重要,曉陽的處理方式是“以我的困惑去討好觀眾的困惑”,把他對社會的困惑表達出來,點到為止,比如,房奴苦哈哈的生活。
不談現世,說說古代,是另—個策略。
曉陽說:“侯寶林說過一個相聲,舊社會的相聲藝人苦,什么都不能說,諷刺軍閥的不能說,諷刺政治的不能說,那這相聲還有什么可樂的呀,說相聲的就只好拿自己開玩笑,‘我給大伙說段相聲,我就是您眼前的歡喜蟲,這是我的搭檔,他叫狗子’,軍閥還是不樂意了,因為軍閥的小名叫阿狗。”
在每個區演出,接受每個區的文化稽查大隊監管,上交節目光盤,蓋章之后才能演出。曉陽會收到很多“叮囑”:“三俗的東西不能說啊。”
“《蝴蝶的尖叫》、《陰道獨白》,這種話劇算不算三俗啊?”曉陽疑問。他們在實際操作中,常常留足安全余量。
北京的“嘻哈包袱鋪”旗下的幾個劇場剛剛因為尺度的問題停演,也對上海的相聲圈有影響。
包括相聲在內,還有一些小劇場演出,尺度比較放開,甚至形成了一種亞文化。這是一個大眾傳播的場域,但又有別于媒體的大眾傳播,有許多臨場發揮,有即時性,聲過無痕,落實到相聲產品的生產者身上,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怎樣把關、自設尺度,就很重要。
海上相聲大會每周三排練自查,所有的活都得在班主那里走—遍。場租幾乎吞食了全部收入
演出非常成功。
演員們自己收拾好桌椅,就該走了。場子所在的古玩城下午6點30分打烊,上海的夜生活才剛進入飯局階段,海上相聲大會的演出已結束,不屬于夜上海。
班主給每個人發勞務費,自己分得100元,他說了兩段相聲還兼任主持;演員嚴夏得到50元;外地趕過來的,多拿一點,聊作路費。
“我們巴望著弄個夜場,觀眾會更多,剛談了另外一個場子,150個座,開價3000,我們怎么付得起呢?”陳傳奇說。
場租幾乎吞食了全部收入。當天下午到了80名觀眾,其中20名買的是25元一張的關系票,另外60人都是團購(39.8元),團購網站每張票扣掉9.8元,票房總收入為2300元(500+1800),場地費2000元,9個演員分300元像分蚊腿肉。業主主動將租金調低到1000元。
上海寸土寸金,在一處剛打響,卻得被迫換個地方。
北京、天津亦為一線城市,相聲場子大而固定,關鍵是租價只有上海的1/2甚至1/3。
曉陽想不明白:現在街道的劇場都很豪華,國家投了那么多錢建造,花錢去請演出團隊,我們說相聲的,不請自到,還付你租金,同為文藝工作者、弘揚主旋律,為什么我們就不受待見。街道劇場又不會請帕瓦羅蒂,不正適合說相聲嗎?
他們曾尋求組織的關照,曲協、藝聯很客氣地表示自己也是民間組織,不能解決關鍵問題。
因為場地,最痛苦的時候1個月賠1萬元。
曉陽的團隊得到一個演出機會,10月去昆山千燈古鎮演1個月,報酬加萬元。
“一年來10場這樣的演出,我的日子就滋潤了。”曉陽說,“郭德綱也是靠走穴賺錢的,德云社貼錢也要演,這是他的陣地。我們在自己的陣地上慢慢地打品牌,要靠積累。”
一場下來最起碼多六七個微博粉絲,這就是這家相聲公司的積累速度。
無論如何,一杯咖啡的錢換來倆小時肆無忌憚大笑的機會,還是“格算”。
2009年初在北新涇街道駐演,找了個微縮景觀戲臺,坐滿了也就30個人,最慘的時候只有三四名觀眾,臺上臺下同洗桑拿。后來好一點了。十幾個觀眾人手一把蒲扇,嘩嘩扇著,就有了人氣旺的錯覺。
處在創業期的相聲公司,對觀眾的珍惜和誠意,常常無與倫比。謝幕時演員們使勁拍著手向觀眾致謝的眼神,真把“衣食父母,這個詞演了出來。“維穩”
在這周的演出中,曉陽預告下周將有3名新人獻藝,他們來自北方曲校,現回去領畢業證了。
周中,距離下輪演出還有3天,有觀眾打電話來,說看到那3個孩子的海報登在另一家相聲會館的團購廣告中,與“海上相聲大會”并列在同一個網頁。
不告而別的感情傷害在其次,措手不及才棘手。
隊伍穩定是與場地同一重量級的難題。上海相聲這幾年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分分合合正是注腳。
郭德綱的成功讓小劇場相聲看到了春天,作為回應,上海先后推出了蔡嘎亮、周立波。前者目前回歸浴場,后者轉會浙江。上海的小劇場相聲亦被視為由這股春風催生。從相聲重新被喜聞樂見的大風氣上,這個觀點有些道理,但從機體上,上海小劇場相聲是自生的。
2004年,上海曲藝之友社成立,它將在日后分生出上海現有的6個主要相聲社團。
2008、2009年之交,曉陽、張文澤、李騰洲脫離上海曲藝之友社,成立海上相聲大會。2009年,金巖、鄧濤接踵獨立,成立品歡相聲會館,曲藝之友社的剩余班底就改組為田耘社。
2010年,李騰洲再次從海上相聲大會分家,成立樂透社,2012年,樂透社的王高飛又分裂形成悅空間。
2011年,張文澤也告別了海上相聲大會,組織起百領社。
除了上述6家,在大裂變的格局中,還誕生了笑海相聲客棧、凌云相聲大會、相聲笑棧等微型相聲社團。
品歡、海上相聲大會兩家,像皇馬、巴薩之于西甲,是高出同行一大截的相聲團體。
品歡班主金巖,致力于解決隊伍穩定的問題,所有演員都在上海有家有業,不指望說相聲的錢開飯。除了主推的金巖和李國靖,其余都是兼職,其中有海歸白領和公務員。
海上相聲大會也在按照這個思路做,“去專職化”是維持隊伍穩定的法寶。
曉陽、嚴夏早年抄底買了房子,房租為其生活打了底線;陸銘俊做家教、賣陜板;陳傳奇忙著趕場子。
“現在我們只招上海人,(他們)在這有房,可以啃老,不必等著說完相聲交房租。說相聲這點錢連房子都租不起。吃可簡單,弄把米、熬個粥,一天十來塊錢也能對付。但2000塊錢只能租個簡陋的一戶室。”曉陽說。
盡管挑剔,可供挑選的人力資源卻不多,全上海固定的相聲演員約30人。一支隊伍可能瞬時分崩離析。
2010年海上相聲大會曾經解散,曉陽去做婚慶主持人,收入頗豐,一年20萬;嚴夏則去做話劇。2011年,重整隊伍,老班底又從四面八方嘯聚老地方。
復雜的競合
相聲這個行業,北方軍團在專業實力上無疑更強大,但是,上海軍團從未將其視為對手。
原因有二:—是北方軍團暫時無意覬覦上海市場,北方還有巨大市場容量,而上海是塊“硬土”,按照先易后難的市場開發順序,上海還不是主戰區;二是海派文化自身修起—道天然屏障,北方缺乏本土經驗,斗不過已在上海耕耘多年的地頭蛇,后者知道上海人的笑點在哪、怎樣戳中。
總之,上海不怕“過境車輛”。反而,北方軍團可被利用借力打壓本地競爭對手。
但是,在“寧合縱、亦抗衡’的大態度下,上海軍團對小股帶有騷擾性質的北方軍團亦有小脾氣。
三個月前,一位上海資深票友自殺。他本是一名愛好說相聲的制圖工程師,登臺表演是最大的愿望,可惜口不順,一肚子貨倒不出來。一個外來的相聲投機者找到他,稱愿對他進行專業打造,包他3個月能登臺,還能大賺一筆。工程師拿出了全部積蓄加上老母親的退休金進行演出投資。后來,演出沒有辦成,投機者說:“你在上海堅持尋找演出機會,我回天津轉一下,賺了錢我再貼補你的虧空。”在渺茫的等待中,萬念俱灰的工程師投河自盡。
“以為在上海演相聲好糊弄,來上海投機,結果砸了北方相聲這塊牌子,后果由整個行業承擔。”一位上海相聲演員說。
其實,就全上海相聲社團的整體競合關系而言,合大于竟,現在是大家攜手烘托市場的階段,不管觀眾進了哪家的門,都算是為上海這塊相聲的“硬土”松土。
創作短板
相聲表演、創作兼修的人鳳毛麟角,但是,幾乎每一個相聲演員又都在忙創作,因為專業的相聲創作者幾近絕跡。
每一次相聲創作的高峰都在社會轉型期,不僅是因為題材多,每個轉型期都是一次思想解放,禁錮少了,社會集體心理處于向上的興奮期,更多看到的是希望。
老舍是建國初的相聲創作者,不僅愛相聲、寫相聲、改相聲,還親自上臺說過相聲,這是他鮮為人知的一面;馬季是改革開放之初的相聲創作代表,同樣是表演、創作雙料大師;梁左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頭號相聲作者,被視為最后的大師級相聲作者,相聲最后—個黃金時期的幕后領軍人物。
“梁左之后,姜昆再無好作品問世。想當年,姜昆的諷刺力度是現在的郭德綱都不及的。”嚴夏評論。
現在,創作仍是短板。
郭德綱說:“廚師都說相聲了。”但是,創作的門檻不低。品歡相聲會館招聘演員,要求本科以上學歷,以保持團隊的創作力。
相聲創作不同于話劇、影視劇本,不需要—個邏輯嚴密、曲折跌宕的故事骨架,對于相聲,骨架存在的主要功用是掛包袱,包袱—個個地抖開,釋放笑料。對主干要求不高,只要故事能發展得下去,包袱有地可掛,這就夠了。
目前,相聲演員的創作方式有三:老活翻新(說老段子,如《捉放曹》)、重新添肉(用老段子的骨架填入現代故事)和全新創作,三者占比大約是4.5:4.5:1。
常用于翻新、改編的老活兒有《報菜名》、《八扇屏》、《茅房話》等。
《報菜名》的賣點在于像RAP一樣的貫口。曉陽不愛在貫口上炫技,“就是靠賣苦力,博得觀眾同情的一笑,機會還是留給年輕人吧”。但他埋怨現在的年輕人功夫下不到家:報菜名都是到“板鴨筒子雞”就結束了,而這才說了152樣,后面還有96樣。“老先生一千多段相聲,到我們這里就兩百段了。”
郭德綱的德云社要求演員肚子里存80-100段活;海上相聲大會要求翻倍,剛入行的曉磊已存了二三十段。
有了這些底貨,能起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的效果。曉磊解密:上場時沒有固定腳本,尚有三成現掛(臨場創作)。
網絡段子是包袱的一個重要來源。網絡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豐富了相聲演員的段子庫,另一方面提高了觀眾的笑點,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因為好扒網絡段子,招致不少詬病。
“我的說話是練過的,怎么寸勁、怎么氣口,停頓、氣息,給網絡語言增添了附加值。同樣的話不同的人說不一樣,‘你走先’被周星馳說出來、‘我看行’被葛優說出來,就搞笑了。”曉陽說。
海上相聲大會號稱每個月演出8到10場,連續4個月“不翻頭”(不重樣)。每周都要進行創作,相聲演員的創作并非趴在案前冥思苦想,而是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對出來的,對的時候也不用表演腔,竊竊私語居多。
一般說來,一段20分鐘的相聲,底本需要1萬字。更多時候,他們并無底本,現掛的多,隨用隨扔。
把相聲上海化難,將上海相聲化很難
海納百川的上海自開埠以降就是一個異質文化交織的空間。
一群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說相聲,沒有半點兒上海普通話的塑料味,京味字正腔圓。
他們仍有豎起“海派相聲”大旗的小小野心,可是,誰都無法定義,何為“海派”。
顯然,不是在作品中夾雜幾句上海話或幾處上海景,這仍浮在表面,深層次是像上海人那樣去思考。這其中的悖論是,作為思維工具的語言,說相聲時被替代成北方官話,但恰是俚語深藏了許多上海地方特有的幽默感。
陳傳奇嘗試南書北說已五六年,他的處理方式遵循了陳云當年的建議:不必每字必翻,有時就給北方人聽幾句上海話。
說評書的陳傳奇及說相聲的嚴夏,不約而同正在做的一項工作是讀上海史,從中挖掘創作題材。
這種從地方史著手的落地,可以找到官方宣傳需要與民間文化需求之間的共同語言。嚴夏正在琢磨瑞金二路上的幾幢公館洋房,瑞金二路街道希望在相聲中植入宣傳,嚴夏看中的是他們有300人的劇場,可以“用劇場換宣傳”。
難點在于怎樣從這百年無語的房子中抖出笑料來。與把相聲上海化相較,將上海相聲化更難。
同時,觀眾對笑點的期待卻越來越高。譜系與江湖
相聲是師承制的,所以有張譜系圖。
曉磊是入門沒多久的“85后”,談起相聲史能將人物梳理得脈絡清晰。拜師后,師父會跟他講自己屬于哪門哪派,這叫“鑿根”,日后行走江湖,碰到門里的人,該行禮就行禮,稱為“盤道”。
曉陽半年前剛接待了3個來“盤道”的天津小孩,“到我這里報報家門,我就收他們在這里演戲賺錢,他能賺到就算他的,他賺不到,是他學藝不精,我就給他盤纏讓他回去”。
相聲譜系在新中國從未斷過,但時隱時現。有人批判這是封建糟粕,但這樣一個全國一統的譜系確實方便了藝人們行走江湖,師徒情分又為公司治理添加了穩固劑、潤滑劑。只是,當譜系這張網碰到權力、現實利益,也可能像蛛網—樣被抹去。
曉陽的海上相聲大會干脆不要這勞什子,“公司里沒有我的徒弟,他們也不指望我的名號出去混飯吃”。
曉陽的輩分很高,“德、壽、寶、文、明”中的“文”字輩,是姜昆、郭德綱的師叔輩。“姜昆那么大官(中國曲藝家協會黨組書記),我總不能見面就說我是你師叔吧。”曉陽打趣道。
公司化外殼下的相聲社團是一個交織著現代治理理念與充滿個性的空間。相互之間日常說話拿腔拿調,用表演腔,在不同方言間切換,酒桌上的高聲發揮把鄰桌的女孩逗到噴飯。在與觀眾的互動中,有人收獲了名聲,有人收獲了金錢,有人收獲了婚姻,有人為利翻臉,有人出走……
這是一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