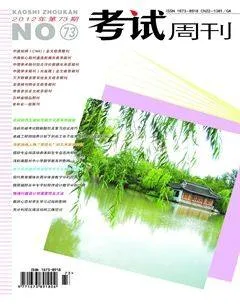中西神話中的女性比較
摘 要: 中國(guó)文學(xué)對(duì)神話中神祇女性的稱(chēng)謂一向是“神女”,“神女”被“女神”取代源于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的翻譯,“神”和“女”的主體更易顯示出女性神格的差異。本文以此為出發(fā)點(diǎn),通過(guò)地母形象及女性在愛(ài)情中地位的差異,進(jìn)一步論證中西神話中女性神格的差異所在。
關(guān)鍵詞: 中西神話 神女 女神 地母形象 愛(ài)情故事
雖然“神女”和“女神”在英語(yǔ)中都可以譯為“goddess”,但“神女”是中國(guó)文學(xué)對(duì)神話中神祇女性的一向稱(chēng)謂。“女神”出現(xiàn)在上世紀(jì)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及以后的翻譯作品中,用以區(qū)別“神女”,意指西方文學(xué)對(duì)神話中神祇女性的稱(chēng)謂。“神”和“女”的主體更易顯示出女性神格的差異。這可以從中西神話中的地母形象及女性在愛(ài)情中地位的差異方面得到論證。
一、“神女”與“女神”
中國(guó)文學(xué)對(duì)神話中神祇女性有兩種稱(chēng)謂,一是“神女”,二是“女神”,二者使用的時(shí)間不同。“神女”多見(jiàn)于古籍,《辭源》稱(chēng)戰(zhàn)國(guó)楚宋玉的《神女賦》即有:“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yáng)之渥飾。”可見(jiàn)該詞在戰(zhàn)國(guó)已經(jīng)出現(xiàn)。
“女神”一詞,《辭源》未收入。“女神”一詞的時(shí)髦,是在上世紀(jì)初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出版于1921年的郭沫若的《女神》可謂這一稱(chēng)謂的高峰,于是在新文學(xué)作品特別是翻譯作品中,“女神”迅速取代了“神女”。
“神女”被“女神”取代,可視為是時(shí)代進(jìn)步的折射。從詞法上看,“神女”為偏正結(jié)構(gòu),“神”為修飾,“女”為主體,所謂“神之女”,如娥皇、女英—堯之女;女娃—炎帝之女;龍女—龍王之女;宓妃—伏羲之女……她們或?yàn)閷し蚰缢澜校蛞蛴蛔由穸劽K齻兊纳窀窈诵氖菍?duì)男神的依附。就連發(fā)誓“以堙東海”的女娃,也在幻化為精衛(wèi)之后被說(shuō)成是“偶海燕而生子”,即以攀附上男神為歸宿。
誠(chéng)然,上古神話中有過(guò)女性崇拜和女性性器崇拜的輝煌,而且,由于女性成為生命的賦予者,從而導(dǎo)致遍布世界各地的“地母”。正如一位西方學(xué)者所說(shuō):“作為地母神,她生育了一切創(chuàng)造物。”[1](38)但是,母系繼嗣關(guān)系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女權(quán)統(tǒng)治。正如英國(guó)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xué)者喬治·湯姆森在他的《史前愛(ài)琴》一書(shū)中所說(shuō):“在我們已知的許多——也許是大多數(shù)——母系制部落中,實(shí)際的統(tǒng)治權(quán)都掌握在男性手中。繼嗣法則本身常常被明顯的權(quán)宜之計(jì)所超過(guò)……”[2](35)
男權(quán)統(tǒng)治雖是世界的普遍現(xiàn)象,但在中西方是有差異的。“神女”的神格核心是對(duì)男神的依附,而“女神”其神格核心是對(duì)男神的不依附。郭沫若對(duì)“神女”意識(shí)的悖逆絕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而是“求新聲于異邦”,即受益于翻譯介紹西方作品。其中古希臘文學(xué),特別是其神話深邃空靈的哲理性與博大明晰的民主精神為一代新青年所推崇,而反映民主精神較為集中的則是西方的女性意識(shí)。古希臘與中國(guó)傳統(tǒng)迥然不同的女性觀念使譯者選取“女神”一詞而摒棄“神女”,從而造成在中國(guó)文學(xué)中由過(guò)去稱(chēng)“神女”而在新文學(xué)中稱(chēng)“女神”的現(xiàn)象。這就是說(shuō)我們有必要探討古希臘神話中神籍女性的神格要素究竟如何,并由此比較古希臘神話的女性意識(shí)與中國(guó)上古神話的差異。
二、地母形象及女性在愛(ài)情中的地位
中國(guó)與古希臘同屬世界有悠遠(yuǎn)歷史的古國(guó),但兩國(guó)流傳至今的神話卻難以頡頏相類(lèi)。古希臘神話有完整的《神譜》和《荷馬史詩(shī)》傳世,而中國(guó)的神話散見(jiàn)于各種典籍諸,如《國(guó)語(yǔ)》、《山海經(jīng)》、《呂氏春秋》、《楚辭》、《詩(shī)經(jīng)》之中。現(xiàn)在,我們從天地起源入手。
(一)地母形象的差異
地母是在宇宙之初的黑暗與混沌中出現(xiàn)的。古希臘赫西奧德的《神譜》把混沌之中最先出現(xiàn)的宇宙物象,即最先產(chǎn)生的神—大地,說(shuō)成女神,一方面說(shuō)明在認(rèn)識(shí)能力低下的條件下,人們只能按目睹的生育現(xiàn)象詮釋自然,另一方面顯示了女性在古希臘人心目中的地位:先于一切。
在北歐神話中,人類(lèi)婚姻與性愛(ài)是由兩個(gè)女神分別掌管的。主宰婚姻的女神佛利茄(Frigg)是婚姻的楷模,她被視為眾神之后,常年住在芬薩利爾宮操作織機(jī)。她在宮內(nèi)邀請(qǐng)世上忠實(shí)的丈夫和妻子去共享歡樂(lè),這些忠貞夫妻因此可以雖死而不分離。
掌管美與戀愛(ài)的女神佛利夏(Freyia)從身份和職能上看均與維納斯相當(dāng)。“在日耳曼,她和佛利茄混為一人,在挪威、瑞典、丹麥及冰島,她是獨(dú)立的神”,[3](295)傳說(shuō)夏天的太陽(yáng)奧度爾是她的丈夫。所有的神包括巨人、侏儒都渴望要佛利夏為妻。值得注意的是,北歐的愛(ài)與美之神也與地母神有相互認(rèn)同的關(guān)系,也正是茅盾先生所說(shuō):“佛利夏也被視為大地之人格化。”[4](296)這一事實(shí)表明,司婚姻生育之神和司性愛(ài)戀情之神都是從地母神信仰中派生出來(lái)的,她們的功能也是地母原有功能在神話中的分化。
地母是最受崇敬的,而那些頭戴皇冠的皇天之父雖高踞于大地之上,但卻是大地所生,全靠大地的負(fù)載和承擔(dān)才得以生存。因此,輕浮飄悠的男神天父還需要依附堅(jiān)實(shí)的女神大地。
中國(guó)神話中地母的情形又是如何呢?可惜的是,這方面的資料現(xiàn)已隱沒(méi),我們只好在天父地母不是純粹的神話形象的《周易·說(shuō)卦》和其他古籍中尋覓蛛絲馬跡。《周易·說(shuō)卦》云:“乾,天也,故稱(chēng)乎父。坤,地也,故稱(chēng)乎母。”《淮南子·精神訓(xùn)》云:“圣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yáng)為綱,四時(shí)為紀(jì)。”
《春秋感精符》云:“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shí)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在所有這些將天父與地母并列、先天而后地的措辭背后,潛藏著早已被父權(quán)制文化所吞沒(méi)的推崇女神——地母的信仰和觀念,因而《周易》鮮明地體現(xiàn)著象征天父的乾卦凌駕于象征地母的坤卦之上。
方俊吉先生說(shuō):先儒以天先而地后,天尊地卑,因而時(shí)以單稱(chēng)“天”以概“地”,而不見(jiàn)稱(chēng)“地”以概“天”,蓋明乎尊足以概卑,上足以概下也。[5](57)意識(shí)形態(tài)中的“以天概地”現(xiàn)象,恰恰是以社會(huì)關(guān)系中“以男概女”現(xiàn)象為背景的。二十五史完全是男人編寫(xiě)的給男人看的歷史,女性只有作為帝王的后妃,作為男子所贊賞的父權(quán)制道德的殉葬者——烈女,才能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確切地說(shuō),她們是作為男人的附庸而留下名字的。因?yàn)椤霸谥袊?guó)古代,女子是沒(méi)有名字的……或以字配姓(伯姬、仲子、孟姜、季嬴之類(lèi)),或以姓搭夫氏上(衛(wèi)孔姬、晉趙姬之類(lèi)),或以姓連在夫爵上(楚息媯、齊棠姜、魯秦姬之類(lèi)),或以姓與子連(陳夏姬、宋景曹之類(lèi))。這些情況都可以看做是女子沒(méi)有自己的人格,只是依靠男子才獲得人格的證據(jù)”[6](15)。
“以天概地”的現(xiàn)象從《禮記·郊特牲》的郊祭禮儀及其郊祭的陪襯社祭中可以看出。社(祭)崇拜作為地母生養(yǎng)功能崇拜的形態(tài),多少還保留著某些原始痕跡,顯示出了我國(guó)第一個(gè)地母崇拜的活標(biāo)本。但是它的社祀遺址與葬地的造型表現(xiàn)了地母崇拜與太陽(yáng)崇拜相融合所產(chǎn)生的擬人化天地觀和天父地母交合的神秘思想,即地母作為陰性的神需從陽(yáng)性天神受孕方可生育萬(wàn)物,確保大自然生命的無(wú)限循環(huán),而充當(dāng)使地母受精的陽(yáng)性角色的天神就是太陽(yáng)神。太陽(yáng)代表了天,也代表宇宙間一切陽(yáng)性力量。于是天陽(yáng)、地陰和天父地母則成其為關(guān)系的準(zhǔn)則。對(duì)此,《周易·說(shuō)卦》的“乾,天也,故稱(chēng)乎父。坤,地也,故稱(chēng)乎母”已做出精辟的概括。我們也可以解釋為“以陽(yáng)概陰”或“以父概母”,這與西方的男神天父要依附堅(jiān)實(shí)的女神地母是有區(qū)別的。
(二)女性在愛(ài)情生活中的地位
愛(ài)情故事本來(lái)是包括神話小說(shuō)在內(nèi)的永恒的文學(xué)主題,但是中西方的情況并不一樣:在西方,愛(ài)情故事尤其是古希臘神話的重要內(nèi)容,但在中國(guó)神話中幾近空白狀態(tài),或只有神女的艷麗嬌媚,而少有兩情相悅的性愛(ài)。
宋玉《神女賦》云:“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yáng)之渥飾。”說(shuō)楚襄王與宋玉游于云夢(mèng),夢(mèng)見(jiàn)一神女,嬌媚得奪天地造化之工。此女神緣何嬌媚如許?從《山海經(jīng)·中次七經(jīng)》可覓其源頭:“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shí)如菟丘,服之媚于人。”死后所化之草,服之能媚于人,想來(lái)她生前定有艷念未果,只好托精誠(chéng)于所化之草,以?xún)斘戳酥浮5档米⒁獾氖牵笆欠裼衅G念,皆系非神的后人所推測(cè)。至于襄王一見(jiàn)神女之艷麗便想入非非,也是由于襄王不是神而是人。
而且,即便是人,也少有不軌之舉。《楚辭·天問(wèn)》里有句反問(wèn):“禹之力獻(xiàn)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臺(tái)桑?”看來(lái)對(duì)“布土以定九州”[7]的日理萬(wàn)機(jī)的禹,群眾中也流傳有“通之于”某處的議論,但這“通”卻光明正大。他雖與涂山女合而終離,但“合”為嗣胤,“離”為事業(yè),無(wú)任何不譽(yù)之隙。在女性,人為的“多媚”便有誘“通”之嫌,“通”則萬(wàn)惡,而中國(guó)上古神女,卻罕見(jiàn)這一作媚之“通”。男性王者雖然有“通”,但在他們則為王者之政,當(dāng)然也是男權(quán)之政。
古希臘神話中的情況則不是這樣。眾神之王,風(fēng)流天神宙斯與風(fēng)流女神阿佛洛狄忒的風(fēng)火戀情一度被其配偶妒恨。以善妒為個(gè)性特點(diǎn)的赫拉“永不約束自己的憤怒”,一有機(jī)會(huì)就施行報(bào)復(fù),且手段狡詐歹毒——阿佛洛狄忒的丈夫赫菲斯托斯僅使對(duì)方難堪,而赫拉則多迫害所妒女子以迫使宙斯斷念。而所妒女子仍是我行我素,并不就范。因而男神比女神并不更有特權(quán),即使輿論上也不占優(yōu)勢(shì)。
宙斯是放蕩不羈的,擁有七位妻子,還常有外遇:伊俄、卡里斯托、歐羅巴、邁亞等。不像中國(guó)只有男性可以這樣,西方神話中的女子亦有如此的“多遇”種子。例如風(fēng)流女神阿佛洛狄忒,除有老公赫菲斯托斯外,還有戰(zhàn)神阿瑞斯、神使赫爾墨斯、英雄安客墨斯、獵手阿爾多尼等“編外”。看見(jiàn)“編內(nèi)”“編外”相互遭遇,眾神十分超脫。當(dāng)她與阿瑞斯被赫菲斯托斯罩以鐵網(wǎng)后,男神中有波塞冬費(fèi)盡口舌動(dòng)員放走他們,女神則幫她沐浴,并“涂上永生天神們整容的神膏,使其光彩動(dòng)人”。[8](96)作為對(duì)照,懷著忿忿然情緒上場(chǎng)的瘸腿赫菲斯托斯,在“鬧”劇結(jié)束時(shí),居然變成小肚雞腸的“妒夫”,真是不可思議。
中國(guó)男神在婚姻性愛(ài)上的地位遠(yuǎn)比女神優(yōu)越。帝俊(亦帝嚳)有妻四位:姜原、簡(jiǎn)狄、慶都、常儀,舜、羿等至少有妻三位。但在神女中,女?huà)z、精衛(wèi)、魃、西王母等,均為一身獨(dú)居。而登比氏、娥皇、女英、羲和等卻為眾妻之一,與眾姐妹共同侍候一位夫君。還有嫘祖、女登、女樞、女祿等更是從一而終的妻子。這表明后來(lái)被視為婦女大節(jié)的守貞觀念這時(shí)已經(jīng)萌生。
對(duì)于希臘和中國(guó)神話中女性的這一差異,茅盾先生極有感觸。他十分欣羨希臘羅馬神話中的美麗女神都有她們雅致或粗俗的愛(ài)情故事,例如阿佛洛狄忒即是愛(ài)與美的女神。而中國(guó)神話卻相形見(jiàn)絀,于是他只有聯(lián)想了,即在他有關(guān)《九歌》、《離騷》的神話敘述中,只能發(fā)出即有美麗女神必有愛(ài)情的聯(lián)想,更有“中部的神話一定有許多戀愛(ài)故事”的推論。[9](75-78)他還把這一聯(lián)想移植到自己的小說(shuō)之中,即將美麗女性置于似可用愛(ài)情概括的兩性關(guān)系之中。
參考文獻(xiàn):
[1]卡莫迪(D.L.Carmody)著.徐鈞堯等譯.婦女與世界宗教[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38.
[2]轉(zhuǎn)引自葉舒憲.唐高神女與維納斯[M].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7:35.
[3][4]茅盾.神話研究[M].白花文藝出版社,1981:295,296.
[5]方俊吉.禮記之天地鬼神觀探究[M].臺(tái)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57.
[6]山川麗.中國(guó)女性史[M].高大倫等譯,三秦出版社,1987:15.
[7]見(jiàn)《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
[8]荷馬著.楊憲益譯.奧德修紀(jì)[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96.
[9]中國(guó)神話研究初探.茅盾評(píng)論文集[M].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8: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