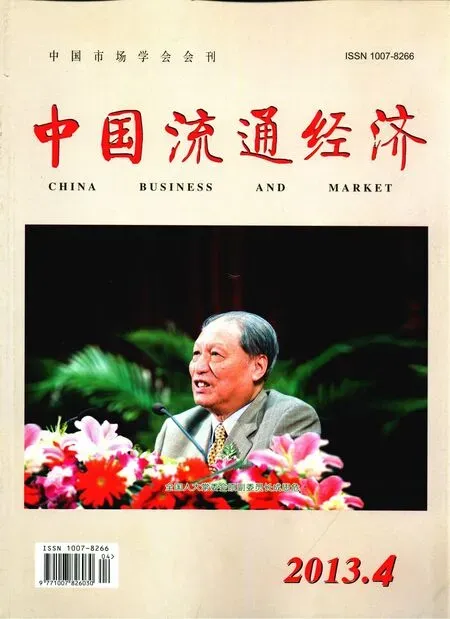論近代中國民族企業戰略管理思想及其實踐
歐紹華
(湖南工業大學商學院,湖南株洲 412008)
論近代中國民族企業戰略管理思想及其實踐
歐紹華
(湖南工業大學商學院,湖南株洲 412008)
近代中國民族企業家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內涵豐富的管理思想。在戰略分析階段,強調對戰略環境作系統、全面的分析,注重投資環境,“謀定而后動”,重視權變;在戰略選擇及評價階段,主張同業合并、聯合經營,多元化經營與專一經營相結合;在戰略實施及控制階段,注重戰略執行,實行層級管理、民主管理和成本計算制,堅持“全員訓練”和“全面訓練”,嚴格考核與獎懲,重視職工福利待遇,加強財務管理,完善財務制度。但是,其管理思想多為價值層面的指導,而忽視了實際操作層面。
近代;民族企業;戰略管理思想
一個規范的、全面的戰略管理過程,可大體分解為三個階段:戰略分析階段、戰略選擇及評價階段、戰略實施及控制階段。本文擬在現代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相關知識的基礎上,從以上三個方面對中國近代民族企業戰略管理思想及實踐作些探討。
一、強調對戰略環境作系統、全面分析
近代民族企業家深深懂得,民族企業要獲得生存和發展,必須在準確分析、預測環境變化的基礎上制訂企業計劃,指導企業的經營。
1.注重投資環境分析,“謀定而后動”
重謀略的管理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劉鴻生在創辦企業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謀定而后動”。他在創辦企業之時,總是首先根據初步獲得的市場信息,大致提出一個經營目標,然后通過艱苦的調查研究,盡可能獲得充分的信息和情報資料,最后在研究分析各種資料、仔細考慮各方面條件和問題后作出投資決策。他認為:“工廠之創立與發展,須適應經濟環境之條件”。[1]也就是只有投資環境適宜,企業才可能展開正常經營。他創辦上海水泥公司的過程,就十分典型地反映出這種戰略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國內工業和國際貿易迅速發展,上海成為東亞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之一,各行業大興土木,對水泥的需求量不斷增加。劉鴻生通過對水泥的供產銷和國內外競爭等方面的研究,了解到當時國內水泥廠只有5家,年產水泥約130萬桶,而市場需求約200萬桶,國內市場供不應求,而且水泥生產成本低,只要質量過關就不怕外貨競爭,加之生產水泥的原料有50%是煤炭,而自己手中有的是煤。這使劉鴻生感到水泥業大有可為。于是繼火柴廠之后,以水泥業作為投資經營目標。在廠址的選擇上,當時國內大部分水泥廠都設立在出石頭的地方,藉以免去運輸程序,節省運輸費用,而劉鴻生卻把水泥廠設在并非原料產地的上海。在他看來,“上海為萬商云集之地,水陸交通之區,設廠于是,良有以也。況白石一百噸可制造水泥七十五噸,如廠基建在石山近邊,其制就之水泥由火車或船只運至上海,所繳運費較之運白石來滬,其價之昂貴,奚啻一倍。再以水泥運至中途,恐有走漏及偶遭潮濕而損失甚巨。即以不幸論之,船只或遭傾覆,則一船之水泥與一船之白石,其價格相差當為如何也。此乃廠宜設于上海也”。[2]與靠近原料產地的水泥廠相比,劉鴻生的上海水泥廠生產的“象牌”水泥雖然在生產成本上不具優勢,但它產于上海,銷路廣闊,而且產品運輸成本低,因而也擁有自己的優勢,在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
2.把握時局變化,重視權變
在近代民族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一些睿智的民族企業家都認識到,民族企業要生存和發展,必須把握市場變化,在對市場進行科學預測的基礎上確定對策,指導企業經營。張謇的重要經營戰略之一便是“察世變,觀物情”。大生集團內部各企業特別是幾座紗廠的創辦,都是把握時局、抓住機遇的結果。甲午戰爭之后外國資本意欲控制中國,“救亡圖存,實業救國”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在這樣的情勢下,清政府放寬對民間設廠的限制,于是掀起了一股民間辦廠的小小浪潮。同時,在經營過程中,張謇還重視考察環境的動態變化。他認為,在現代競爭市場中“商情變幻,瞬息萬易,營業之計劃,則尤在衡量時局、斟酌市情以權操縱”。[3]在對市場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采取各種辦法順應市場,應對市場變化,常常可以使企業轉危為安。
二、戰略選擇及評價
戰略選擇及評價過程實質就是戰略決策過程,即對戰略進行探索、制定及選擇。
1.同業合并,聯合經營
在近代中國,外商憑借著資本、技術與享有的特權等優勢在中國開礦設廠,傾銷商品,給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生存壓力。在這種形勢下,中國近代民族企業不僅要同國內的同行進行競爭,還面臨著在華外資企業和外國進口產品的競爭。在這種形勢下,民族企業要求得生存和發展,就必須采取合適的競爭戰略。在當時,歐美乃至日本的企業界普遍發生了同業合并的浪潮。中國近代企業界在外國商品的強烈沖擊下,認識到托拉斯組織的龐大勢力,有識之士不斷呼吁中國企業應當同業合并,組成大公司,以增強勢力,抵御外貨入侵。其中同業合并意識最強烈并將之成功付諸實踐的企業家便是劉鴻生。他在1928年指出:“外來火柴充斥,營業競爭,危機潛伏,再三思維,惟有合并數廠為一,以厚集資力人才,藉圖競存”。[4]經過反復磋商和協調,鴻生、熒昌和中華三家火柴廠就合作問題達成共識,于1930年7月組成大中華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劉鴻生出任總經理。次年,他又合并了漢口燮昌、九江裕生、揚州耀楊、蕪湖大昌等華資火柴廠,1934年又將杭州光華火柴廠并入大中華火柴公司,從而使該公司發展成一個擁有8家火柴廠、主導華東和華中火柴行業和市場的壟斷企業集團。1935年成立華中地區火柴產銷管理委員會,次年又成立中華全國火柴產銷聯營總社,劃分了以大中華火柴公司為首的華資火柴廠商和日資火柴廠商的勢力范圍,“產銷聯營總社的成立,控制了全國火柴產銷數量,阻止了走私漏稅,在一定程度上把日資火柴勢力穩在東北和魯豫地區,以維持國產火柴的銷售市場。由于競爭減弱,銷路穩定,售價上升,大中華火柴公司開始獲得了大量的盈余”。[5]此外,劉鴻生還在其他行業多次實施了合并聯營的戰略。譬如,1930~1934年,他的中華煤球廠就和上海的其他煤球廠達成了數份同業聯營協定;1934~1936年,他的中華碼頭公司、章華毛紡廠也和幾家運輸公司、毛紡廠搞了幾份同業聯營協定。
同業合并、聯合經營的戰略,減少了民族企業間的內部競爭,抵擋了外國商品的沖擊,同時為民族企業增加了資本、改進了生產技術、提高了管理效率,因此,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搖搖欲墜的民族工業,保護了本國市場。
2.多元化經營與專一經營相結合
多元化經營是企業分散風險或有效利用經營資源向其他領域發展的戰略,是指企業同時經營兩種以上基本經濟用途不同的產品或服務的一種發展戰略。
民生公司創辦之初,盧作孚就在合川建起了電燈自來水廠,進行多元化經營的嘗試。隨著公司的發展,盧作孚又建成了與航運業相關的民生機器廠、天府煤礦和三峽織染廠。至統一川江航運業以后,盧作孚多元化經營戰略思想更加明確。他指出:“公司事業的重心永遠在航業上則永遠不安全,必須有岸上事業。必須有岸上的生產事業,必須有與交通事業相夾輔的生產事業……因此在航業上既有相當的基礎之后,更應得進一步經營生產事業,庶幾于四川未來之開發問題上有些微幫助”。[6]抗戰期間,盧作孚繼續致力于實現他以民生公司為中心發展其他實業的主張。他一方面極力擴大民生公司的附屬企業,使民生機器廠除能承擔民生公司全部船只的修理以外,還能制造較大的新船,成為大后方最大的民間機器制造廠;另一方面,對七十多個企業特別是與民生公司密切相關的能源、冶金、機器制造等企業進行投資。抗戰時期,盧作孚投資其他產業的數十家企業,大都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為彌補公司航運業虧損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援助。到抗戰勝利前夕,民生公司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之一。
在張謇大生集團的發展過程中,多元化戰略思想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大生紗廠創辦成功之后,張謇陸續創辦了其他各企業。創辦這些企業的初衷,是想讓大生紗廠從原料到廢料再到運輸、銷售一條龍式運行,使南通工農商自成體系,對外地不形成依賴。譬如,為擴大原料來源與改良棉質,創立了通海墾牧公司;為了解決紗廠的生產廢料(棉籽),在大生紗廠附近興辦廣生油廠;廣生油廠設立后,又有大量的下腳油脂、油渣,為解決此問題又創立了大隆皂廠,大隆皂廠利用廣生油廠的下腳油脂制造肥皂、蠟燭;為解決設備制造和維修問題,又創辦了資生鐵冶廠;為解決新式棉紡工業對動力的需要,還建立了電力工業和輪船公司;為了使大生各企業的原料、成品更便于運輸和銷售,便籌建以通州為樞紐的交通運輸企業;此外,還投資了釀造公司、印書局、銀行、面廠、房地產公司、漁業等多家公司。至20世紀20年代,大生系統已形成一個龐大的企業資本集團,企業與企業之間彼此關聯,一個企業的產品或廢料,往往成為另一個企業的資源,進行延續生產或回收再生產,使企業集團可以不依賴外界而獨立生存、運轉。
由此可見,近代民族企業家這種以主營業為龍頭、逐漸向其他行業拓展的多元化經營戰略,在民族企業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是其戰略思想實踐成功的有力證明,也為當今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三、注重戰略執行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興起了以泰勒的“科學管理”為代表的管理制度變革浪潮,一些思想比較先進的民族企業家開始主動接受、傳播和運用這種思想,希望借此提高企業管理效率和生產效率。許多管理理念與方法頗具開創性和先進性。
1.組織管理思想
企業為了確保戰略順利實施,必須建立與戰略相適應的組織機構,明確各自的責任和權利,同時按照戰略所需及時調整。
在組織管理方面,盧作孚提出了“建立秩序”的思想。他指出“管理的要求在使整個事業中人力物力配合活動達到最高效率,即要求以最少人力、最少物力、最快時間,換得最多結果、最好結果”,“管理的主要方法為建設秩序,建設人的秩序、物的秩序,成文的規章、不成文的習慣,皆應確立秩序,秩序以成文表現之即系‘法’,而主持一個機關或一個事業,第一任務即在建設一個機關或一個事業的秩序,‘組織’即完成一個機關一個事業的秩序”。[7]盧作孚在這種“建立秩序”思想的指導下,經過十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到1937年左右,民生公司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效益較高的管理體制,即總經理集權制與分級管理、分工負責管理體制。
民生公司成立以前,中國航運業普遍實行的是“買辦制”的管理體制。所謂“買辦制”是指公司把輪船上各項業務分別包給買辦辦理,從上到下,層層買辦,形成各種利益小團體,公司無權干涉,因此管理相當混亂,互相傾軋,效率極其低下。盧作孚在民生公司成立之初,便廢除了“買辦制”,實行“四統制”。即船上人員統一由公司任用,任人唯賢,不準濫用私人;船上財務統一由公司掌握,一切收入歸公司,不得營私舞弊;船上燃料、油料消耗統一由公司定額核發、節約有獎;全船由船長統一指揮。[8]這種以總經理為首的總公司集權的管理體制,高度集中了公司的人力、財力、物力,為民生公司迅速發展提供了保證。
盧作孚在采用集權模式的同時也特別注意層級管理,認為“不宜事事均達到上層,更不宜事事均到最上層”,“必須每一階層各有應負的責任,各有其負責處理的問題”。[9]為此,盧作孚對不同人員制定了不同要求的工作手冊,對各類人員每年、每月甚至每日的工作內容、程序及職責范圍都有具體詳盡的規定。層層節制、分級管理制度的施行,保證了民生公司的有效運作。同時,盧作孚為了加強各部分的橫向聯系,建立了各種制度機構,如各級聯席會議制度,成立人事委員會、駕駛研究委員會、業務研究委員會等。
民主管理是盧作孚組織管理的另一特色,特別是主張把企業領導放在群眾監督之下,受群眾監督的觀點在當時也是罕見的。他提出:“最高才能的領導者,不在其個人天才監督人群,而應建立群的秩序監督個人,不但應當發揮每一個工作人員的能力,尤其應當發揮整個社會組織的能力”。[10]在實際領導工作中,盧作孚實施了許多發動員工獻計獻策、參與決策的措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盧作孚在民生公司建立了各種各樣的會議制度。如每天一次的聯席會議、每周兩次的“朝會”和不定時召開的部處聯席會等。同時對會議在發言時間、會議主題等方面作出了明確要求,以提高會議的效率。
盧作孚在組織管理方面的理論和實踐,實際上是對現代企業事業部制的較早運用,并且創造性地將這種制度與民主管理相結合,不僅在當時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即使在今天也仍有推廣價值。
2.成本管理思想
張謇是近代中國最早提出成本管理思想的民族企業家。他認為“各工廠制造之貨,非減輕成本,不足以敵外國進口之貨。”指出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并在其經營的企業施行了一系列成本管理的措施:(1)成本計算制。規定每天要編制相應的成本計算表,分送給經理、銀行和主管人員,并在表上注明原料、產品的市價,經營的盈虧,工作的效率等,以便了解經營狀況,對成本及時監控。(2)領用和消耗的計劃分析。各部門對當天要使用的人力、原材料、燃料事先作好計劃,按計劃領取,當天晚上統計實際消耗,從而大大降低了企業的成本。(3)節約開支。張謇從辦廠開始就力求節儉,這對于降低總成本具有積極作用。(4)改進技術。通過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從而降低產品單位成本。
張謇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將其成本管理思想付諸于實踐并獲得了成功,建立了比較全面的成本管理制度,對企業各部門、各環節都進行了有效的成本控制,降低了成本,提升了企業競爭力,這在中國當時是獨一無二的。時至今日,雖已時過境遷,但其中仍有值得借鑒之處。
3.人事管理思想
傳統的企業管理長期比較重視物的因素,隨著西方科學管理思想的傳入,一些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民族企業家逐漸開始了“以人為本”管理企業的思考,并在實踐中把人才問題作為事業的基礎工作,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頗多建樹。(1)擇人用人是關鍵。劉鴻生曾提出:“缺乏具有經營管理能力以及訓練有素的人才,成為企業經營管理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要辦好一個企業,首先得物色好專門人才,沒有人才,不可冒昧從事”。[11]盧作孚認為:“人事管理之第一要義在用人,用人之第一要義在為事擇人”。[12]可見,民族企業家已經認識到企業經營過程中選拔人才和發現人才的重要性。在擇人用人的標準上,盧作孚堅持用人唯賢,提出“重才干和品行”、“不徇私情”的標準。劉鴻生也有自己的用人標準:“量才使用,人盡其才”。他認為人無完人,才無通才,“好人有好人的用處,壞人有壞人的用處,全才有全才的用處,偏才有偏才的用處,要學會善用他們”。[13](2)“事業即學校”。人員培訓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方面,同時也是企業提升人力資源水平的重要途徑。盧作孚在創辦民生公司之初,就十分重視職工的知識教育和技能訓練,始終堅持“全員訓練”和“全面訓練”。他曾指出“事業即學校,且系最實際的學校”。[14]為此,民生公司不惜重金開展了對職工的培訓,通過舉辦各種短期和長期訓練班,建立培訓學校,創辦企業刊物,開展文化活動等方式,對包括管理人員在內的全體職員進行培訓。培訓的內容涉及專業技能、職業道德、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這種把教育和實業結合起來的全面培訓方式,在當時中外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史上是一種創舉,也為民生公司贏得了“社會大學”的美譽。其他的民族企業家如穆藕初、宋棐卿、劉鴻生、范旭東等,在所創辦企業中也都設立了培訓班、培訓學校。通過這些培訓提高了民族企業的職工素質,為民族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大批專業人才。(3)嚴格考核與獎懲。職工被聘用以后,為合理使用人才,使其更好地為企業發展服務,提高企業效率,制定合理有效的人員考核制度十分關鍵。盧作孚認為:“全體職工在行為、能力、工作業績上都須有明白之標準以資考察及比較”。[15]為此,民生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規章制度和考核標準,作為對職工行為和業務考核的依據。如《民生公司考勤通則》、《民生公司給假規程》、《辦事細則》、《職員手冊》及各種“須知”等。同時,為具體考核職工的業務、品行、服務態度及對公司的忠誠度,公司還制作了各種考績表格,由主管依照此表考核每人成績,并逐項登記。[16]劉鴻生也比較重視對職工的考核,主要針對行為和業務兩個方面。1930年,大中華火柴公司還專門設立了用于考核其員工的考工科。“關于工人的進退、調動、升降、懲獎、請假、考勤等等,均由考功科負責”。[17](4)重視職工福利待遇。人才的使用,不僅要人盡其才,而且要重視人才之所需,在物質上關心職工,重視職工福利待遇,解決職工的后顧之憂。盧作孚指出“人事管理的另一問題,在謀職工的福利,不僅為謀當前福利,并須為謀未來福利,不僅謀個人福利,并須為謀家庭福利”。[18]把重視職工福利看作是調動職工生產積極性的基本措施,給職工提供了優厚的待遇,如免費膳食、免費就醫、免費宿舍、養老撫恤、文體活動設施等。其他民族企業家也十分重視職工的福利待遇,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
4.財務管理思想
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在發展初期,由于缺乏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一些企業曾出現資金混亂與浪費的現象。民族企業家深感其弊端,主張加強財務管理,完善財務制度。如盧作孚認為:“任何機關和事業之業務能發展到何種程度,皆以財務為決定之條件,工商事業尤以財務決定其成敗”。[19]為此,民生公司建立起了集財權于總公司的財務制度。在總經理室下設立會計處(或稱財務處),下設出納、會計、統計、船賬、審計五個科室(股)。全公司的預算、收支、盈余分配計算以及成本核算與統計等都由會計處統一執掌,總公司所屬船只、碼頭、分公司或辦事處雖有財會收支業務,但不能進行獨立核算,有關工廠雖有成本核算,但不自負盈虧,盈余虧損仍由總公司會計處統一掌握使用。這種制度對民生公司在集中使用財力應對外部競爭、保證資金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近代民族企業家在長期實踐中大膽吸收外國先進的管理理論,并努力與中國當時的國情相結合,充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形成了內涵豐富的管理思想,留下了經營管理近代企業的寶貴經驗。但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統管理思想,往往注重的是價值層面的指導,而忽視了實際操作層面。因此我們在發掘近代企業管理思想的同時,必須廣泛吸收西方的先進管理理論和管理經驗,融會貫通中西方管理理念,促進管理思想發展和創新,讓最先進的管理思想為我所用。
[1]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劉鴻生企業史料(下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
[2]、[4]、[17]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劉鴻生企業史料(上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50、299-300、349.
[3]通州大生紗廠第十一屆說略[Z].1909.
[5]、[11]、[13]劉念智.實業家劉鴻生傳略[M].北京: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19、60、60.
[6]盧作孚.增加股本是公司當前最大的問題[J].新世界,1936(3):31-32.
[7]、[9]、[10]、[16]、[18]凌耀倫,熊甫.盧作孚文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581-582、584、585、242-243、586.
[8]凌耀倫.民生公司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98.
[12]盧作孚.盧作孚文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585.
[14]、[15]盧作孚.盧作孚談業務管理[J].新世界,1945,30(2):48-50.
[19]凌耀倫,熊甫.盧作孚集[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468.
On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Thinking of China’s Modern 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ir Practices
OU Shao-hua
(Hunan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Hunan412008,China)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s,China's modern national entrepreneurs developed abundant management thinking. At the stage of strategic analysis,they emphasized the systematic and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nd contingency;at the stage of strategic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they advocated horizontal merger,joint oper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diversified and specified operation;at the stage of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the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carried out hierarchical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cost accounting,strengthened cultivation of employees,paid more attention to evaluation and rewards and punishment,strengthened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improved financial system.But they paid excessive attention to guidance in the level of value and neglected that in the practical level.
modern China;national enterprises;strategic management thinking
F279.33
A
1007-8266(2013)04-0067-05
歐紹華(1964-),男,湖南省武岡市人,湖南工業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主要從事企業文化與管理思想史研究。
林英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