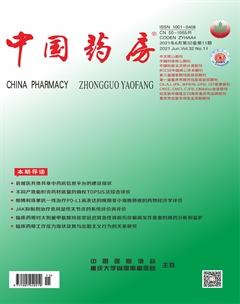臨床藥師工作壓力現狀及其與出勤主義行為的關系研究
裴佩 徐懷伏


摘 要 目的:調查我國三級醫院臨床藥師的工作壓力和出勤主義行為的現狀并研究二者的相關性。方法:采用工作壓力簡潔量表(BJSQ)以及出勤主義行為單項問卷,對我國31個省份共311家三級醫院的623名臨床藥師進行調查。通過建立工作壓力及其各維度(工作需求、工作控制、支持)與出勤主義行為之間的Logistic模型,對二者的調查結果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受訪臨床藥師的工作壓力平均分為36.75分;發生出勤主義行為的概率為20.38%。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臨床藥師工作壓力及其2個維度(工作需求、工作控制)與其出勤主義行為呈顯著正相關(P<0.05)。結論:我國三級醫院臨床藥師工作壓力較大,這也是引起其出勤主義行為的主要原因;可通過降低臨床藥師工作壓力(例如適當增加人員配置、提供合理的休息時間、提高臨床藥師的工作替代性)以減少其出勤主義行為的發生。
關鍵詞 工作壓力;出勤主義;臨床藥師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job stress and presenteeism behavior in tertiary hospitals of China and study their correlation. METHODS: Using the Brief Job Stress Questionnaire (BJSQ) and the presenteeism behavior individual questionnaire, a survey of 623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311 tertiary hospitals from 31 provinces in China was conducted; by establishing Logistic model between job stress, its various dimensions (job demand, job control, support) and presenteeism behavior,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their survey results. RESULTS: The average job pressure of the interviewed clinical pharmacists was 36.75 points; the probability of presenteeism behavior was 20.38%.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job stress and its two dimensions (job demand, job control)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resenteeism behavior (P<0.05). CONCLUSIONS: The job stress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in tertiary hospitals in my country is relatively high, which is also the main reason for their presenteeism behavior. Job stress can be reduced (such as increasing the staffing appropriately, providing reasonable rest time, improving the job substitution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to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presenteeism behavior.
KEYWORDS? ?Job stress; Presenteeism; Clinical pharmacist
臨床藥師是醫療團隊中的重要組成人員,保障著臨床藥學服務的安全與質量[1]。由于工作時間過長、技能和社會支持不足等原因,臨床藥師常面臨著較大的工作壓力[2]。長期以來,由于三級甲等醫院門診數量的不斷增加,臨床藥師的人員編制相對不足,導致藥師的工作量超負荷、工作壓力陡增,嚴重影響了藥師的工作質量和患者用藥安全[3]。面對這樣大的工作壓力,臨床藥師能否保持良好的出勤狀態已成為相關學者關注的問題。出勤主義行為(presenteeism)是目前研究員工出勤情況的重要概念,是指員工在生病、壓力太大或有其他事情而無法專心工作時還必須照常上班的情況[4]。該理論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優秀的出勤表現”;隨后,學者們也逐漸認識到出勤主義的消極影響(例如工作效率降低、工作產出減少、員工身心健康無法恢復等),開始從多個角度分析研究出勤主義行為[5]。目前,學者間已達成基本共識,即較高的出勤主義水平會帶來不利影響[6-7]。
目前,國外對社區藥師的出勤主義行為較為關注,或是在了解所有臨床工作者的出勤主義行為時考慮了臨床藥師,但也缺乏對臨床藥師職業人群的單獨研究,導致臨床藥師的出勤主義行為數據缺乏客觀準確性[8-9]。在我國,臨床藥師作為醫療衛生體系中的重要角色,目前針對這一群體的工作壓力和出勤主義行為的研究較少,缺乏相關的客觀數據。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全國各地三級醫院共623名臨床藥師進行出勤主義行為和工作壓力現狀的調查研究,旨在了解臨床藥師工作壓力和出勤主義行為的現狀,并分析二者的相關性,以期為醫院管理者提供科學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為使樣本覆蓋范圍更為廣泛,真實反映我國三級醫院臨床藥師的整體工作狀態,本次調研采用多階段抽樣的方法抽取樣本。具體步驟如下:將我國大陸全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納入抽樣范圍。在每個省份,將其下轄全部城市/城區按照其2018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劃分為3個城市組(GDP高、中、低組),31個省份共有93個城市組。以醫院管理者是否愿意在院內開展調研作為依據,使用方便抽樣抽取具體醫院。每個城市組內至少抽取2家三級醫院。在每家醫院中,以是否能找到2名愿意參與調研的臨床藥師并完成調研為依據,使用方便抽樣抽取受訪對象,每家醫院至少抽取2名臨床藥師。調研期間,調研人員使用移動電子設備中的調研軟件打開調研問卷,向受訪者詳細解釋答題要求,口頭朗讀問卷項目以及選擇題的應答項,并使用軟件記錄受訪者的口頭回答。結果,共回收問卷706份,其中有效問卷623份,有效率88.24%。
1.2 研究工具
1.2.1 工作壓力簡潔量表 采用工作壓力簡潔量表(BJSQ)評價臨床藥師的工作壓力情況[10]。該量表共有3個維度,分別為工作需求(job demand)、工作控制(job control)和支持(support);共計15個條目,每個條目按“同意”“基本同意”“基本不同意”“不同意”分為4個等級,依次計1、2、3、4分,其中,工作需求維度的前6個條目(對應工作需求)采用反向計分。對工作壓力的3個維度分別求和,分數越高表明受訪者的工作壓力越大[11]。在本研究中,BJSQ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6。
1.2.2 出勤主義行為單項問卷 根據定義,本研究通過詢問臨床藥師“在過去的1年中,因身心原因感到不適但仍然堅持工作的次數”來測量其出勤主義行為,受訪者可回答“從未”“1次”“2~5次”“5次以上”。本研究將選擇“從未”和“1次”的臨床藥師界定為不存在出勤主義行為,而將選擇2次以上的臨床藥師界定為存在出勤主義行為[12-14]。在本研究中,出勤主義行為單項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8。
1.2.3 其他控制變量 除了工作壓力可能會對藥師的出勤主義行為造成影響外,本研究還考慮了諸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借鑒Cocker等[12]對影響出勤主義的因素的研究,本研究將控制變量分為人口統計學因素和工作因素。在人口統計學因素中,主要測量藥師的年齡、性別、婚姻狀態、孩子個數、個人教育程度;在工作因素方面,主要測量藥師的工作科室、從業年限、職稱、工作資質、從事專業、工作培訓情況等。
1.3 調查方式和數據處理
本次調研均在獲得醫院負責人的許可后進行,事前請受訪臨床藥師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問卷調查在不受干擾的環境下進行。為了避免受訪者隨機選擇答案、確保調查結果的真實性,調研人員要求受訪者充分理解調查問卷的項目和選項后,在移動電子設備上記錄受訪者的口頭回答項目。隨后,采用Excel 2016軟件對數據進行整理,并借助Stata 13.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對出勤主義行為與工作壓力的關系進行相關性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受訪臨床藥師的基本情況
本次調查包括311家三級醫院,受訪臨床藥師共有623名,其中女性409人,男性214人;被調查者整體年齡偏年輕化,其中25~34歲的有342名(占54.90%);已婚的有530人(占85.07%),擁有1個孩子者居多;擁有本科和碩士學歷的共有583名(占93.58%);從業年限在10年以下的有340名(占54.57%);449名受訪者歸屬于藥學部(占72.07%);348名臨床藥師具備中級職稱(占55.86%);有223名(占35.79)臨床藥師經歷了國家專科培訓,工作資質較高;從事抗感染專業的臨床藥師最多,有96名(占15.41%);多數藥師都參與了衛生部組織的臨床藥師培訓(37.40%)。受訪臨床藥師的基本情況詳見表1。
2.2 受訪臨床藥師的工作壓力及出勤主義行為情況
受訪臨床藥師的BJSQ得分見表2。其中,工作需求維度的總分為24分,受訪者平均得分19.58分;工作控制維度的總分為12分,受訪者平均得分6.14分;支持維度的總分為24分,受訪者平均得分11.02分。經求和,工作壓力的總分為60分,受訪臨床藥師的平均得分為36.75分。總體而言,從BJSQ的得分可以看出,臨床藥師正承受著較大的工作壓力。按照受訪臨床藥師的基本特征分類,其中年齡、子女數、學歷、技術職稱和從事專業在工作壓力水平上存在明顯差距,部分組別臨床藥師所承受的工作壓力較大;而性別、婚姻狀況、工作年限、所屬科室或部門、工作資質和參與的培訓等方面,受訪臨床藥師的工作壓力水平基本相差不大。
受訪臨床藥師的出勤主義行為單項調查結果顯示,有過2次及以上感到身心不適仍堅持到崗經歷的臨床藥師有127人(占20.38%),判定該部分受訪者存在出勤主義行為;而從未有過以及只有1次感到身心不適仍堅持到崗經歷的臨床藥師有496人(占79.61%),判定該部分受訪者不存在出勤主義行為。
2.3 受訪臨床藥師工作壓力與出勤主義行為的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中,以是否存在出勤主義行為作為因變量,以工作壓力及其3個維度(工作需求、工作控制、支持)的得分作為自變量,其余控制變量見表1。將收集得到的數據代入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工作壓力及其工作需求、工作控制維度與出勤主義行為顯著相關,比值比(OR)分別為1.076(P<0.01)、1.098(P<0.05)、0.033(P<0.05),即這3個自變量對受訪臨床藥師的出勤主義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還有3個控制變量(年齡、工作資質和從事的專業)對臨床藥師的出勤主義行為有顯著影響,呈顯著正相關(P<0.05)。受訪臨床藥師工作壓力與出勤主義行為的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詳見表3。
3 討論
3.1 臨床藥師工作壓力較大,社會關注度有待提升
由于我國臨床藥師工作制度建立較晚,對其工作狀態與組織行為(如工作壓力、缺勤/出勤行為、組織承諾、管理決策等)的研究相對落后,目前只有較少學者研究臨床藥師工作壓力的相關問題。現有研究中,李晗[15]調查了山東地區100名臨床藥師的心理壓力與職業倦怠的關系,結果發現,臨床藥師心理壓力較大,且心理壓力與職業倦怠高度相關,心理壓力過高可直接導致高程度的職業倦怠,從而引起藥學服務質量與患者滿意度的降低。段露芬等[3]調查了蘇州市4家三級醫院79名靜脈用藥調配中心(PIVAS)藥師的工作壓力現狀,發現因大多數醫院的這一環節明顯存在人手緊缺、工作強度大等問題,故有92%以上的藥師認為自己承受的壓力處于中等以上,并提到出現差錯問責和工作強度是壓力最大的部分。上述研究與本次調研在結果上基本一致,表明我國醫院臨床藥師的工作壓力普遍較大。同時,國家衛生部于2011年頒布的《醫療機構藥事管理規定》中強調臨床藥師要承擔查房、會診等臨床工作,也表明國家對于藥師臨床工作的要求提高了,這也使得臨床藥師的工作壓力正逐漸增加。
關注臨床藥師的工作壓力是為了更好地了解壓力帶來的影響,目前已發現工作壓力會通過組織承諾和工作滿意度等中介變量來調節對藥師離職傾向的影響[16];同時,較大的工作壓力還會給藥師帶來心理健康狀況的負面影響,長此以往還會導致生理上的疾病,最終從多個方面損害藥師的職業健康[7,17]。然而,本研究發現,相較于國外,國內學者對臨床藥師工作壓力的關注度相對較低,不僅研究數量較少,而且針對臨床藥師工作壓力的測量工具的發展也相對不夠成熟、存在年代久遠和數據陳舊等問題[18]。因此,提升對臨床藥師工作狀態的社會關注度很有必要。
3.2 工作壓力與出勤主義行為的相關性較強,但對臨床藥師的相關研究不足
出勤主義行為是指臨床藥師帶病堅持工作的現象[4, 19],其發生不僅可以歸因于員工的身體或心理健康出現問題,也可歸于潛在的社會環境和工作氛圍[6]。本研究的重點是探究臨床藥師工作壓力與出勤主義行為的相關性。國外已有較多研究證明,工作壓力是出勤主義行為的關鍵因素之一[20-23],但缺乏對于臨床藥師這一職業人群的研究及相關數據。本次調研的結果顯示,臨床藥師的工作壓力與出勤主義行為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且在工作壓力的3個維度中,除支持維度以外,工作控制維度和工作需求維度也與出勤主義行為有顯著的相關性(P<0.05)。Schmidt等[24]的研究也發現,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與出勤主義行為存在一定關聯性,并指出減少工作壓力,可影響出勤主義行為的發生,顯著提高生產率和降低成本。事實上,出勤主義行為是一種較差的出勤表現[25],當臨床藥師出現出勤主義行為時,表明該醫療團隊工作效率下降、患者用藥安全存在風險[7],因此應極力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
對此,筆者建議醫院應適當增加臨床藥師的人員配置(如增加實習藥師、編外人員等),從而減少藥師的人均工作量。此外,醫院也要及時做好醫療服務工作的管理,為身體不適的臨床藥師提供合理的休息時間,重點分攤工作替代力較弱的臨床藥師的工作量,提高臨床藥師群體的工作替代性,增加了同事間的相互支持,從而減輕該人群的工作壓力,最終減少其出勤主義行為的發生。
本次調研發現,受訪臨床藥師在過去12個月中有1次及以上身心不適仍到崗工作經歷的藥師比例不到50%,其中被判定為存在出勤主義行為的人數僅占20.38%,與臨床醫師相比這個數據似乎不算高[5],但考慮到這是國內首次對臨床藥師的出勤主義行為進行研究,故仍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因此,雖然本研究在方法上還存在不足,但希望能為臨床藥師出勤主義行為的后續深入研究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 1 ] MASOOD U,SHARMA A,BHATTI Z, et al. A successful pharmacist-based quality initiative to reduce inappropriate stress ulcer prophylaxis use in an academic medical intensive care unit[J].Inquiry,2018,55(1):0046958018- 75911.
[ 2 ] YONG F R. Instruments measuring community pharmacist role stress and strain measures:a systematic review[J/OL].RSAP,2020[2020-11-01].https://doi.org/10.1016/j.sapharm.2020.08.017.
[ 3 ] 段露芬,周琴,劉馨,等.蘇州市4家三級醫院PIVAS藥師的工作強度、疲勞狀況和壓力現狀調查[J].中國藥師,2020,23(2):391-395.
[ 4 ] ARONSSON G,GUSTAFSSON K,DALLNER M. Sick but yet at work. An empirical study of sickness presen- teeism[J]. 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2000,54(7):502-509.
[ 5 ] PEI P,LIN G,LI G,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octors presenteeism and job burnout:a cross-sectional survey study in China[J]. BMC Health Serv Res,2020,20(1):715.
[ 6 ] LOHAUS D,HABERMANN W. Presenteeism:a review and research directions[J]. HRMR,2018,29(1):43-58.
[ 7 ] YANG T,GUO Y,MA M,et al. Job stress and presen-? teeism among Chinese healthcare workers: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ffective commitment[J]. Int J Env Res Public Health,2017,14(9):978.
[ 8 ] FARAH R,MALAEB D,SACRE H,et al. Factors asso- ciated with work impairment and productivity among? Lebanese community pharmacists[J]. Int J Clin Pharm Net,2020,42(4):1097-1108.
[ 9 ] AL NUHAIT M,AL HARBI K,AL JARBOA A,et al.Sickness presenteeism among health care providers in an academic tertiary care center in Riyadh[J]. J Infect Public Heal, 2017,10(6):711-715.
[10] JOHNSON J V,HALL E M. Job strain, work place social support,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a random sample of the Swedish working population[J]. Am J Public Health,1988,78(10):1336-1342.
[11] OTSUKA T,KAWADA T,IBUKI C,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ain and radial arterial wave reflection in middle-aged male workers[J]. Prev Med,2009,49(2/3):260-264.
[12] COCKER F,MARTIN A,SCOTT J,et al. Factors asso-? ciated with presenteeism among employed Australian adults reporting lifetime major depression with 12-month symptoms[J]. J Affect Disorders,2011,135(1/2/3):231- 240.
[13] JOHNS G. Presenteeism in the workplace: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J Organ Behav,2010,31(4):519-542.
[14] KARANIKA-MURRAY M,PONTES H M,GRIFFITHS M D,et al. Sickness presenteeism determines job satisfaction via affective-motivational states[J]. Soci Sci Med,2015,139:100-106.
[15] 李晗.臨床藥師心理壓力對職業倦怠影響研究[J].中國民康醫學,2013,25(8):14-15,33.
[16] GAITHER C A.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 pharmacists future work plans[J]. J Am Pharm Assoc,2007,47(2):165-173.
[17] APPELS A,MULDER P. Excess fatigue as a precursor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J]. Eur Heart J,1988,9(7):758- 764.
[18] 李文君,張婧,黃蓉,等.醫院藥師工作壓力及其測量方法研究現狀[J].中國藥房,2020,31(1):7-11.
[19] ARONSSON G,GUSTAFSSON K. Sickness presenteeism:prevalence, attendance-pressure factors,and an outline of a model for research[J]. J Occup Environ Med,2005,47(9):958-966.
[20] ELSTAD J I,VABO M. Job stress,sickness absence and sickness presenteeism in Nordic elderly care[J]. Scand J Public Health,2008,36(5):467-474.
[21] HUFF J,ABLAH E. Stress and presenteeism among? ? Kansas hospital employees:what stress reduction interventions might hospitals benefit from offering to employees?? ? ? ? ? ?[J]. J Occup Environ Med,2016,58(11):E368-E369.
[22] MACGREGOR J N,CUNNINGHAM J B,CAVERLEY N. Factors in absenteeism and presenteeism: life events and health events[J]. Management Research News,2008,31(8):607-615.
[23] V?NNI K, VIRTANEN P, LUUKKAALA T,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work 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loss[J]. Int J Occup Saf Ergon,2012,18(3):299-309.
[24] SCHMIDT B,SCHNEIDER M,SEEGER P,et al. A comparison of job stress models: associations with employee well-being,absenteeism,presenteeism,and resulting costs[J]. J Occup Environ Med,2019,61(7):535-544.
[25] 胡文娟,陳毅文.出勤主義及其影響因素述評[J].人類工效學,2015,21(6):70-74.
(收稿日期:2020-12-02 修回日期:2021-04-30)
(編輯:羅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