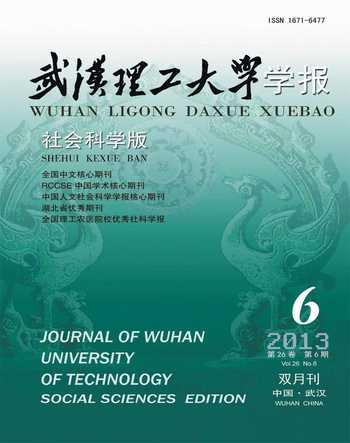論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度”的把握
摘要:在《水滸傳》中,與蘇軾有關的描寫只有三處——高俅的發跡史,玉蘭陪酒唱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宋朝四絕蘇、黃、米、蔡的所指。但三處描寫中兩處存有諸多錯誤,一處則有爭議。從歷史真實的角度分析,三處描寫漏洞明顯,經不起推敲。然而從文學虛構的角度來看,三處描寫卻是成功的,至少與作者的美學觀念和表達的主題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由此觀之,歷史與文學之間的關系,真實與虛構之間“度”的把握,值得認真探討。
關鍵詞:《水滸傳》;蘇軾;歷史真實;文學虛構
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水滸傳》與蘇軾有關的描寫只有三處。三處描寫都是作為故事的背景出現的,初看似乎尋常,深思卻讓人詫異:三處描寫中兩處存有諸多錯誤,一處則有爭議。究竟是作者粗心所致(歷史戲說),還是有意為之(文學虛構的需要)?筆者認為,實有對其作一番探究的必要。
一、《水滸傳》中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描寫
在《水滸傳》中,涉及到蘇軾的三處描寫分別如下:
第一處與蘇軾有關的描寫出現在第二回敘述高俅的發跡史時。閑漢高俅因勾引王員外兒子賭錢,被王員外一紙訴狀告發,斷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流浪到淮西臨淮州;又被閑漢柳世權收留,后因得了赦宥罪犯的機會回到東京;柳世權將高俅薦給東京開藥鋪的董將士,董將仕又將其轉薦給小蘇學士:
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罷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閑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著得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里,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馳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1] 17。
在作者筆下,高俅由于品行很差,被人當皮球一樣推來送去,直到遭際小王都太尉王晉卿才安身。高俅的發跡非常偶然,王晉卿指派高俅給端王送東西,端王發現高俅踢球水平高,不肯放高俅回府,而更為湊巧的是“未及兩個月,哲宗皇帝宴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后來沒半年之間,直抬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1]20。
第二處與蘇軾有關的描寫出現在第三十回的玉蘭陪酒唱的詞曲上。張團練買通張都監設計陷害武松,中秋之夜,張都監設家宴宴請武松,張都監的養娘玉蘭陪酒唱的詞曲是蘇軾最為著名的曲子詞《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那張都監指著玉蘭道: “這里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個。”玉蘭執著象板,向前各道一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一只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卷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萬里共蟬娟。”[1]399
第三處與蘇軾有關的描寫出現在第三十九回和第四十回的關于宋朝四絕蘇、黃、米、蔡的定義上。在第三十九回,梁山英雄為救宋江,需要戴宗給江州知府蔡九送一封假信保住宋江的性命:
晁蓋愁道:“好卻是好,只是沒有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1]542
在第四十回,因這封假信本是父親寫給兒子的家信卻錯用了蔡京的名諱圖章,以致被無為軍通判黃文炳識破。作者通過黃文炳的嘴再次明確蘇、黃、米、蔡的蔡為蔡京,黃文炳告訴蔡九道:
“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況兼這個圖書,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如今升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1]549
上述三處有關蘇軾的描寫,都是背景材料,談不上對蘇軾的褒貶,作為蘇軾研究者,大可一笑置之,而且小說家言,似也沒有較真的必要。但《水滸傳》作為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之一,僅僅三處涉及蘇軾的描寫就出現諸多錯誤,似又有辨證和分析的必要。
二、對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描寫的辨析
《水滸傳》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描寫,從歷史真實的角度看,可以說漏洞百出;而從文學虛構的角度說,作者這樣處理又體現了藝術的真實。
從歷史角度看,《水滸傳》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描寫中兩處與歷史真實存在較大差距,一處存在爭議。
第一處敘述高俅發跡史時與蘇軾有關的描寫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小蘇學士究竟指誰?宋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才識》記載:“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也。”[2]按照王辟之的說法,老蘇指蘇洵,大蘇指蘇軾,小蘇指蘇轍。從小蘇學士處置高俅的簡單描寫看,倒也符合蘇轍的為人處世態度——謹小慎微,不與“幫閑浮浪的人”交往。但考諸歷史,高俅實乃“東坡先生小史”,將高俅送給王晉卿的實際上是大蘇而非小蘇,南宋王明清的《揮麈后錄》“高俅本東坡小史”條載:“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扎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3]138王明清的記載很明確,蘇軾出帥定州,先是將高俅送給曾布,曾布婉辭才轉送給王晉卿的。換句話說,將高俅送給王晉卿的是大蘇學士蘇軾而非小蘇學士蘇轍。熟悉宋朝歷史和蘇軾情況的人都知道,蘇軾出帥定州在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當時高太后去世、哲宗親政,政治形勢驟變,蘇軾已經預感到“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4]。因此,蘇軾將跟隨自己的小史高俅妥善安置,正是蘇軾為人負責的一貫作風。先是“留以予曾文肅”,大致原因有三:一是曾文肅(曾布)是曾鞏的弟弟,與蘇軾兄弟存有私交;二是曾文肅是新黨人物,在即將到來的政治變局中,可能占據有利位置,需要“筆扎頗工”的“小史”;三是可以為高俅提供一個安身之處。在曾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的情況下,蘇軾將高俅轉送給王晉卿,更是在情理之中。蘇軾與王晉卿關系非同一般,過從甚密,根據“烏臺詩案”蘇軾的交代材料,早在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雙方就有交往:“熙寧二年,軾在京授差遣,王詵作駙馬。后軾去王詵宅,與王詵寫作詩賦,并《蓮花經》等,本人累經送酒食茶果等與軾。當年內王詵又送弓一張、箭十只、包指十個與軾。”[5]這種交往歷經“烏臺詩案”的考驗,一直延續到元祐時期①。
二是駙馬王晉卿身份出現明顯錯誤。考諸史實,《宋史·王全斌傳》附其曾孫《王凱傳》載:“子緘,緘子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國長公主,官至留后。”[6]8926而據《宋史·公主傳》記載,英宗四女,蜀國長公主為英宗第二女,“魏國大長公主,帝第二女,母曰宣仁圣烈皇后。嘉祐八年,封寶安公主。神宗立,進舒國長公主,改蜀國,下嫁左衛將軍王詵”[6]8779。王晉卿所尚蜀國長公主是神宗皇帝一母同胞的親妹妹,是哲宗皇帝、徽宗皇帝的親姑姑。《水滸傳》作者將王晉卿輩分降了一輩,認為王晉卿“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明顯把輩分弄錯了。
三是關于高俅的描寫失真。《水滸傳》描寫的高俅劣跡斑斑,是將林沖等好漢逼上梁山的罪魁禍首,是《水滸傳》里最主要的反派角色,但王明清《揮麈后錄》“高俅本東坡小史”條載:“然不忘蘇氏,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恤甚勤。靖康初,佑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為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于牖下。(胡元功云)”[3]138從王明清的記載看,歷史上真實的高俅并不是一個惡貫滿盈的壞蛋:一是高俅對蘇軾頗有情義。在徽宗統治的絕大部分時期,蘇軾其人其文屬于禁區,政治上被打入另冊,詩文處于被取締狀態。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蔡京拜相,極力主張繼續追貶元祐黨人,查禁元祐學術:“蔡京籍文臣執政官文彥博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蘇軾等三十五人,馀官秦觀等四十八人,內臣張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等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7]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和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朝廷又兩度重申除毀蘇軾諸人文集的禁令。在這樣的政治高壓形勢下,曾與蘇軾有過交往的人士遇蘇氏子弟避之惟恐不及,邵博《聞見后錄》載:“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家廟像。后東坡南遷,公麟在京師遇蘇氏兩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日所有公麟之畫于人。”[8]高俅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在恩寵無比之時,仍然能夠“不忘蘇氏,其子弟入都,則給養問恤甚勤”,這比落井下石的文人似乎還高一等。二是高俅并非當時臭名昭著的“六賊”之一②,并非蔡京、童貫似的千夫所指,與蔡京、童貫、梁師成的結局也不同。蔡京被寫入《奸臣傳》,童貫、梁師成遭到誅殺,而高俅算是自然壽終:靖康初年,高俅因為疾病,隨駕至臨淮時辭職回到京師汴梁,不久病死于家里——“俅獨死于牖下”。
第二處描寫玉蘭唱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同樣出現了三處錯誤:一是將“又恐瓊樓玉宇”改成了“只恐瓊樓玉宇”,二是將“轉朱閣”改成了“高卷珠簾”, 三是將“但愿人長久,千里共蟬娟”改成了“但愿人長久,萬里共蟬娟”[9] 。從藝術角度看,三處改寫與原作有霄壤之別。
第三處描寫關于宋朝書法“四絕”的所指存在爭議。宋朝書法“四絕”, 又稱“宋四家”,一般指蘇、黃、米、蔡。 蘇、黃、米指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不存在爭議,而蔡,按《辭海》的解釋,指蔡襄[10]而非蔡京。由于聲名狼藉,蔡京一般被排除于“宋四家”或宋朝書法“四絕”之外。第三處描寫將蔡指為蔡京,與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并列,與通常流行的看法有別,是存在爭議的。
綜上所述,不能說《水滸傳》三處與蘇軾有關的文字一點根據都沒有,但大都張冠李戴,雖然有歷史的影子,但都嚴重變形。
從文學的角度分析,《水滸傳》描寫蘇軾的文字存在明顯的歷史錯誤,那究竟是因作者粗心,還是其有意為之呢?筆者認為,雖不能完全排除作者因粗疏造成的錯誤,但更可能與作者的美學觀念、表達的主題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有關,也就是說,極有可能是作者對歷史的有意改寫。
首先,可能與作者的美學觀念有關。人物類型化是中國傳統小說塑造人物所遵循的基本美學原則——好人與壞人涇渭分明,好人從小都好,從頭到腳都好,而壞人從小都壞,從頭到腳都壞。從《水滸傳》作者秉持的美學觀念來看,高俅發跡史中存在的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了。作為貫穿水滸全書最重要的反派角色,高俅一出場就被完全定型:出身不好——“浮浪破落戶子弟”;不務正業——“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球”“只在東京城里城外幫閑”;品行不好——“這人吹彈歌舞,刺槍使棒,相撲頑耍,頗能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卻是不會”;有犯罪前科——勾引王員外兒子賭錢“斷了四十脊杖”;人緣很差——“東京城里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收留他的人是“開賭坊的閑漢柳大郎”這樣的社會閑雜人員。一般人對高俅是避而遠之的,故董將仕將高俅推給小蘇學士,小蘇學士又將高俅推給小王都太尉。董將仕、小蘇學士是不喜歡高俅這類“幫閑的破落戶”的。因此,歷史上是大蘇(蘇軾)還是小蘇(蘇轍)將高俅送給小王都太尉并不重要(小蘇或者大蘇在小說中的作用實際上與董將仕相同,只是為了反襯高俅為人的不堪;作者用小蘇代替大蘇,更有利于對高俅形象的塑造,也更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值得我們注意的倒是對小王都太尉輩分的改動。王晉卿與蘇軾同年,生于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如果王明清記敘“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將高俅送給王晉卿屬實,時間當在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王晉卿是年57歲。接近花甲之年的王晉卿,即使如小蘇學士認為的“喜歡這樣的人(幫閑浮浪的人)”,與高俅、小舅端王(后來的宋徽宗)在一起廝混,輩分上不合適,年齡上差距過大,作為玩伴多少顯得牽強,反不如“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更為合情合理。
總之,不管作者是有意改動歷史還是無意出現的知識錯誤——小蘇大蘇身份的混淆、高俅身份上的錯誤以及小王都太尉輩分上的錯誤——這些都更符合中國傳統小說塑造人物所遵循的基本美學原則。換句話說,小蘇大蘇身份的混淆、高俅身份上的錯誤以及小王都太尉輩分上的錯誤,是小說塑造人物時“必須的錯誤”。《水滸傳》中的高俅必然也必須是徹頭徹尾的邪惡——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先決條件,也是作者美學觀念導致的必然結果。
其次,可能與作者要表達的主題有關。《水滸傳》的主題,簡單來說是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表面上看主角是梁山108位好漢,但仔細分析,高俅才是撬動梁山好漢造反的原動力,才是《水滸傳》暗中真正的主角。金圣嘆對此有精到的見解:“一部大書七十回,將寫一百八人也。乃開書未寫一百八人,而先寫高俅者,蓋不寫高俅,便寫一百八人,則是亂自下生也;不寫一百八人,先寫高俅,則是亂自上作也。亂自下生,不可訓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亂自上作,不可長也,作者之所深懼也。一部大書七十回,而開書先寫高俅,有以也。”[11]43對于高俅的發跡,金圣嘆進而指出:“小蘇學士,小王中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豈得哉!”[11]46金圣嘆的看法既精到但也存在片面性。小王都太尉,特別是小舅端王(徽宗)與高俅的發跡的確有關系,金圣嘆用“群小”指代不無道理,但將小蘇學士包含在“群小”當中就明顯牽強。小蘇學士與高俅不同道,甚至與小王都太尉不同道:“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罷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閑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著得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里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歡這樣的人。’”金圣嘆見到“小蘇學士,小王中尉,小舅端王”中同樣有“小”字就斷定是“群小相聚”使高俅發跡,多少有脫離文本望文生義、主觀臆斷的嫌疑。另外,還需指出的是,金圣嘆腰斬水滸,其實有削弱他自己所說的“亂由上作”的主題之嫌。100回本以高俅始并以高俅終,更能突出“亂由上作”的主題。魯迅對金圣嘆尋求伏線及腰斬水滸的做法曾有尖銳的批評:“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并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余;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余蔭,便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于《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自稱得到古本,亂改《西廂》字句的案子且不說罷,單是截去《水滸》的后小半,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12]。
再次,可能與作者對人物形象的塑造有關。如果說第一處出現的諸多錯誤與塑造高俅形象有關,那么第二處、第三處出現的錯誤或者爭議同樣與塑造人物形象有關。玉蘭唱的“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即《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這是一首稍有文化的中國人都熟悉的詞。其中出現的三處錯誤,當然可以理解為作者學識的粗疏,但其實存在另外的可能:玉蘭作為下層歌女,文化層次不高,其主人張都監也非文才之士,作者將著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讓玉蘭唱錯,更符合下層歌女的身份,也隱含了對張都監等人附庸風雅的諷刺。至于將蔡京與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并列為“宋朝‘四絕’”,主要是為了突出蔡九的身分特殊,是為了塑造人物形象和情節發展需要作出的特殊界定。因此,不管作者是有意還是無意,《水滸傳》有關蘇軾的三處錯誤或者爭議,對于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均可以看作是必須的、有意的錯誤。
綜上所述,《水滸傳》三處與蘇軾有關的描寫,從歷史真實的角度上說可能經不起推敲,但從文學虛構描寫的藝術真實的角度上看卻是非常成功的,至少與作者的美學觀念、表達的主題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
三、《水滸傳》敘事美學的啟示
從敘事美學角度分析,《水滸傳》中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描寫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的關系問題,二是人物描寫的類型化問題。這兩個問題對文學創作都很重要。
首先,文學創作中應該如何處理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的關系。這是評判《水滸傳》中三處與蘇軾有關的敘寫文字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歷史要求真實,文學崇尚虛構,如何處理歷史與文學、真實與虛構的關系,是歷史小說不能回避的問題。《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都面臨這個問題,魯迅先生在評論《三國演義》處理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關系時有一段著名的話:“容易招人誤會。因為中間所敘的事情,有七分是實的,三分是虛的;惟其實多虛少,所以人們或不免并信虛者為真。如王漁洋是有名的詩人,也是學者,而他有一個詩的題目叫‘落鳳坡吊龐士元’,這‘落鳳坡’只有《三國演義》上有,別無根據,王漁洋卻被它鬧昏了。” [13]291《三國演義》文字的七實三虛的確容易造成誤會,但《水滸傳》中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描寫嚴格說并不存在這個問題,從敘事美學角度看,由于與作者的美學觀念、表達的主題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水滸傳》中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描寫不但不存在問題,而且是相當成功的。除非是專門研究蘇軾的專業人士,否則是很難發現其虛構與真實的細微差別的。
不但古典小說面臨著處理歷史與文學、真實與虛構的關系問題,現代小說如《李自成》《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同樣面臨這個問題,特別是現當代小說,由于與歷史真實存在不小的距離,常常遭到人們的質疑與非議。勞倫斯·勒納認為,“對于歷史與虛構之間的關系所作的最好描述,是柯林武德作出的……‘歷史學家的圖畫意在真實’”[14]。而文學就其本質來說,是虛構的敘事藝術。在《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古典小說的敘述和描寫中,盡管與歷史真實多有不合,但一直雄居中國古典文學經典之列,關鍵在于人們把《水滸傳》《三國演義》當小說看,而不是當歷史教科書看。人們對現代小說如《李自成》《康熙大帝》《雍正王朝》質疑或者非議,其實與今天的時代思潮有關:“在一個務實的、追求‘真實’而非崇尚想象力的時代”,“敘事尤其是虛構敘事正在迅速地沒落。這是一個論證和論爭的時代,而不是敘事或講故事的時代……因為虛構敘事既不能提供論證也不能提供信息”[15]。直白地說,今天的人們對小說虛構已經缺乏審美的從容,在小說與歷史、虛構與真實之間,更看重后者。這當然不是正確解讀小說的方法。正確的解讀方法是回到文本,這也是胡塞爾現象學運用于文學作品的方法:“由于胡塞爾排除‘真正的客體’,所以文學作品真實的歷史背景、它的作者、產生的條件和讀者都不受重視;現象學批評完全重視的是一種完全‘于意識之內’的對文本的理解,絲毫不受外界事物的影響。”[16]這為我們解決歷史真實與文學虛構關系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回到文本。
其次是人物描寫類型化問題。《水滸傳》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改寫,都與塑造人物——高俅、張都監、蔡九的形象有關。類型化是中國古典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魯迅先生對此曾有精辟論述,在評論《三國演義》類型化人物時曾說:“寫好的人,簡直一點壞處都沒有;而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13]291《水滸傳》里的高俅也是這樣一個“一點好處都沒有”的類型化人物。這種“‘類型化人物’,有時又被稱做‘漫畫式人物’……是作者圍繞著一個單獨概念或者素質創造出來的”[17]232。E.M.福斯特又將其稱為“扁形人物”“體液性人物”,并認為“真正的扁形人物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17]232。高俅就是“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的人物,《水滸傳》里的其他人物也是“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的人物,比如“高俅是壞蛋”,“宋江是及時雨”,“吳用是智多星”,等等。這種“扁形人物”當然有不少優點:“不管他們在小說里的什么地方出現,都能讓讀者一眼就認出來——讀者用的是感情之眼”[17]232,“讀者容易在事后把他們回想起來”[17]232。但這種“扁形人物”的缺陷也是明顯的,魯迅在肯定《紅樓夢》時曾委婉地批評了中國古典小說中的類型化:“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13]306如果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描寫高俅,高俅的形象當更為豐滿、復雜、生動,有可能塑造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給人以驚奇之感”[17]237“變化莫測,如同生活本身一樣難以意料”的“圓形人物”[17]238。《水滸傳》作者受制于自己的美學觀念,受制于主題的表達,給我們塑造了一個扁平型、類型化的高俅形象,這不能不是一種遺憾。當然,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苛求古人。
綜上所述,《水滸傳》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描寫雖然都存在歷史錯誤或者爭議,雖然從中尋找其歷史上的瑕疵是容易的,但文學不是歷史,從文學角度看,三處錯誤或者爭議與作者的美學觀念、表達的主題以及塑造的人物形象一致。因而,可以認為是作者有意為之的。總之,文學與歷史、虛構與真實之間存在相當復雜的關系,類型化描寫也自有其長處和短處,關鍵在于“度”的把握。這是《水滸傳》中與蘇軾有關的三處描寫留給我們最重要、最深刻的啟示。
注釋:
① 蘇軾與王晉卿的關系,張榮國在《王詵與蘇軾之交游》曾有比較詳細的論述(參見《 榮寶齋》2010第5期、第9期)。在《蘇軾詩集》中保留了數量不少的詩文往來,根據筆者統計,僅蘇軾寫給王晉卿的和詩就有30首(參見王文誥、馮應榴編輯的《蘇軾詩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可見二者關系非同一般。
② “六賊”源自陳東在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的上書:“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國,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危如絲發。此六賊異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參見畢沅《續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 2496-2497頁)可知高俅不在“六賊”之列。
[參考文獻]
[1]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百回本[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2] 王辟之.澠水燕談錄[M].隋同文,點校.青州:青州古籍文獻編委會,2008:45.
[3] 王明清.揮麈后錄[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4] 王文誥,馮應榴.蘇軾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1.
[5] 顏中其.蘇東坡佚事匯編[M].長沙:岳麓書社,1984: 285.
[6] 脫脫.宋史 [M].北京:中華書局,1977.
[7] 畢 沅.續資治通鑒[M].北京:中華書局,1957:2244-2245.
[8] 邵 博.邵氏聞見后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3:215.
[9]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2:173-174.
[10]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藝術分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385.
[11] 金圣嘆. 金圣嘆全集一: 水滸傳[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12] 魯 迅.魯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27.
[13] 魯 迅. 中國小說史略[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14] 勒納.歷史與虛構[M]∥閻 嘉.文學理論精粹讀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99.
[15] 耿占春.敘事美學[M].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2:1.
[16] 伊格爾頓. 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理論: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57.
[17] 福斯特.小說面面觀[M]∥童慶炳,趙 勇.文學理論新編.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