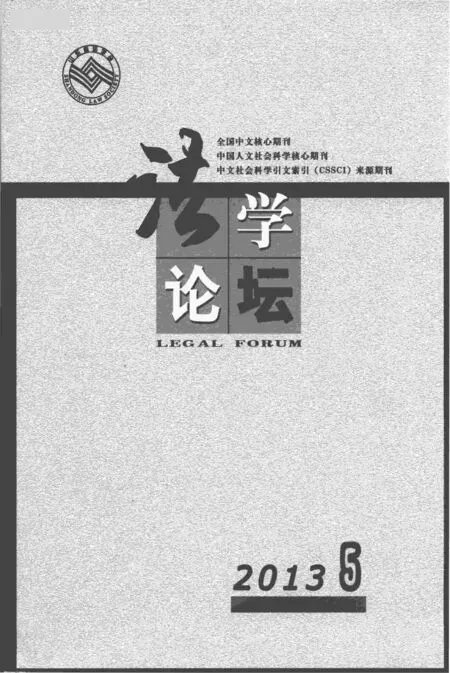論不可反駁的推定
張海燕
(山東大學(xué)法學(xué)院,山東濟(jì)南250100)
一、問題的緣起
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也無論是學(xué)界觀點(diǎn)還是立法明文,對于推定的概念界定大致相同,即在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鳡顟B(tài)下從已知基礎(chǔ)事實(shí)推斷未知推定事實(shí)的一種法律機(jī)制。①廣義而言,推定可以分為有基礎(chǔ)事實(shí)的推定和沒有基礎(chǔ)事實(shí)的推定兩類。有基礎(chǔ)事實(shí)的推定是指推定事實(shí)的推出需要建基于一定的基礎(chǔ)事實(shí)之上。沒有基礎(chǔ)事實(shí)的推定則是指在不需要基礎(chǔ)事實(shí)的前提下法律直接規(guī)定推定事實(shí)的存在,除非存在相反事實(shí),比如刑法中的無罪推定和民法中關(guān)于民事行為能力的推定。本文論及的推定僅指有基礎(chǔ)事實(shí)的推定。在此基礎(chǔ)上,我國學(xué)界對于推定的分類基本達(dá)成共識,即分為法律推定和事實(shí)推定。前者是指法律明確規(guī)定由某一基礎(chǔ)事實(shí)推出另一推定事實(shí),后者是指裁判者根據(jù)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法則從某一基礎(chǔ)事實(shí)推出另一推定事實(shí)。然而,在是否所有推定都可以被反駁這一問題上,卻表現(xiàn)出了不同看法,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所有推定都是可以被反駁的,但也有少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事實(shí)推定全部可以被反駁而法律推定中存在一種不可被反駁的推定。這一分歧在我國2010年10月1日施行的《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58條②該條具體內(nèi)容為“當(dāng)出現(xiàn)如下三種情形之一的,推定醫(yī)療機(jī)構(gòu)有過錯(cuò):(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以及其他有關(guān)診療規(guī)范的規(guī)定;(二)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guān)的病歷資料;(三)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關(guān)于醫(yī)療機(jī)構(gòu)過錯(cuò)推定的規(guī)定中得以凸顯:以王利明教授為代表的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該條規(guī)定的推定是可以被反駁的,即醫(yī)療訴訟中作為被告的醫(yī)療機(jī)構(gòu)可以提出相反證據(jù)證明自己沒有過錯(cuò)從而反駁對于自己有過錯(cuò)的推定;[1]603然而,以梁慧星教授為代表的少數(shù)學(xué)者則認(rèn)為,該條規(guī)定的推定是一種不可反駁的推定,是一種法律擬制,是一種直接認(rèn)定,訴訟中的醫(yī)療機(jī)構(gòu)不能提出相反證據(jù)予以反駁,原告只要能夠證明存在該條規(guī)定的三種情形之一,醫(yī)療機(jī)構(gòu)就絕對存在過錯(cuò)。[2]這種學(xué)者之間理論上的論爭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學(xué)者就是否存在不可反駁的推定這一問題的相異觀點(diǎn),更讓司法實(shí)務(wù)人員在具體的醫(yī)療侵權(quán)訴訟中不知所措。鑒于此,筆者認(rèn)為有必要對不可反駁的推定這一問題進(jìn)行深入探討。
二、存在不可反駁的推定嗎?
所謂“不可反駁的推定”(irrebuttable presumption),①不可反駁的推定,在英美法系國家又被稱為結(jié)論性推定(conclusive presumption)。顧名思義,就是指受推定不利影響的一方當(dāng)事人不能提出任何證據(jù)來反駁推定事實(shí)。要論證是否存在不可反駁的推定,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先回答這樣一個(gè)問題,即為什么有人認(rèn)為推定是可以被反駁的?答案很容易找到,即人們認(rèn)為推定是建立于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存在或然性常態(tài)聯(lián)系這一高概率聯(lián)系基礎(chǔ)之上的,既然從基礎(chǔ)事實(shí)推出推定事實(shí)只是一種或然性常態(tài)聯(lián)系,那就必然存在非常態(tài)的例外聯(lián)系,其結(jié)果便是應(yīng)當(dāng)允許反對推定事實(shí)的一方當(dāng)事人享有提出證據(jù)反駁推定事實(shí)的權(quán)利。那么,是不是所有推定都建立在高概率基礎(chǔ)上呢?如果是的話,則所有推定均可被反駁;如果不是,就有不可反駁的推定的存在空間。此時(shí),是否存在不可反駁的推定這一問題便可推演為是否所有推定的創(chuàng)設(shè)或適用基礎(chǔ)都是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
(一)所有事實(shí)推定的適用基礎(chǔ)都應(yīng)當(dāng)是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
在事實(shí)推定中,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或然性常態(tài)聯(lián)系是推定得以適用的大前提,基礎(chǔ)事實(shí)只有在其涵攝下才能得出推定事實(shí)。關(guān)于兩事實(shí)之間的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注意兩個(gè)問題:第一,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或然性常態(tài)聯(lián)系是一種近似充分條件關(guān)系,基礎(chǔ)事實(shí)存在則推定事實(shí)極有可能存在或不存在。如果兩事實(shí)之間是一種充分條件的邏輯必然關(guān)系,則不存在推定的適用空間,此時(shí)裁判者只能無條件地根據(jù)該邏輯必然關(guān)系得出某一確定事實(shí),該事實(shí)就不是推定事實(shí),就更談不上該事實(shí)能否被反駁的問題了。第二,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或然性常態(tài)聯(lián)系是一種高概率聯(lián)系,只有將其作為經(jīng)驗(yàn)法則,才能保證推定事實(shí)的正當(dāng)性,也才能有效防止裁判者在適用事實(shí)推定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的偏頗或恣意裁判。
(二)法律推定的創(chuàng)設(shè)基礎(chǔ)呈現(xiàn)多元化狀態(tài)而不限于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
法律推定的創(chuàng)設(shè)基礎(chǔ)多數(shù)情況下是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因?yàn)榇蠖鄶?shù)法律推定來源于事實(shí)推定,是立法者(或準(zhǔn)立法者)將那些在司法實(shí)務(wù)中適用較為成熟且為當(dāng)事人所普遍認(rèn)可的事實(shí)推定用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使其發(fā)揮普遍性約束力。比如2011年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2條②該條具體內(nèi)容是“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確認(rèn)親子關(guān)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證據(jù)予以證明,另一方?jīng)]有相反證據(jù)又拒絕做親子鑒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請求確認(rèn)親子關(guān)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張成立。當(dāng)事人一方起訴請求確認(rèn)親子關(guān)系,并提供必要證據(jù)予以證明,另一方?jīng)]有相反證據(jù)又拒絕做親子鑒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請求確認(rèn)親子關(guān)系一方的主張成立。”關(guān)于親子關(guān)系存在或者不存在的推定就是一適例。此種情形下法律推定的基礎(chǔ)便是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因?yàn)樽鳛槠鋪碓椿A(chǔ)的事實(shí)推定必須要建立于高概率基礎(chǔ)之上,這便使得這部分法律推定成為可以被反駁的法律推定。
然而,有些法律推定的創(chuàng)設(shè)并非建基于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或然性常態(tài)聯(lián)系,而是與這種高概率聯(lián)系毫無關(guān)系。這些例外情形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
第一,避免因證據(jù)缺乏而陷入訴訟僵局。比如,關(guān)于同一事故中死亡人員死亡順序的確定,1985年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繼承法意見》)第2條規(guī)定:“相互有繼承關(guān)系的幾個(gè)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確定死亡先后時(shí)間的,推定沒有繼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繼承人的,如幾個(gè)死亡人輩份不同,推定長輩先死亡;幾個(gè)死亡人輩份相同,推定同時(shí)死亡,彼此不發(fā)生繼承,由他們各自的繼承人分別繼承”。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也有類似規(guī)定,《日本民法典》第32條之2規(guī)定:“死亡的數(shù)人中,某一人是否于他人死亡后尚生存事不明時(shí),推定該數(shù)人同時(shí)死亡。”我國臺灣地區(qū)“民法典”第11條規(guī)定:“二人以上同時(shí)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后時(shí),推定其為同時(shí)死亡。”上述條文中作出的關(guān)于死亡人員死亡順序的法律推定與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概率聯(lián)系沒有任何關(guān)系,僅僅是為了避免訴訟陷入僵局而無法繼續(xù)進(jìn)行下去。
第二,對于程序性便利的追求。比如,在普通法中,托運(yùn)人將貨物以良好狀態(tài)交付第一承運(yùn)人,經(jīng)過若干中間環(huán)節(jié),最后承運(yùn)人將貨物交付收貨人時(shí)貨物處于損壞狀態(tài),此時(shí)推定該貨物損壞是由最后承運(yùn)人造成的。此種情形下的推定,其被創(chuàng)設(shè)的基礎(chǔ)并不是出于對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內(nèi)在概率的考量,而是對訴訟中程序性便利的追求。①Edmund M.Morgan,Some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Presumptions.44 Harv.L.Rev.906,1930-1931.和Mason Ladd,Presumptions in Civil Actions.1977 Ariz.St.L.J.275,1977.
上述兩種例外情形下的法律推定既然不是建立在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高概率聯(lián)系基礎(chǔ)之上,其被創(chuàng)設(shè)僅僅是為了促進(jìn)訴訟程序的順利進(jìn)行,故此類情形下的法律推定不允許對方當(dāng)事人反駁。需要注意的是,不以概率為基礎(chǔ)的法律推定肯定是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但反過來,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并非全部都不以概率作為其創(chuàng)設(shè)基礎(chǔ)。大多數(shù)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仍是建立在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概率聯(lián)系基礎(chǔ)之上,只不過是立法者為了實(shí)現(xiàn)特定目的或者滿足特定利益而剝奪了反對推定事實(shí)一方當(dāng)事人提出相反證據(jù)反駁推定事實(shí)的權(quán)利。比如美國1965年通過的《加利福尼亞證據(jù)法典》第621條②該條具體內(nèi)容是“不論其他法律規(guī)定如何,妻子與丈夫同居所生的子女,只要該丈夫具有性能力且能生育,則該子女被結(jié)論性地推定為婚生子女”。關(guān)于婚生子女的推定就是一個(gè)建基于概率基礎(chǔ)上的不可反駁的推定的典型例子;再比如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16(b)條規(guī)定“當(dāng)一個(gè)公司的董事、高管或者持股10%以上的股東在6個(gè)月內(nèi)購買和銷售該公司股票時(shí),推定其進(jìn)行內(nèi)部交易”,這也是一個(gè)建立于概率基礎(chǔ)上的不可反駁的推定。
盡管存在與概率無關(guān)的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但絕大多數(shù)法律推定仍是建立于高概率聯(lián)系基礎(chǔ)之上。概率是創(chuàng)設(shè)法律推定的最核心考量要素,那種不以此為基礎(chǔ)的法律推定僅僅是一種例外而非普遍現(xiàn)象。誠如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在Greer v.United States案中曾主張對于概率的考量是每一個(gè)真正推定的基礎(chǔ)。③Greer v.United States,245 U.S.559,561,38 Sup.Ct.209,62 L.Ed.469(1918).而且,所有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均具有強(qiáng)烈的社會利益和公共政策之價(jià)值指向。
綜上,事實(shí)推定是裁判者根據(jù)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法則從基礎(chǔ)事實(shí)推出推定事實(shí),基于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法則的高度蓋然性,為保障當(dāng)事人訴訟中的對等權(quán)利,事實(shí)推定的適用必然會賦予對方當(dāng)事人提出相反證據(jù)進(jìn)行反駁的權(quán)利,故所有事實(shí)推定都是可以被反駁的。而法律推定的創(chuàng)設(shè)基礎(ch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作為基礎(chǔ),另一類不以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作為基礎(chǔ)。前者可以被反駁,而后者則不可被反駁。因此,作為對于本文前提性問題的回答,在推定范疇中,存在不可反駁的推定,且這種推定只能是法律推定而不能是事實(shí)推定。嚴(yán)謹(jǐn)起見,我們應(yīng)當(dāng)將“不可反駁的推定”稱為“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
三、不可反駁的推定和法律擬制的關(guān)系
法律擬制是指法律在特定情況下把某事實(shí)視為另一事實(shí)并賦予兩事實(shí)相同法律效果的一種制度。例如,我國《勞動(dòng)合同法》第14條第3款規(guī)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滿一年不與勞動(dòng)者訂立書面勞動(dòng)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dòng)者已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dòng)合同。”法律擬制與法律推定都表現(xiàn)為兩個(gè)事實(shí)(A和B)之間的關(guān)系,但是法律擬制的含義是明知B不是A,卻把B視為A,法律擬制中被擬制的事實(shí)B不能被反駁。法律推定的含義是B是不確知的,根據(jù)A推出B,被推出的事實(shí)B多數(shù)情況下可以被反駁但也存在不能被反駁的情形。在法律擬制下,A和B都是明確的,是不需要認(rèn)定的,法律擬制就是立法者明知性質(zhì)不同的兩個(gè)事實(shí)卻賦予其相同法律效果;但在法律推定下,A是明確的,但B是不明確的,需要根據(jù)A去認(rèn)定B。由此,法律擬制和可以反駁的推定之間的界分是非常明確的,僅僅從事實(shí)B能否被反駁這一點(diǎn)上就可以準(zhǔn)確作出判斷。問題的難點(diǎn)在于如何有效區(qū)分不可反駁的推定和法律擬制,因?yàn)閮烧卟幌窨梢苑瘩g的推定與法律擬制那樣能夠直接從事實(shí)B能否被反駁這一點(diǎn)上進(jìn)行判斷,相反,不可反駁的推定和法律擬制表現(xiàn)在事實(shí)B上的外部屬性都是不能被反駁,這便使得理論層面、立法層面以及實(shí)務(wù)層面在此問題上呈現(xiàn)出極其混亂的認(rèn)知和適用狀態(tài)。
基于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與法律擬制在事實(shí)B上的不可反駁這一共同屬性,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是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的交叉地帶,并將其稱為“推定性擬制”或者“擬制性推定”。江偉教授曾在其主編的《證據(jù)法學(xué)》一書中主張:所謂推定性擬制,是指那些當(dāng)事人并未為意思表示,或意思表示不明確的情形下,基于規(guī)范上的要求,擬制有某種意思表示的存在,或?qū)⒉幻鞔_的意思表示,擬制為有特定的內(nèi)容。當(dāng)然,其也承認(rèn),這種擬制與其他擬制迥然有別,實(shí)際上是一種法律上的推定。[3]126此外,陳界融教授主張“原則上講,法律上的推定,如果是強(qiáng)力推定或擬制性推定,不允許當(dāng)事人以反證反駁,除此之外的其他推定,則可允許當(dāng)事人以反證反駁”。筆者認(rèn)為,“推定性擬制”或者“擬制性推定”概念的提出并不科學(xué),其本質(zhì)上是無法對法律擬制和不可反駁的推定進(jìn)行有效區(qū)分的一種“四不像”產(chǎn)物。[4]立法層面的混亂狀況同樣存在且非常嚴(yán)重。一般而言,法律推定制度往往通過“推定”語詞予以表達(dá),而法律擬制制度則往往通過“視為”語詞予以表達(dá)。筆者曾以2011年司法考試大綱中“民法”(增加《婚姻法解釋(三)》)和“民事訴訟法”(不包括《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列出的所有規(guī)范性民事法律文件為分析樣本,對檢索到的17處“推定”語詞以及159處“視為”語詞進(jìn)行過實(shí)證分析,發(fā)現(xiàn)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制度最容易產(chǎn)生混淆的情形發(fā)生在對民事主體主觀意思的規(guī)定,22處用“視為”表達(dá)出來的主觀意思,其中有19處之多是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而僅有2處是“視為”通常所表達(dá)的法律擬制。比如《民法通則》第66條規(guī)定的“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義實(shí)施民事行為而不作否定表示的,視為同意。”該條就是典型的用“視為”語詞表達(dá)出來的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制度。不難想象,理論和立法層面上的混亂肯定會對司法實(shí)務(wù)人員的認(rèn)知產(chǎn)生影響。筆者不認(rèn)同有學(xué)者提出的認(rèn)為法律擬制和不可反駁推定之間區(qū)分僅具理論意義而無較大實(shí)踐意義的觀點(diǎn)。[5]之于司法實(shí)務(wù)人員而言,雖然混淆對于不可反駁的推定與法律擬制之間的界分不會直接引起實(shí)務(wù)操作上的不利影響,但這種對于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混沌的思想認(rèn)知狀態(tài)有時(shí)卻會影響到對于兩者根本性質(zhì)的判斷。比如前述我國《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58條適用中的困惑便是一明證。鑒于上述三個(gè)方面,確實(shí)有必要厘清不可反駁的推定和法律擬制之間的關(guān)系。
如前所述,不可反駁的推定和法律擬制的相同點(diǎn)是形式上的,即事實(shí)B不能被反駁。這一點(diǎn)也是導(dǎo)致人們難以區(qū)分兩者的根本原因。然而,深入分析兩者的概念界定,不難發(fā)現(xiàn)還是存在本質(zhì)區(qū)別的:在不可反駁的推定中,B是未知、真?zhèn)尾幻鳌⑿枰⒎ㄕ邚腁中推出的;而在法律擬制中,立法者明知B和A的性質(zhì)不同,為實(shí)現(xiàn)特定目的或保護(hù)特定利益而將A的法律效果賦予B。比如我國《合同法》第171條規(guī)定“試用買賣的買受人在試用期內(nèi)可以購買標(biāo)的物,也可以拒絕購買。試用期間屆滿,買受人對是否購買標(biāo)的物未作表示的,視為購買”。在該條中,A是試用期間屆滿買受人未作出是否購買標(biāo)的物的意思表示,B是買受人同意購買還是不同意購買,這一點(diǎn)對于立法者而言是未知的,是真?zhèn)尾幻鞯模切枰⒎ㄕ邚腁中進(jìn)行推斷認(rèn)定的。于此,立法者考量到試用買賣合同中雙方當(dāng)事人的利益衡平,便做出了買受人同意購買的推定。再比如,我國《民法通則》第15條規(guī)定:“公民以他的戶籍所在地的居住地為住所,經(jīng)常居住地與住所不一致的,經(jīng)常居住地視為住所。”在該條中,A是公民的住所是其戶籍所在地的居住地,B是公民有經(jīng)常居住地,此時(shí)B的性質(zhì)是確定的、不需要認(rèn)定的,立法者也非常清楚作為A的戶籍所在地的居住地和作為B的經(jīng)常居住地的性質(zhì)截然不同,但立法者為了追求法律上的便利(如方便訴訟管轄或財(cái)產(chǎn)保全等情形)硬是將經(jīng)常居住地規(guī)定為住所。
兩事實(shí)之間是否存在概率聯(lián)系是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的本質(zhì)區(qū)別嗎?在回答該問題之前,筆者有必要進(jìn)行一個(gè)說明。關(guān)于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的區(qū)別,筆者之前曾主張兩者的唯一區(qū)別在于兩事實(shí)之間是否存在或然性常態(tài)聯(lián)系即高概率,存在者為法律推定,不存在者為法律擬制。[4]該命題的得出是建基于所有法律推定均建基于概率基礎(chǔ)之上。然而,筆者后來對法律推定創(chuàng)設(shè)基礎(chǔ)的觀點(diǎn)有所修正,認(rèn)為其基礎(chǔ)不僅包括概率還存在例外情形下的與概率無涉的因素,具體內(nèi)容筆者已在本文第一部分予以詳述。所有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均是建立在高概率聯(lián)系基礎(chǔ)之上的,故其與法律擬制的本質(zhì)區(qū)別在于兩事實(shí)之間是否存在概率關(guān)系。但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有的建立于概率基礎(chǔ)之上,有的則是純粹為了追求程序便利或者解決程序窘境,故不能說其與法律擬制的本質(zhì)區(qū)別也在于兩事實(shí)之間是否存在概率聯(lián)系。當(dāng)然,立法者對于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的創(chuàng)設(shè)也不是隨意而為,不能是一個(gè)“純粹主觀的,或者完全不合理的、非自然的和奇怪的”推斷過程,①People v.Cannon,139 N.Y.32,34 N.E.759(1893).其應(yīng)當(dāng)在作為推定的基礎(chǔ)事實(shí)和最終要建立起來的推定事實(shí)之間形成一種“理性聯(lián)系”(“rational connection”),立法者不得濫用權(quán)力。②Paul Brosman.The Statutory Presumption.5 Tul.L.Rev.178,1930 -1931.和 The Conclusive Presumption Doctrine:Equal Process or Due Protection?72 Mich.L.Rev.800,1973-1974.
四、不可反駁的推定的類型化考察
以我國現(xiàn)行民事法律規(guī)范作為分析對象,不可反駁的推定主要存在以下兩種類型:
(一)關(guān)于主體內(nèi)心意思的法律推定
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為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意思表示真實(shí)是決定某一民事法律行為能夠引起民事法律關(guān)系發(fā)生、變更和終止的重要因素。意思表示真實(shí)是指民事主體的內(nèi)心意思和表示意思相一致,就此,民事主體內(nèi)心意思的確定便成為民法上的一個(gè)重要內(nèi)容。關(guān)于內(nèi)心意思的法律推定,是指根據(jù)某一個(gè)(組)已知基礎(chǔ)事實(shí)推出民事主體同意或者否定的內(nèi)心意思。比如,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08條第2款規(guī)定:“保證范圍不明確的,推定保證人對全部主債務(wù)承擔(dān)保證責(zé)任。”該條便是在保證范圍不明確時(shí),推定保證人同意對全部主債務(wù)承擔(dān)保證責(zé)任的一種對于保證人內(nèi)心意思的推定。我國《繼承法》第25條規(guī)定:“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放棄繼承的,應(yīng)當(dāng)在遺產(chǎn)處理前,作出放棄繼承的表示。沒有表示的,視為接受繼承。受遺贈人應(yīng)當(dāng)在知道受遺贈后兩個(gè)月內(nèi),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③該條雖然使用“視為”語詞,但表達(dá)出來的是法律推定而非法律擬制。該條是當(dāng)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在繼承開始后法定期間內(nèi)未作表示時(shí)對其同意或者拒絕的內(nèi)心意思進(jìn)行推定的規(guī)定。此外,日本《民法典》第619條第1款規(guī)定:“租賃期間屆滿后,承租人對租賃物繼續(xù)使用或者收益,而出租人明知這一情況卻未提出異議時(shí),推定其為以相同租賃條件繼續(xù)租賃。”該條是當(dāng)出現(xiàn)法條規(guī)定情形時(shí)對于出租人同意以相同租賃條件繼續(xù)租賃租賃物這一內(nèi)心意思推定的規(guī)定。
通過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來確定主體的內(nèi)心意思這是法律推定適用的一個(gè)非常重要的場域范圍,因?yàn)橹黧w內(nèi)心意思具有高度抽象性,訴訟中當(dāng)事人往往難以證明,但該內(nèi)心意思的確定對于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變動(dòng)又具有重要意義。關(guān)于主體內(nèi)心意思的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的創(chuàng)設(shè)基礎(chǔ)一般有兩個(gè):一個(gè)是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另一個(gè)是解決因抽象主觀心態(tài)難以證明而造成的程序困境以便利訴訟程序的順暢進(jìn)行。
(二)關(guān)于標(biāo)的物客觀屬性的法律推定
標(biāo)的物是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一個(gè)重要客體對象,其客觀性質(zhì)或者狀態(tài)有時(shí)是決定民事主體是否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某種民事責(zé)任(如違約責(zé)任或侵權(quán)責(zé)任)的重要因素。比如我國《合同法》第158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約定檢驗(yàn)期間的,買受人應(yīng)當(dāng)在檢驗(yàn)期間內(nèi)將標(biāo)的物的數(shù)量或者質(zhì)量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出賣人。買受人怠于通知的,視為標(biāo)的物的數(shù)量或者質(zhì)量符合約定。”“當(dāng)事人沒有約定檢驗(yàn)期間的,買受人應(yīng)當(dāng)在發(fā)現(xiàn)或者應(yīng)當(dāng)發(fā)現(xiàn)標(biāo)的物的數(shù)量或者質(zhì)量不符合約定的合理期間內(nèi)通知出賣人。買受人在合理期間內(nèi)未通知或者自標(biāo)的物收到之日起兩年內(nèi)未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biāo)的物的數(shù)量或者質(zhì)量符合約定,但對標(biāo)的物有質(zhì)量保證期的,適用質(zhì)量保證期,不適用該兩年的規(guī)定。”上述兩種情形下如果買受人未在約定期間或者合理期間內(nèi)就標(biāo)的物的數(shù)量或者質(zhì)量通知出賣人,則推定該標(biāo)的物的性質(zhì)是數(shù)量或者質(zhì)量符合約定,且該推定是不可反駁的,以達(dá)方便程序進(jìn)行和平衡雙當(dāng)事人利益之目的。
此外,不可反駁的推定還適用于前述我國《繼承法意見》第2條關(guān)于同一事故中死亡人員死亡順序的確定上,以保障那些以自然人死亡順序之確定作為前提條件的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順利進(jìn)行。
五、不可反駁的推定的語言表達(dá)形式
關(guān)于不可反駁的推定的語言表達(dá)形式,應(yīng)當(dāng)分兩個(gè)層次進(jìn)行分析,首先應(yīng)當(dāng)將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從語言表達(dá)上進(jìn)行區(qū)分,然后再將不可反駁的推定和可以反駁的推定區(qū)分開來。
(一)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通過“推定”語詞而避免使用“視為”語詞表達(dá)推定制度
望文生義,通過“推定”語詞表達(dá)出來的應(yīng)當(dāng)是推定制度,而法律擬制的習(xí)慣表達(dá)方式是“視為”。[6]然而,我國在設(shè)定法律推定制度時(shí),對于標(biāo)識性語詞的使用非常混亂,有時(shí)使用“推定”,如我國《合同法》第78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對合同變更的內(nèi)容約定不明確的,推定為未變更”;有時(shí)使用“視為”,如我國《合同法》第47條第2款規(guī)定:“相對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個(gè)月內(nèi)予以追認(rèn)。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視為拒絕追認(rèn)”;有時(shí)甚至不使用任何標(biāo)識性語詞,如我國《民法通則》第23-25條規(guī)定的自然人宣告死亡制度中的死亡推定,這是一種典型法律推定卻未使用“推定”術(shù)語。此外,在民事法律之外的規(guī)范性文件中,推定還有使用“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和“以……論”語詞表述的情形。[7]如前所述,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最容易產(chǎn)生混淆的情形發(fā)生在關(guān)于民事主體主觀意思的規(guī)定上,22處用“視為”語詞表達(dá)出來的主觀事項(xiàng)竟有19處之多是法律推定制度,且其中的推定事實(shí)均不可被反駁。因此,可以說,在民事領(lǐng)域中,用“視為”語詞表達(dá)出來的主觀事項(xiàng)都是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制度。鑒于此,為了有效區(qū)分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制度,避免兩者適用中的混淆和錯(cuò)誤,法律推定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通過“推定”語詞予以表達(dá),而法律擬制應(yīng)當(dāng)盡可能通過“視為”語詞進(jìn)行表達(dá),爭取做到凡是“推定”語詞表達(dá)出來的都是法律推定制度,凡是“視為”語詞表達(dá)出來的都是法律擬制制度。
(二)應(yīng)當(dāng)通過不同的語言范式來表達(dá)可以反駁的推定和不可反駁的推定
國內(nèi)不少學(xué)者和司法實(shí)務(wù)人員長期以來認(rèn)為凡是推定都可以被反駁,于是我國才出現(xiàn)了對于《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58條規(guī)定的推定醫(yī)療機(jī)構(gòu)過錯(cuò)的不同解讀。因此,筆者認(rèn)為需要再次闡明的是,概率并非創(chuàng)設(shè)法律推定的唯一基礎(chǔ),法律推定創(chuàng)設(shè)的基礎(chǔ)是多元的,于是表現(xiàn)在推定的類別上便是推定存在可以反駁和不可反駁的二元區(qū)分。明確這一點(diǎn)后,在立法上,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通過不同的語言范式表達(dá)可以反駁的推定和不可以反駁的推定,以盡可能避免法律適用過程中可能產(chǎn)生的不必要分歧。具體做法是:可以反駁的推定應(yīng)當(dāng)通過“除非受推定不利影響的一方當(dāng)事人能夠證明推定事實(shí)不存在”的語言范式予以表達(dá),比如我國《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88條規(guī)定的是可以反駁的過錯(cuò)推定,目前條文表述:“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損害,堆放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cuò)的,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筆者認(rèn)為如果將其修改為:“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損害,推定堆放人存在過錯(cuò),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除非堆放人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cuò)”會更好一些。不可反駁的推定則應(yīng)當(dāng)通過“推定推定事實(shí)的存在”的語言范式予以表達(dá),比如我國《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58條規(guī)定的“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醫(yī)療機(jī)構(gòu)有過錯(cuò):……”便是一適例。可見,可以反駁的法律推定和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之間在語言表達(dá)上的本質(zhì)區(qū)別應(yīng)當(dāng)是是否存在“除非受推定不利影響的一方當(dāng)事人能夠證明推定事實(shí)不存在”這一語言范式。
六、結(jié)論
我國學(xué)界和實(shí)務(wù)界一直對是否所有推定都可以被反駁這一問題觀點(diǎn)不一,實(shí)質(zhì)問題在于是否承認(rèn)存在不可反駁的推定。鑒于此,本文首先肯定存在不可反駁的推定,理由是推定被創(chuàng)設(shè)的基礎(chǔ)具有多元化,并非所有推定均建立在基礎(chǔ)事實(shí)和推定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基礎(chǔ)之上,有些推定的創(chuàng)設(shè)與概率無關(guān),僅僅是立法者追求程序便利或者解決訴訟困境的一種方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事實(shí)推定都是建立在兩事實(shí)之間的或然性常態(tài)聯(lián)系基礎(chǔ)之上、都是可以被反駁的,否則將會導(dǎo)致裁判者自由裁量權(quán)的濫用。因此,筆者主張存在不可反駁的推定,其適用的場域范圍僅僅是法律推定。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呈現(xiàn)在外的表現(xiàn)狀態(tài)是被推定事實(shí)的不可反駁性,這必然又使人們在認(rèn)知上容易與法律擬制相混淆,甚至理論界還出現(xiàn)了類似“擬制性推定”或者“推定性擬制”等將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交織在一起的術(shù)語。筆者認(rèn)為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雖然在外顯層面具有相似性,但兩者在性質(zhì)層面存在本質(zhì)區(qū)別:前者中的推定事實(shí)是未知、真?zhèn)尾幻鳌⑿枰门姓咄ㄟ^基礎(chǔ)事實(shí)予以認(rèn)知的;后者中的擬制事實(shí)立法者明知其在性質(zhì)上與基礎(chǔ)事實(shí)是不同的。兩事實(shí)之間是否存在或然性常態(tài)聯(lián)系不是兩者的本質(zhì)區(qū)別,因?yàn)橛行┎豢煞瘩g的推定的創(chuàng)設(shè)基礎(chǔ)并非兩事實(shí)之間的高概率聯(lián)系。不可反駁的推定在民事領(lǐng)域中主要適用于對于主體內(nèi)心意思的推定和對于標(biāo)的物客觀屬性的推定。不可反駁的推定應(yīng)當(dāng)有科學(xué)的語言表達(dá)方式,這需要從兩個(gè)層面進(jìn)行規(guī)范:首先從語言上區(qū)分法律推定和法律擬制制度,應(yīng)當(dāng)通過“推定”語詞而避免使用“視為”語詞表達(dá)推定制度;然后應(yīng)當(dāng)通過不同的語言范式來表達(dá)可以反駁的推定和不可反駁的推定,可以反駁的法律推定應(yīng)當(dāng)通過“除非受推定不利影響的一方當(dāng)事人能夠證明推定事實(shí)不存在”這一語言來表達(dá),而不可反駁的推定則不需要。
[1]王利明,等.中國侵權(quán)責(zé)任法教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2]梁慧星.《侵權(quán)責(zé)任法》中的醫(yī)療損害責(zé)任[J].法商研究,2010,(6).
[3]江偉.證據(jù)法學(xué)[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張海燕.“推定”和“視為”之語詞解讀:以我國現(xiàn)行民事法律規(guī)范為樣本[J].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12,(3).
[5]勞東燕.推定研究中的認(rèn)識誤區(qū)[J].法律科學(xué),2007,(5).
[6]劉風(fēng)景.視為的法理與創(chuàng)制[J].中外法學(xué),2010,(2).
[7]何家弘.從自然推定到人造推定[J].法學(xué)研究,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