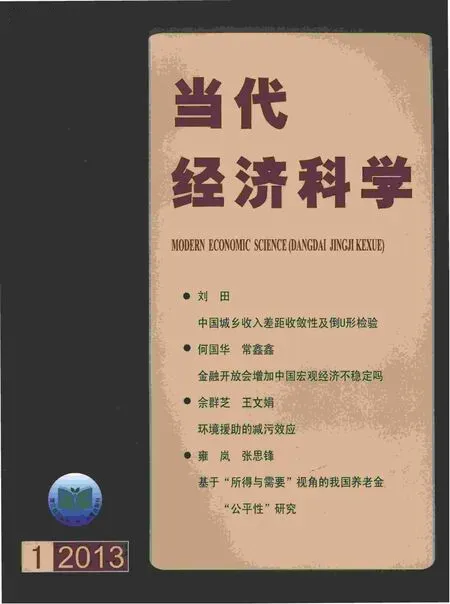營銷學的學科淵源與發展:基于思想史視角的探討
夏春玉,丁 濤
(東北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遼寧大連116025)
一般認為,營銷管理是管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但對于營銷管理為什么可以作為管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界并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本文認為,營銷管理更多的采用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奉行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具有新古典經濟學的屬性,甚至可以稱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營銷管理也不是營銷學的全部,后者還包括宏觀營銷等非主流的營銷學。宏觀營銷代表了不同于營銷管理的營銷范式。這兩種不同的營銷學范式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二者為什么沒有被整合到一起?我們認為經濟學在營銷學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不同的經濟學范式決定了不同的營銷學范式;經濟學的主流范式也決定了營銷學的主流范式。從營銷學的發展歷程看,不同的營銷學范式之間相互對立,此起彼伏,從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往往有不同的主流范式。基于此,本文沿著營銷思想的發展歷程,從經濟學的視角解讀營銷學在不同階段的發展狀況。
一、前營銷時期:營銷思想的萌芽
對于營銷思想的產生,西方有學者認為可以追溯到柏拉圖那里[1]。更有趣的是,一般認為,“以顧客為中心”的營銷哲學對于20世紀營銷學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然而,在一些學者看來,這算不上是什么新思想,早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就將其表達出來了[2]。其實,西方學者在探求營銷思想的淵源時,往往訴諸于經濟學,如Dixon從18世紀的古典經濟學著作中發現了大量的營銷思想[3]。可以認為,經濟學原本就是營銷思想的一個重要源泉。但這些思想只是些零星的片段,并沒有對營銷問題給予專門的關注,那個時候還不存在“營銷”這個概念①嚴格說,“marketing”(營銷)這個概念在16世紀就出現了[3],但只是在極少的情況下使用。。
西方學者對營銷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商品流通(distribution)開始的,如貿易、流通、批發和零售。19世紀后期,出現了一些專門研究商品流通的著作[4]。其中,Edward Atkinson于1885年發表的《產品流通》(Distribution of Products)可能是最早的營銷學著作,此書提出了營銷的各種功能,可能對20世紀初最著名的營銷學者Arch Shaw產生了影響。盡管這些著作對早期營銷學的產生具有重要影響,但營銷問題還未成為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研究領域,“營銷”這一術語還沒有正式出現,也沒有專門的營銷學課程,因此,這一時期仍然屬于前營銷時期(Pre-Marketing)[5],也可認為是營銷理論正式產生之前的過渡期。
Bartels不贊同將營銷思想追溯到太久遠的年代,認為真正的營銷學是從1900年以后才出現的[6]。他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此做出了解釋,即新思想需要新的概念來表達,只有當“營銷”這個概念被應用時,才表明新思想的形成。就此而論,由于“營銷”這個術語的正式應用是在1900年之后開始的,因而營銷學也產生在1900年之后。
二、作為經濟學分支的營銷學:形成和發展
(一)1900-1920營銷理論的形成階段
學界普遍認為,營銷學是作為一門應用經濟學產生的[2],早期的營銷學者都是經濟學家。20世紀初,美國的營銷思想集中產生于兩所經濟學思想最活躍的大學里,即威斯康辛大學和哈佛大學[7]。威斯康辛大學云集了當時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如R.T.Ely、H.C.Adams、J.B.Commons等。這些經濟學家多是德國歸來的留學生,深受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也是美國制度學派的奠基人或重要成員。伊里(Ely)曾是美國經濟學會(AEA)的發起人,他強烈反對正統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并成為威斯康辛大學新經濟學派的領袖,奉行一種被稱為“威斯康辛思想”的學術理念[8]。他培養出的一些經濟學家成為美國早期最重要的營銷學者,使威斯康辛大學成為美國營銷思想形成與發展的領導者[7]。這些學者包括 E.D.Jones、Samuel Sparling、James Hagerty、H.C.Taylor、Hibbard、Nystroms等。伊里總是鼓勵學生到德國學習一段時間,因此,威斯康辛大學的這些營銷學者都有在德國學習的經歷[8],他們的研究方法也具有德國歷史學派的風格。施穆勒領導的德國歷史學派反對正統經濟學的抽象和演繹方法,注重對事件全面而詳盡的分析,強調縱向歷史分析和橫向結構比較。在正統經濟學中,沒有關注介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中間組織機構,從而沒有將商品流通過程視為研究對象[9]。而美國制度經濟學繼承了德國歷史學派的研究傳統,強調在對經濟現象進行詳細描述的基礎上進行因果解釋,因此,介于生產和消費的商品流通過程和組織成為美國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Sparling在《經濟組織入門》(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Organization)一書中應用歷史研究方法解釋了市場、批發、零售等商業組織的演化過程。Nystroms在《零售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Retailing)中對各種零售組織形式或業態進行了歷史分析。威斯康辛大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農產品流通領域,對農產品流通過程中的各種組織機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在這些研究中,機構或制度分析(也包括功能分析)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方式[8-9]。威斯康辛大學的這些早期的營銷研究深深扎根于制度經濟學[9],甚至可以認為是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由于制度經濟學在20世紀初非常活躍,對哈佛大學也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但其對營銷問題的研究卻表現出一種與威斯康辛大學不同的發展思路。
哈佛大學也受到了德國歷史學派的影響,如E.F.Gay和F.W.Taussig兩位哈佛資深學者都是德國歸來的留學生。但他們的研究風格與威斯康辛大學大不一樣,尤其是案例教學研究的發展使他們更多的從微觀的企業組織層面看問題。哈佛大學的著名營銷學者M.T.Copeland在設計營銷學課程時就將營銷學定義為商品分銷過程中商業管理原理的研究,即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看待營銷問題,包括市場定位、渠道選擇、品牌、廣告、價格等一系列營銷策略[10]。這實際上也是后來營銷管理的雛形。在對這些營銷策略的分析過程中,Copeland重點對商品進行了各種分類,為后來的商品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微觀經濟學對營銷策略的分析發揮了重要作用,如Arch Shaw在對價格策略的分析中充分運用了馬歇爾提出的“消費者剩余”原理[11]。Shaw的一個突出貢獻是對商業活動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分類,為后來的功能分析奠定了理論基礎。微觀經濟學對營銷管理的影響已經在哈佛大學的營銷學中表現出來,但20世紀初,在美國最活躍的是制度經濟學,因而威斯康辛大學在營銷學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認為營銷學的發展表現出兩種路徑,一種是宏觀視角的商品流通過程研究,另一種是微觀視角的營銷管理研究。前者在美國制度學派的推動下得到了更快的發展,成為當時營銷研究的主流;后者在微觀經濟學的影響下也得到了發展。該時期也形成了三種基本的研究方式(approach),即商品分析、機構分析和功能分析。實際上,這三種研究方式很難隔離開來,正如血液、心臟和造血功能三者密不可分一樣。但早期的研究并沒有將這三者很好的整合在一起,多數研究被視為描述性或簡單的統計研究,沒有在理論上實現重要的突破。以后的營銷學者開始對這些營銷理論進行整合,但制度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根本對立又決定了營銷學向著兩個相互分離的方向發展。
(二)1920-1950營銷理論的整合與分離
上個世紀20年代以后,有很多學者開始嘗試對早期的營銷理論進行系統整合,一個重要的表現是“營銷原理”方面的著作大量出現[6]。在理論的整合過程中,商品分析和機構分析更多地發揮了描述性的作用,而理論的提升多是通過功能分析來實現的,因而功能分析成為多數研究者構建營銷理論的主要路徑[5]。盡管如此,西方學者并沒有把營銷理論真正整合在一起,早期形成的宏觀視角的商品流通與微觀視角的營銷管理依然分道揚鑣。Savitt對這一時期(1920-1950)的一些重要論著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營銷學的這兩條發展路線的分離,一條路線偏重宏觀視角的營銷研究,主要代表有Clark、Breyer、Duddy & Revzan、Barger等;另一條路線偏重營銷管理,主要代表有 Converse、Maynard等[12]。顯然,宏觀視角的營銷主要關注的是社會問題,如價格歧視、流通成本、廣告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等,在Breyer的著作中,相關問題占到幾乎一半的篇幅,而在Converse的著作中僅占十分之一[5]。總體上,該時期宏觀視角的營銷占據著營銷學的主流[13]。但到了50年代后期,以阿爾德森為分水嶺,營銷管理逐漸成為營銷學的主流。
(三)兩種經濟學范式在阿爾德森營銷理論體系中的整合與分離
在阿爾德森看來,早期營銷學者在構建營銷學的一般理論框架方面收效甚微,他認為:“營銷學文獻并沒有為讀者提供有分量的原理或理論”[14]。阿爾德森由于在這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被西方學者譽為營銷學教父。他對營銷學理論框架的構建是從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開始的,認為傳統經濟學的價格分析建立在同質市場和同質產品的基礎上,脫離了現實。但這并沒有使阿爾德森脫離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因為他對異質性市場和產品的分析也恰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基礎之上,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市場細分理論[15]。在其他營銷管理策略的分析中,阿爾德森也廣泛應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如他認為邊際分析是營銷研究的一種有力分析工具,并具體闡述了這種分析方法在產品定價、促銷手段的選擇等營銷策略中的應用[16]。實際上,阿爾德森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初步建立了一套營銷管理理論。
阿爾德森注意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均衡分析建立在不現實假定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交易費用的重要性。新古典經濟學正是缺乏對交易費用的關注而忽略了對營銷問題的研究。阿爾德森對各種交易費用都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強調信息費用,因而信息問題成為他關注的核心問題[17-18]。在很大程度上,阿爾德森應該被視為交易費用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先驅者,但他的這一貢獻很少被經濟學家注意到。其實,阿爾德森對交易費用的認識已經超越了新制度經濟學,從而走上了一條與后來新制度經濟學完全不同的道路。以科斯、威廉姆森為代表的交易費用經濟學或新制度經濟學盡管也推崇康芒斯的偉大洞見,即將“交易”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但實際上“引而不用”。新制度經濟學沒有脫離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19],因而在他們的論著中實際上看不到康芒斯的影響。而阿爾德森沿著康芒斯的思路脫離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并走向了功能主義和系統論。他在上個世紀50年代發表的著名論文《營銷學的分析框架》中,通篇多處提到康芒斯,表明康芒斯對他的理論框架產生了重要影響。他還津津樂道:“在所有經濟學家中,康芒斯最出色的表述了我所謂的‘功能主義分析’”[16]。康芒斯創立的交易公式深刻體現了人類社會系統中各種組織體的功能關系,這被阿爾德森很好地吸收了,如一般性交易(routine transaction)和關鍵性交易(strategic transaction)這兩個概念在他的分析框架中占據很重要的位置[16]。康芒斯明確區分了機械結構、有機體和運行中的機構[20],其中,后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運行中的機構(going concern)包含著人類的目的性,而生物有機體顯然沒有這樣的特點。阿爾德森領悟到了這一洞見,多次提到“運行中的機構”,并由此引申出他在功能主義分析中的兩個最關鍵的概念,即“組織行為系統”和“團體行為”[16],并將團體(group)的“目標”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人的目的性是不能作為研究對象的,因為它把人簡化為原子式的個體。原子式個體正如物理學中的質點一樣對外界做出機械的反應,也就是所謂的理性選擇。也正是基于這種物理學的類比,經濟學才被人為設計為硬科學,遠離了人與社會。可見,制度經濟學對阿爾德森的功能主義分析產生了重要影響。
當然,阿爾德森的初衷是通過功能主義分析為營銷理論建立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這可以從他的名著《市場營銷行為與經理行動》的副標題“營銷理論的功能主義構建路徑(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Marketing Theory)”看出。然而,我們看到阿爾德森一方面應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同時又應用了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二者屬于兩種不相容的研究范式,因此他在整合營銷理論的過程遇到了無法調和的困頓。也就是說,建立在制度經濟學基礎上的功能主義分析難以用來整合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營銷管理理論。后來的營銷學者,大都強調了阿爾德森對營銷管理做出的貢獻,但拋棄了他的功能主義。原因之一是阿爾德森的功能主義晦澀難懂[21],因為當時的營銷學者很少接觸制度經濟學;原因之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以后,新古典經濟學已經取代制度經濟學成為經濟學的主流,制度經濟學逐漸被邊緣化,甚至被斥為異端學說。所以,西方學者在討論經濟學對阿爾德森的影響時,都是關注新古典經濟學家[22]、奧地利學派[18]等,而完全忽略了制度經濟學對他的影響,尤其是制度經學的集大成者康芒斯。阿爾德森傾其一生致力于功能主義和系統論的研究,因而拋棄了功能主義也就等于拋棄了阿爾德森的精華,從這個意義上講,阿爾德森實際上被當代營銷學界所遺忘[23]。
阿爾德森在營銷學中的命運與馬歇爾在經濟學中的命運有很多相似之處。一般認為馬歇爾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而實際上,邊際分析只是馬歇爾整個理論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經濟學家,馬歇爾是按照亞當·斯密、李嘉圖和約翰·穆勒的傳統受到訓練的,因此,他繼承了正統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如分工理論。他還是一個“一流的經濟史學家……將活生生的事實歸納成原理,再將原理運用到純粹的歷史研究中”[24]。馬歇爾不但不反對歷史學派,還多次公開稱贊德國歷史學派的許多觀點和領袖,并被很多學者奉為歷史學派或制度學派的成員,如霍奇遜就認為:“馬歇爾是歷史學派傳統的產物和一部分”[25]。宏大的知識結構足見馬歇爾的淵博,使他的后繼者們遙不可及。由于推崇自然科學的邏輯實證主義,數學形式化主導了經濟學的發展潮流,因而被馬歇爾形式化的邊際分析和價格均衡理論得到繼承和發展,并成就了新古典經濟學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開展了一場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革命,在這次革命浪潮中,馬歇爾的其他重要經濟思想因不能被形式化而逐漸被拋棄了,如分工理論或經濟組織問題,尤其是對商品流通過程的研究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消失了。從根本上講,馬歇爾的理論體系中包含著兩種根本對立的研究范式,即奉行邏輯實證主義的新古典經濟學和重視歷史主義研究傳統的非主流經濟學(包括制度經濟學)[19],這兩種根本對立的研究范式導致了馬歇爾經濟學體系的最終決裂。在這兩種研究范式的對峙中,邏輯實證主義占了上風,而歷史主義研究傳統逐漸被弱化。這在阿爾德森的理論體系中也體現得非常明顯。阿爾德森一方面致力于通過功能主義和系統論建立一個統一的營銷學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又運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理論建立了一套營銷管理理論。然而,兩種經濟學范式的對立決定了兩種營銷學范式的最終分裂。如前所述,功能主義和系統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制度經濟學基礎之上,而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代表了兩種對立的研究范式。他們之間的對立可以追溯到德國歷史學派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方法論之爭,盡管有很多學者試圖將兩種研究范式整合到一起,但經濟學的發展一再證明二者一直是分離的。按照庫恩對范式的理解,經濟學的這兩種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incommensurable),因而也就不難理解,馬歇爾和阿爾德森的理論體系最終都被分裂為兩個不同的發展方向。阿爾德森的營銷學分裂為宏觀營銷和營銷管理兩個流派,后者發展為營銷學的主流,因為它奉行著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
三、現代營銷(1960-)的經濟學基礎
(一)營銷管理的微觀經濟學基礎
通過上述對1900-1950年代營銷理論的討論,本文認為營銷學被分裂在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之中。營銷管理范式確立以后,營銷管理與微觀經濟學表現出逐漸分離的趨勢[26],發展為兩個看似不相干的學科。這種表面的分離現象使很多學者忽視了營銷管理與微觀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從大學的課程設置來看,一般將營銷管理設置為管理學的一個分支,從而缺少對營銷管理與微觀經濟學之間關系的關注。盡管國內學界將營銷管理劃歸為管理學的一個分支,但“營銷管理”這個概念并不是來自管理學。的確,泰勒的科學管理也對營銷管理產生了重要影響[27],但這種影響主要局限于“銷售管理”。實際上,管理學本身主要專注于生產率的提高,而不是營銷,如科學管理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生產率。另外,管理學自身也是一個“理論匱乏”的學科,其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微觀經濟學[28]。因此,管理學者也被稱為工程經濟學家[29],專注于提高生產效率,而非市場營銷。康芒斯將企業定義為一種“運行中的機構”,包括兩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即運行中的工廠和運行中的營業,二者屬于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前者是注重“效率”的工程經濟學,后者是負責“營銷”的所有權經濟學[20]。但在西方學界,恐怕只有阿爾德森注意并領悟到了康芒斯的這一重大貢獻[16]。因此,將營銷學或營銷管理視為管理學的分支可能是對理論的一種誤讀。
另外,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確立的營銷管理范式也不是一個新的范式,在早期的營銷學發展過程中就已經產生了,如在Shaw、Copland和Alderson的著述中就已經看到營銷管理范式的存在。早期學者對營銷管理的研究都采用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方法,可以說,營銷管理在產生之日就嫁接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西方學者也已經發現,STP營銷戰略、4Ps以及國際市場營銷的各個方面都采用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30],如4Ps理論是由上世紀30年代羅賓遜和張伯倫提出的壟斷競爭或不完全競爭理論直接延伸而來的[15,31]。營銷管理應用微觀經濟學方法也必須建立在利潤最大化、價格均衡等微觀經濟學的前提假定基礎之上。例如,在價格策略的分析中,西方營銷學者多應用馬歇爾提出“消費者剩余”原理,這個原理是由邊際分析得來的,而邊際分析又是建立在利潤最大化和價格均衡這兩個前提假定基礎上。營銷管理研究在方法論上也遵循微觀經濟學的邏輯實證主義[32]。由于奉行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營銷管理同微觀經濟學一樣,不斷向形式化的方向發展,強調數學意義的嚴格化和精確化,并由此形成一套模型構建、假設檢驗、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的研究模式[32]。對數理模型和定量分析技術的應用正是西方學界所推崇的學術標準,營銷管理范式因符合這種學術標準而得以迅速發展成為營銷學中的主流范式。當然,邏輯實證主義也給營銷管理帶來了短視性、脫離現實等嚴重缺陷[33-34]。
(二)宏觀營銷與營銷歷史研究的制度經濟學基礎
微觀視角的營銷管理范式發展為營銷學的主流后,宏觀視角的營銷研究并沒有被忽視,而是發展為各個非主流營銷流派,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宏觀營銷學派。營銷管理范式只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看問題,以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從而忽視了“營銷與社會”相關的宏觀視角的營銷問題[5]。宏觀營銷學派形成于上個世紀70年代后期,從1976年第一屆宏觀營銷年會到1981年《宏觀營銷學報》(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的創立標志著宏觀營銷正式成為營銷學中一個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的組成部分[35]。目前,宏觀營銷依然處于前科學階段,其研究對象和理論范式都處于一種分散化狀態[13]。西方的一些宏觀營銷學者正在努力嘗試通過系統分析建立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36-38]。這種研究方式顯然受阿爾德森的功能主義和系統論的影響,實際上是在復歸阿爾德森的宏觀營銷研究路線。如前所述,阿爾德森的功能主義和系統論建立在制度經濟學基礎之上,因此,通過系統分析為宏觀營銷建立統一的分析框架,似乎需要對美國早期的制度經濟學有很深刻的理解,這可能是目前宏觀營銷學者所普遍忽視的方面。營銷歷史學派是西方新興的一個營銷學流派,這個流派看似年輕,2009年才創立自己的專業期刊《營銷歷史研究學報》(Journa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Marketing),實際上卻有著比任何營銷流派都古老的研究傳統[39],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奉行德國歷史學派的世界觀和方法論。20世紀初產生的宏觀視角的營銷理論可以認為是制度經濟學的分支,而后者又被視為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衍生物。因此,營銷歷史學派自然而然與美國制度學派走到了一起,同時也成為宏觀營銷的戰略聯盟[40]。1994-2005年,在《宏觀營銷學報》上發表的所有137篇論文中,有61篇屬于營銷歷史研究領域,占45%[41]。這就進一步說明了美國制度經濟學對宏觀營銷研究的重要意義。
四、小 結
本文認為每個營銷流派都與經濟學有密切的聯系,正如巴特爾斯所言:“較之其他諸多社會學科,經濟理論為營銷思想提供了更多的觀念……不論對于個體組織的營銷管理還是更宏觀經濟視角的營銷,經濟學的觀念都是對分析和解釋營銷現象所不可或缺的”[6]。早期的很多營銷理論扎根于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制度經濟學;營銷管理范式的理論內核來自微觀經濟學,如利潤最大化、一般均衡理論等,其方法論同微觀經濟學一致,遵循邏輯實證主義;宏觀營銷學派的系統分析可以認為是對阿爾德森功能主義和系統論的繼承和發展,而阿爾德森功能主義和系統論顯然受到美國制度經濟學的深刻影響;營銷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顯然溯源于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制度經濟學。正如Seelye所言:“如果我們想要展示一門真正具有理論價值的營銷學課程,教會營銷專業的學生去思考,那么我們就必須把經濟學理論寫進營銷學教科書中”[42]。因此,營銷學盡管也吸納了其他諸多學科的理論,但其主干仍是經濟學的延續,國內也有學者指出:“我國在學科分類中將市場營銷學納入管理學的門類,實際上是理論分類中的一種謬誤”[43]。
經濟學其實就像一只無形的手左右著營銷學的發展。20世紀初至20、30年代,溯源于德國歷史學派的美國制度學派在美國占據了經濟學的主流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使扎根于制度經濟學的宏觀營銷研究發展成為營銷學的主流。20世紀40年代以后,制度學派的影響力日漸式微,而新古典經濟學的影響力蒸蒸日上。因此,建立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基礎上的營銷管理研究迅速發展起來,直至上個世紀50、60年代成為營銷學的主流,而宏觀營銷研究逐漸被邊緣化。從最近的發展趨勢看,營銷管理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而宏觀營銷的影響力驟增,尤其是新興營銷歷史學派已成為宏觀營銷學派強有力的戰略聯盟。進一步而言,2008年金融海嘯的爆發同樣也給新古典經濟學造成重創,非主流的經濟學隨之興起,從而給宏觀營銷的發展帶來了歷史機遇。
[1] Cassels J M.The significance of early economic thought on marketing[J].Journal of Marketing,1936,1:129-133.
[2] Karlinsky M.Changing asymmetry in marketing[A].Firat A F,Dholakia N,Bagozzi R P.Philosophical and radical thought in marketing[C].Lexington:Lexington Books,1987.39-55.
[3] Dixon D F.Marketing as production:The development of a concept[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1990,18:337-343.
[4] Goehle D G.A historical approach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wholesaling thought[A].Nevett T,Hollander S C.Marketing in three Eras: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marketing history conference[C].Landing:MSU,1987.225-241.
[5] Wilkie W L,Moore E S.Scholarly research in marketing:exploring the“4 Eras”of thought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ublic & Marketing,2003,22:116-146.
[6] Bartels R.The history of marketing thought(Second ed.)[M].Columbus,OH:Grid,1976.29-30.
[7] Bartels R.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ing thought,1900-1923[J].Journal of Marketing,1951,16:1-17.
[8] Jones D G B,Monieson D D.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marketing thought[J].Journal of Marketing,1990,54:102-113.
[9] Brown G.What economists should know about marketing[J].Journal of Marketing,1951,16:60-66.
[10] Copeland M T.Scope and content of a course in marketing[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20,28:375-398.
[11] Shaw A W.Some problems in market distribu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51-59.
[12] Savitt R.Pre-Aldersonian antecedents to macromarketing:Insights from the textual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1990,18:293-301.
[13] Wilkie W L,Moore E S.Macromarketing as a pillar of marketing thought[J].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2006,26:224-232.
[14] Alderson W,Cox R.Towards a theory of marketing[J].Journal of Marketing,1948,13:137-152.
[15] Dixon D F,Wilkinson I F.An alternative paradigm from marketing theory[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989,23:59-69.
[16] Alderson W.Marketing behavior and executive action[M].Homewood,IL:Richard D.Irwin,1957.237-240,21,295-306,25.
[17] Alderson W.The heterogeneous market and the organized behavior system[A].Wooliscroft B,Tamilia R D,Shapiro S J.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 to Aldersonian marketing thought[C].New York:Springer,2006.189-215.
[18] Reekie W D,Savitt R.Marketing behaviour and entrepreneurship:A synthesis of Alderson and Austrian Economics[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982,16:55-66.
[19] 賈根良.西方異端經濟學傳統與中國經濟學的激烈轉向[J].社會科學戰線,2005(3):43-51.
[20] (美)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下)[M].于樹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272-283,287-291.
[21] Hostiuck K T,Kurtz D L.Alderson′s function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ing theor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73,2:141-156.
[22] Grether E T.Alderson and Chamberlin[A].Wooliscroft B,Tamilia R D,Shapiro S J.A Twenty-First Century guide to Aldersonian marketing thought[C].New York:Springer,2006.333-336.
[23] Wooliscroft B.Wroe Alderson′s influence on marketing theory through his textbooks[J].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2003,31:481-485.
[24] (美)約瑟夫·熊彼特.從馬克思到凱恩斯[M].韓宏,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78.
[25] (英)杰弗里·M·霍奇遜.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M].高偉,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26.
[26] 李陳華,柳思維.論營銷學與經濟學的離合[J].消費經濟,2001(5):46-49.
[27] La Londe B J,Morrison E J.Marketing management concepts yesterday and today[J].The Journal of Marketing,1967,31:9-13.
[28] 張培剛.微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504.
[29] (美)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M].于樹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142.
[30] (美)愛德華·K·陳,羅杰·M·席勒.市場營銷的經濟學基礎[A].邁克爾·J·貝克.市場營銷百科[C].李恒,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37-48.
[31] Gr?nroos C.Quo vadis marketing?Toward a relationship marketing paradigm[J].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1994,10:347-360.
[32] Arndt J.On making marketing science more scientific:Role of orientations,paradigms,metaphors,and puzzle solving[J].Journal of Marketing,1985,49:11-23.
[33] Hayes R H,Abernathy W J.Managing our way to economic declin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80,58:67-77.
[34] Wind Y,Robertson T S.Marketing strategy:New direc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J].Journal of Marketing,1983,47:12-25.
[35] Hunt S D.On the founding of the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J].Journal of Macromarkeitng,2011,31:199-214.
[36] Dixon D F.Macromarketing:a social systems perspective[J].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1984,4:4-17.
[37] Mittelatadt J D,Kilbourne W E,Mittelstaedt R A.Macromaketing as agorology:Macromarketing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agora[J].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2006,26:131-142.
[38] Layton R A.Marketing systems:A core macromarketing concept[J].Jounal of Macromarketing,2007,27:227-242.
[39] Shaw E H,Jones D G B.A history of school of marketing thought[J].Marketing Theory,2005,5:239-281.
[40] Shapiro S J.Macromarketing:Origins,development,current status and possible future direction[J].European Business Review,2006,18:307-321.
[41] Jones D G B,Shaw E H.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1981-2005[J].Jounal of Macromarketing,2006,26:178-192.
[42] Seelye A L.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theory in marketing courses[J].Journal of Marketing,1947,11:223-227.
[43] 晁鋼令.市場營銷的理論內核——交換障礙的克服[J].市場營銷導刊,2002(6):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