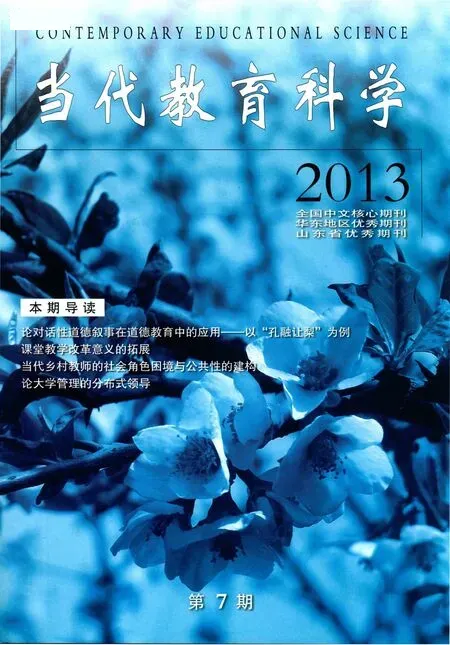大學生自媒體敘事場域生成與高校德育創新*
● 郁云琦
當前自媒體3.0(we media)以其零技術發展成為人們可以自由進行信息生產、制作與傳播的敘事場域,習慣于被動閱讀的“受眾”在恣意表達中獲得了一種顛覆式的互動愉悅,使得傳播意義上的“受眾”成為自媒體時代的“新主播”。雖然這種敘事場域為個體表達與社群交往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使人們長久以來渴望表達與交流的欲望獲得滿足,但同時也給高校德育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與機遇,特別是自媒體催生大學生話語權的彰顯與高校德育敘事的轉向,值得我們認真地研究與對待。
一、大學生自媒體敘事語境的生成
現在新聞傳播3.0產生的新文化形式得到了大學生的認同與推崇,他們能夠熟練掌握與使用視頻手機、博客、微博、維基百科、BBS、QQ、陌陌、啪啪、微信以及分享網站等為代表的新媒介,并形成大學生自媒體(we media)現象。即大學生借助各種可讀、可寫、可互動新科技傳播方式,在分享參與式的新文化傳播運作中,創新與形成新的信息、知識攝取、話語敘事表達、人際交往等范式,從而表達自己的敘事主張,成長為比他們父母一代更為開放、民主和社會自覺的“新新一代”。
(一)大學生攝取知識信息自主化
自媒體為大學生提供了強大的信息平臺,消解了高校集權式管理的約束性,把“宣講”、“灌輸”變成一種以“平權”為特征的話語表達與互動傳播場域,高校傳統的單純靠書面以及教師面授的學校教育已經沒有絕對的優勢與權威。大學生在攝取知識信息時表現出個性化、娛樂化、功利化等特征,自主查找自己想要的信息、知識和資源。當遇到問題時,大學生首要做的不是向老師請教或窩在圖書館苦讀,而是轉向到網上“谷歌”一下,他們利用網絡可以輕而易舉的獲取想要的信息。同時,高校現有專業設置以及課程學習對大學生也沒有太強的吸引力,大學生更加渴望高銳的知識。而自媒體催生大學生的學習模式由教堂式教育模式的集體“聽經”躍進到“集市式教育模式”的自主選取,他們從一元的學習轉向自媒體多元的體驗,由被動既定知識的灌輸提升到現實要求及自身需求的攝取,并發揮自身的參與性、創造性,他們通過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方式來凸顯當代大學生的文化、性格主張,如大學生媒體工作室、新生代網絡寫手、大學生flash創作、DV作品等等,并有意識地利用這一開放平臺進行自身個人觀點的發布,以及個人形象的打造,自主的攫取與創造。
(二)大學生敘事話語表達凸顯化
大學生借助自媒體形態,不斷消彌了自身與社會分眾之間的分融,由象牙塔走向社會公眾,同時他們也學會與掌握如何利用自媒體來聚集、累積與發揮自身的權力與能量,表現出與以往大學生不同的時代特質與需求。自媒體的即時性、跨時空性以及“由我做主”非人格化的理念契合了大學生追求自我中心主義或純粹個性化生活方式的特質,大學生可以在自媒體中自由釋放心情,分享體驗表達自我,交朋友、寫日記、加好友、傳照片、曬心事……逐漸形成大學生自媒體社群文化現象。在展示自己個性生活的同時,自媒體也成了大學生表達自我訴求的所在,形成了大學生自媒體話語場域,并掀起了大學生“敘事話語表達”的浪潮。大學生通過設立QQ群、BBS跟貼,自拍DV、手機短劇、撰寫博客、微博圈等自媒介手段,記錄大學生原生態的生存狀態,把大學里身邊發生的事情以及對社會的看法寫成博客、制作網頁或以音像形式直接上傳到分享互動網站。如清華大學生anti-CNN事件,大學生自編山寨版春運指南等等。這里既有訴諸于情緒的簡單、直白表達,也有出自理性思考的復雜、委婉敘事;既有超級文本小說,也有虛擬現實、角色扮演,更有遠程交互,無不凸顯了大學生通過自媒體對自身、社會訴求的敘事話語表達。
(三)大學生自媒介德育認知多元化
高校是大學生道德認知生成與行為品性養成的重要場所,而新媒介的草根性與離散性構成大學生自媒體非線性與非邏輯性的敘事表達。在虛擬與現實藕合的時空里,自媒體為大學生自我意識發展提供更多的對話對象和參照標準,大學生在與各種社會資源和各類人物的接觸中不自覺地形成一種開放多元的認知和體驗的成長經歷,從而形成多元的道德認知、行為規范乃至人格品性。特別是大學生的宣泄、另類、叛逆等個性與自媒體產生共振效應,形成當代大學生特有的認知表達方式。據了解,當前惡搞、自拍等現象在大學生中非常流行,這其中也夾雜著許多不良的自媒介現象,如北外女大學生的“香水事件”、南京某大學生自建QQ“后宮群”等事件。甚至有部分大學生經常上泡泡堂、勁舞團等網居社交網站,引發一些網絡與社會問題。
可見,大學生媒介草根話語的興起與微小敘事的取向,對當前高校權威道德敘事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這要求高校教育者必需關注大學生自媒體亞文化現象,從制度、文本的灌輸回歸到大學生個體的塑造來創新德育模式。
二、高校大學生自媒體德育敘事的消極現狀
多年以來,如何增強高校德育的實效性一直是我國教育界的中心課題。從解釋學視角講,教育敘事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教育經驗和現象,而當前大學生自媒體的生成迫切要求高校德育范式轉向,因此,我們有必要在此語境下,對高校大學生自媒體德育敘事的現狀進行梳理考察,厘清高校德育敘事與大學生自媒介主體間的背離與關聯,為切實提升大學生自媒體德育實效性找出突破口。
(一)德育敘事剝離了現實依照與人文關懷
道德教育的對象指向的是人,其必然以大學生主體的特征與本體需求為出發,考量自身的工作目的與途徑。而當前高校教師德育敘事雖然付諸了學生個體與現實關照,但其剝離與忽視了對學生主體的尊重與研究。主要來說,德育敘事缺少學生的生活體驗,缺少與學生的平等交流以及與之相適應共同建構知識的過程。把學生作為一種既定的有預期的受體進行,存在一種客體模子的刻板印象,缺乏“意義”、“對話”與“理解”,沒有讓教師和學生實現“詩意地棲居”[1],背離了大學生鮮活個體在當下的話語表達語境、價值倫理取向以及個體實現本體需求。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當前德育敘事仍然是傳統德育知識體系的沿襲或從“教育者”的經驗出發設計課程體系與知識內容,把學生看作是一個“美育袋”,來灌輸他們認為應該讓大學生知道或掌握的道德規范。可見,其仍然是浮于表面而無法打動人,抑或存于平庸而流于形式無法塑造人。
(二)德育敘事是后驗單子式的教育過程
德育是以學生個體品德的生成與提升為最終目標的,而當前德育敘事主要是從師者的角度進行整理與認知,大多囿于原有知識體系或已完成的教育事件的表達,過于看重德育體系或理論的宣講與傳習,強調宏大社會價值體系或行為規范沿襲的強制要求,缺少對學生個體生命與自我價值實現的關照,缺少對當下或將來的演繹,有學者認為教育敘事講述的是一個“過去”的、已經完成的教育事件,而不是對未來的展望或發出的某種指令。[2]從而造成德育敘事的“平板化”、“文本化”、“簡單化”。當然,德育敘事中也有案例、教學傳記、教育自傳、教育小說等敘事,其中也不乏有些出眾的地方,但從總體上來講,仍存在著說教性太強、個案泛化、缺乏深度等問題,從而容易陷入本本主義與形而上學的誤區。
(三)教師教育敘事與大學生自媒體敘事相脫節
當前大多數學者認為“所謂教育敘事,就是教師以BLOG、BBS等自媒體方式,將自己日常的生活感悟、教學心得、教案設計、課堂實錄、課件等上傳發表,超越傳統時空局限,促進教師個人隱性知識顯性化,并讓全社會可以共享知識和思想”。[3]可見,當前德育敘事主要是教師群體內部的互動交流,以反思并改變教師自身的教學生活,并沒有通過自媒體直接與大學生互動對話,其仍然是一維的封閉的研究過程,割斷師生雙主體或多主體的自媒體敘事場域、德育敘事與教育現實之間的天然聯系,使二者出現背離與對立,形成新型師生博弈,從而走向另一種德育僵化。
總之,大學生不是被動地被說教、考慮或描述的對象,而自媒體消解了傳統師生關系與教育模式,為師生交流提供了新的平臺與語境。因此,我們應認真思考與研討當前高校德育敘事的不足與弊端,積極探索自媒介環境下高校道德模式。
三、高校自媒介主體間性德育敘事的創新
自媒體的表達和傳播方式代表著新型互聯網發展趨勢,當前高校教師敘事與大學生自媒體敘事存在著一定的現實共融性。即大學生與教師兩大敘事主體可以通過自媒體直接對話,并通過多范式的參與、互動、共享達到教學相長。
(一)高校應彰顯尊重主體個體本真的人文尺度
高校自媒介主體間性德育敘事是高校德育工作的擴展與延伸,其必須首先尊重師生雙主體或多主體文化、區域與群體之間的差異以及交流本身的流動性和模糊性。通過德育主體當下現實地呈現交往,反對整體性和同一性,拒絕簡單化和穩定化,強調非中心性和反正統性,倡導多元性、多樣性、主體性和他者性,[4]并需要通過借助類似口耳相傳的兩種文本敘述,進行多義的接受與反饋,進而生成生動活潑的教育情境。高校自媒介主體間性德育中師生敘事主體都應是敘事事件與文本的生產者、傳播者與消費者,在參與共享中自然地達到自我教育理解、信任與支持,從而達到視界融合與“教、學”融合。同時,在這過程中必須賦予主體個體的生命應有的關注與尊重,關注個體的生命經歷和體驗,通過對當下自身真實生活世界的表達與對話,敘事主體應很容易進入彼此的內心世界,真心體會、理解和接納對方,共同思考其道德價值,從而最終達到意義交互共享,“教、學”相長。
(二)必須建立平等共享的對話機制
高校自媒介主體間性德育敘事作為一種道德互動敘事情境,必須是一種“你—我”對話的機制,其超越傳統的主客體二元對立以及主體個體的自我異化與不對等化,強調的是建立在平等、互信、尊重基礎上的教育主體之間的道德體驗與生成。由于其具有自由性與隱蔽性,自媒介主體間性道德敘事主體往往都處于相對精神自由狀態,通過師生雙主體或多主體平等、民主、尊重的自助性交往活動,從而真正擺脫師生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異以及“教育設計”的束縛,實現不同心靈或主體間的互動作用和溝通。同時,自媒體主體間性德育敘事注重的是動態、交叉、交互式過程的把握和演繹,師生在多元開放的論述場域中,通過參與者的共時動態情感與敘事的融合,超越文本本身產生師生感官功能的價值增值以及文本背景的多界面意義的累加,形成一種新型合作者關系,并在敘事表達情境中訴說、傾聽、分享彼此的道德故事,共同感受道德真諦,互相影響、討論、激勵、了解和鼓舞。
(三)推行生活化“情境”道德實踐過程
高校自媒體主體間性德育敘事本身作為一種現象學德育教學方法,消解現有高校德育制度性的既定規范性與程式化,把傳統道德規范化、程式化的傳授轉向生動多元的自媒介鮮活個性敘事,使其“教育生活化”,體現當前高校德育生活的自我參與體驗式的教育目的。高校自媒體主體間性德育敘事是具有一定“情節性”的故事或描述,雖然敘事過程中必然會摻雜著敘事者一定的個人情感、價值乃至目的,具有一定隨機性與偶發性,但它更多的是強調雙主體或多主體的互繞與信任。把有關人倫道德的理論和思想引入鮮活的敘事之中,使受教育者在日常的世界中體驗活著的價值,并通過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不斷地揭示生活世界的意義。[5]通過敘事主體的 “角色互換”、“情境互動”、“虛擬現實”、“遠程交互”,道德敘事主體的角色被弱化,而教育敘事的真實性和感染力更容易使德育主體之間形成道德自我構建體系,從而完成道德的個性生成與內化功能。
總之,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我們需要仔細考量自媒體敘事的演進,反思高校德育敘事的現實,結合當前時代賦予大學生的基本特質,使高校德育注重個體生命的本能,以自媒體為依托,從文本話語轉向生活話語,從道德內容的灌輸、共性的強調回歸到每個鮮明個體生命的關懷與自身發展的引導,從單向的后驗單子式的培養到注重以“交互性”為特質的自媒體敘事場域的德育敘事教化,構建高校自媒體主體間性新德育體系,切實提升德育的實效性。
[1]丁鋼.教育研究的敘事轉向[J].現代大學教育,2010,(1).
[2]劉良華.論教育“敘事研究”[J].現代教育論叢,2002,(4).
[3]教育博客中心.http://js.blogchina.com.
[4]林淑湘.教育敘事研究方法文獻綜述[J].山東教育,2009,(18).
[5]劉丙元.生活敘事:道德教育方式的新取向[J].基礎教育研究,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