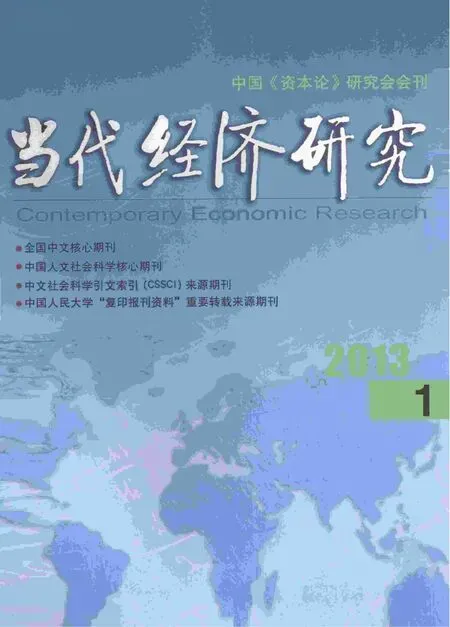為什么全球市場會遭受長期的產能過剩?——來自凱恩斯、熊彼特和馬克思的視角
詹姆斯·克羅蒂
(馬薩諸塞大學經濟學系,美國馬薩諸塞州01002)
引言
在大蕭條和二戰以后,各國經濟普遍都被置于政府的最終控制之下,即使那些市場化程度非常高的國家也是如此,而國際經濟關系也被IMF和世界銀行有意識地加以管理。西方國家的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對工會加以支持,對商業進行管理,加強對金融市場的控制,并建立社會福利體系。它們還通過管理總需求以實現高就業率和快速的經濟增長,這就是所謂的“凱恩斯革命”。商業和金融利益集團接受了這些變化,這部分是因為戰后強有力的資本控制與低水平的貿易和投資流動,使它們沒有對抗政府管制政策的可靠手段。戰后持續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全球繁榮——所謂的現代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強化了市場經濟需要強有力的社會調節才能有效運轉的信念。黃金年代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最終導致了繁榮的終結。[1]經濟的不穩定始于1960年代后期,隨著19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和第三世界國家債務的累積,經濟危機全面爆發。這些問題帶來了一場強有力的運動,其領導者是商業、特別是金融利益集團,這場運動旨在打擊政府對經濟的管制能力,用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取代社會的有意識的調控,消除商品和貨幣跨境流動的限制,創建一個一體化的全球經濟。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持者利用新古典經濟理論來兜售他們的方案。標準的新古典理論認為,如同大學教科書里的完全競爭市場模型一樣,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條件下,一國和全球的經濟將能夠有效地運行。競爭市場的壓力將使勞動和生產性資本得到充分利用,使總需求與充分就業的產出相平衡,即滿足薩伊定律。因此,政府的凱恩斯式總需求管理是不必要的,全球一體化的金融市場將提高效率和生產率,因為,據稱其能夠把全球的儲蓄配置到最優的生產性投資項目中去。對進出口和投資跨境限制的取消同樣能提高效率,因為,這能夠把國內落后的寡頭壟斷企業置于更加激烈的競爭壓力之下,并可以讓小國家的企業也能享受到全球規模經濟的好處。總之,新自由主義者們堅信,只要用全球自由市場體系取代政府主導的經濟體系,就會給所有國家帶來更高的收入增長和更好的經濟績效。
然而,對新自由主義持批判態度的非主流學者認為,一旦放棄以增長為目標的主動需求管理,將會導致實際GDP增長的放緩和失業率的增加。高失業率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反過來造成實際工資的低增長和不公平的加劇。金融的自由化又導致實際利率高企,并增加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用新自由主義代替干預主義的經濟發展政策,也減弱了它們快速長期增長的可能。這些問題并不是全球一體化本身的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是由新自由主義的特殊制度及其實踐所造成的。
盡管雙方都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數據來捍衛各自的立場,但過去二十年的主要證據支持了批評者一方。與黃金年代相比,現在全球收入和資本積累的增長率都出現了顯著的放緩,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的增速下降,大多數國家的社會不平等加劇。實際利率高企,金融危機越來越頻繁(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失業率上升,除東亞以外,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國家的增長也放慢了。
是什么造成了新自由主義時代長期的全球產能過剩?本文把關注的焦點放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一個最重要的經濟問題上,即大多數的全球主要競爭產業中大量過剩產能的產生及其持續問題。
關于全球產能過剩并沒有官方的數據,甚至連一個如何定義和測量產能過剩的共識也沒有。但是,來自咨詢公司、產業貿易協會以及國際組織的研究報告都一致認為,大規模的產能過剩已困擾幾乎所有的全球競爭性產業至少二十年之久了。《商業周刊》提到:“到處都是供給超過需求,造成價格下降、利潤受損和裁員增加。”①前通用電氣董事長韋爾奇認為,“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存在產能過剩。”②《華爾街日報》稱:“從羊絨衫到牛仔褲,從銀飾到鋁罐,世界處于過剩之中。”③《經濟學家》擔心,“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會造成嚴重的通貨緊縮,”并認為目前全球銷量和產能之間的鴻溝是“自1930年代以來之最”。④鋼鐵的過剩產能接近20%,汽車的過剩產能達到30%,而與近期在半導體和通訊行業出現的閑置產能相比,上述數字還算小的。
要充分理解產能的長期過剩,首先必須認識到和新自由主義擴張相伴隨的全球經濟增長的顯著放緩。盡管經濟學家們對這一問題的原因爭執不休,但增長放緩的事實從經驗數據上看是毋庸辯駁的。關于全球經濟長期增長問題,最廣為接受的報告是麥迪遜為OECD所作出的:全球實際GDP的年均增長率從黃金年代1950~1973年的4.9%,下降為1973~1998年的3%,降幅達39%,按人均GDP來算,降幅達到55%;在拉丁美洲,前后兩段時期GDP增速的降幅為43%,非洲的降幅則為38%。GDP增速提高的唯一主要地區只有亞洲(不包括日本),而該地區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也降了下來。[2]聯合國用了與麥迪遜不同的一套方法來計算,得到的結果是:全球GDP的年均增速在1960年代為5.4%,1970年代為4.1%,1980年代為3%,1990年代為2.3%。[3]
新自由主義的鼓吹者們沒有預見到全球經濟增長率的減速,因為他們依賴于薩伊定律,以為需求不可能長期落后于供給。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言,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體現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它假定市場能夠完美地運行,對勞動力以及任何商品或要素的需求必然與其供給相匹配”,資本的供求也是如此。[4]然而,凱恩斯教導我們,在一個不受調節的市場經濟中,總需求是可能會長期不足的,比如在大蕭條時期。
對1970年代初以來的全球需求增長的放緩,給出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是不難的,許多經濟學家已經做到了這一點。過剩產能的最初形成因而也不神秘。但是,為什么全球的供給始終沒有因需求增長率的放緩而相應調整,實現慢一些但更為均衡的經濟擴張?這個問題的答案并不清晰。新自由主義者沒能預見到長期產能過剩存在的可能性,因為在標準的新古典微觀理論中,這是不會發生的。甚至凱恩斯宏觀理論對此也存在盲點,因為它假定總需求增長的放緩能通過對投資和生產率的影響,最終導致總供給增長的相應減速。
筆者對長期產能過剩的解釋綜合了熊彼特和馬克思的觀點,并歸納如下:兩次石油危機及應對其后的通脹所采取的緊縮型宏觀政策壓低了需求,而1970年代末全球主要國家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則給世界經濟的需求增長進一步造成了阻礙。需求增長的停滯反過來又導致了全球競爭性產業過剩產能的劇增。同時,全球的自由化消除了商品和貨幣跨境流動的限制,國內的寡頭壟斷市場失去了保護,全球競爭的強度加劇。初始存在的大量過剩產能,加上資本跨國流動的障礙被清除,引發了企業的生存競爭大戰。正如下面將詳加解釋的那樣,這使得企業采取了那些進一步限制全球需求增長并擴張產能的舉措,它們以超過新古典或凱恩斯框架所能理解的速度去制造更多的過剩產能。因此,全球新自由主義在宏觀和微觀層面的經濟活動之間,激起了一個破壞性的互動,一個惡性的經濟循環。
哪些原因造成了全球需求增長率的放緩?
由于全球需求的放緩已經被許多進步的乃至主流的經濟學家所分析過,因此,我在這里僅列出六條阻礙全球總需求增長的因素,其每一條都根植于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之中。
第一,全球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工資和就業緩慢增長,阻抑了消費需求的增長。工資增長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高失業率、工會的衰落、政府對集體談判支持力度的減弱,以及全球范圍內生產率增長的減速。一份對19個發達國家(不包括美國)的研究發現,在1970年代早期的迅速增長后,實際支出的年均增長率在1979~1989年降至1.2%,在1989~1996年進一步降至0.7%。[5]人們對失去工作的擔憂迅速上升,這是由于進口產品競爭的加劇、實物資本的流動性增強、1990年代的兼并重組大潮,以及與勞動節約型的技術進步和企業采用人員精簡和機構重組戰略,對工作的穩定性長期不斷的“攪動”。通過弱化勞動者的談判力量,工作的不穩定性壓低了實際工資和家庭收入的增長。在許多國家,由于稅負從資本轉向了勞動力,加上家庭債務負擔的上升,工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長也因此受阻。
第二,全球金融體系的演變壓低了全球經濟增長。1980年以來,獨立、保守和飽受通脹困擾的中央銀行實行高水平的實際利率。1980~1990年代金融去管制化的擴散,進一步強化了獨立央行對高實際利率的偏好。對于那些實施低利率以求提振增長和就業的國家,全球投資者們可以越來越方便地利用資本外逃的手段去懲罰它們。進一步地,全球金融市場高度的不穩定性大大增加了銀行和貨幣危機的發生率,危機在其影響的地區內造成了嚴重的衰退,并導致金融投資者們對其所提供的貸款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
第三,私人和公共的投資支出的增長放緩。這是由于低利潤、高實際利率、不確定性的增加、總需求增長的停滯,以及保守派對政府支出的攻擊。
第四,財政政策越來越趨于緊縮。歐洲和北美的政府支出仍然較大,但毫無疑問的是,除了為應對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的低增長和高失業,政府支出曾有過顯著增長之外,隨著保守政治勢力的空前強大,很多國家的政府支出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達到了峰值之后開始下降。作為政府支出和稅收對總需求的凈刺激,1990年代發達國家結構性預算赤字占GDP的比重減少了3.4%,進一步阻礙了總需求的增長。[6]
第五,包括G7國家的政府、世界銀行和IMF在內的內外部新自由主義勢力強力推行的自由化項目,嚴重地削弱了包括東亞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降低了發展中世界的總需求增長。⑤
第六,IMF和世界銀行在發展中國家主導的緊縮和重組項目,嚴重地限制了全球經濟的增長。
為什么新古典“完全競爭”理論不能幫助我們理解長期產能過剩?
要對長期產能過剩作出充分的解釋,就需要一個面向現實的競爭理論。在新古典理論中,激烈的或“完全的”競爭通常能帶來最優的效率,并迅速消滅過剩產能。主流的完全競爭理論主要關注的是完全競爭均衡的美妙狀態,而不是達到這一狀態所要經歷的混亂并常常具有破壞性的非均衡過程。準確地認識新古典競爭理論的短板在哪里是很重要的。
非學術的商業分析和大多數商業史家們懂得,競爭可能變得過度直至對企業“要命”,包括價格大戰、低利潤、危險的債務負擔,以及那些在短期內或許必要卻損害長遠產業效率的做法(例如在勞資關系上的焦土策略)。新古典微觀理論通過兩條在經驗上站不住腳的關鍵假設,排除了劇烈競爭所具有的破壞性方面:第一條在表面上看起來無傷大雅,即生產的單位成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迅速上升;第二條就是資本可以“自由”或無代價地從低利潤產業退出。
該理論的一個主要信條就是激烈競爭將促使價格下降,并一直降到剛好等于經濟學家們所稱的“邊際成本”為止。邊際成本是最后一單位產出所消耗的額外生產成本(勞動力、原材料等)。如果生產的單位成本在任何產出水平上都保持不變,那么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將會相等。當完全競爭促使價格等于邊際成本時,企業的總收入將等于總生產成本,而沒有多余的收入來彌補企業的“固定”成本,即為貶值和報廢準備的用于維持資本存量的成本,或補償那些為企業提供金融資本的投資者支付利息和紅利的成本。在這樣的情形下,激烈的競爭將導致代表性或典型企業在每一個周期里都遭受固定成本無法彌補的損失,最終使產業無法長期持續下去。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數全球重要產業的領先企業都有著巨大的固定成本投入。
新古典理論通過生產的單位成本總是隨著產出的增長而迅速上升這一經驗上的錯誤假設,掩蓋了激烈競爭破壞性的一面。該假設意味著邊際成本和價格將超過平均生產成本,均衡時單位商品價格與平均生產成本的差額足以彌補所有的固定成本,即使競爭激烈,典型的企業也不會虧損。
考慮一個簡單的數值例子。假定某典型企業生產第一件產品的成本是1美元,生產第二件產品的成本是2美元,生產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產品的成本是3美元,那么,平均的單位生產成本就是2美元。即使競爭迫使價格降低到邊際成本3美元,企業仍將在平均生產成本的基礎上獲得1美元。這個價格和平均生產成本的差額將足以彌補固定成本的支出,因此,企業能夠在產業中快樂地生存下去。那末,如果單位生產成本維持在2美元不變會是什么后果呢?顯然邊際成本和價格都將是2美元,因此,價格將與平均生產成本相等,企業將面臨固定成本無法彌補的損失。考慮產業在價格為3美元時達到均衡的情況,假設此時需求出現下降并導致一次暫時的產能過剩,由于產銷量下降,邊際成本和價格也將隨之下降,導致價格和平均成本之間的差額縮小,從而不足以彌補全部的固定成本。因此,產能過剩至少可以讓典型企業在短期內蒙受損失。那么,產能過剩問題在新古典條件下會變得長期化嗎?這里,第二條假設就開始發揮作用了。如果我們假設退出是“自由”或無損失的,那么,產能過剩所導致的虧損將促使企業退出該行業,并把它們的生產資本轉移到利潤率更高的行業中去,直至產能過剩被消除為止。當產能重新得到充分利用時,留下來的企業將重新獲得足夠高的收入以彌補生產成本和固定成本,行業將回歸均衡狀態。
新古典理論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有效運行的市場體系中,產能過剩是一種能夠自我修復的、過渡性的現象,因此,當然不可能長期化。但不幸的是,這個故事是虛構的。要理解為什么產能過剩變得長期化,我們必須把關于邊際成本和投資資本可轉移性的假定建立在現實基礎之上。
全球貿易和投資被以下一些產業所主導,如汽車、電子、半導體、飛機、耐用消費品、造船、鋼鐵、石化和銀行業,我稱它們為核心產業。關于核心產業的經驗研究表明,隨著產能利用率的提高,它們的邊際成本通常并不隨著產出的增長而上升,而是保持不變甚至下降,除非其產能已經達到了充分利用的水平。因此,如果不受約束的競爭迫使核心產業的產品價格降低到與邊際成本相等,最終將會導致一系列的企業破產。
這個問題從重要且新興的信息技術和通訊(ITC)產業最容易看出來,這些產業的產品邊際成本常常接近零,制作一份軟件拷貝或者增加一人次的網絡服務幾乎是零成本的,因此,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也認識到新古典完全競爭理論不能用于ITC產業。例如,哈佛大學校長、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就聲稱,ITC企業有著“巨大的固定成本和相對小得多的邊際成本”。他認為,這種“新經濟是熊彼特式的”:“推動企業生產的唯一動力來自暫時的壟斷權力,如果沒有壟斷權力,價格將會被壓低到邊際成本線上,高額的初始固定成本將無法收回。因此對壟斷權力的不懈追求成為新經濟的驅動力量。”⑥
但這些經濟學家所沒有認識到的是,ITC產業與其他核心產業在這方面僅僅是程度上的區別而已。認識到大多數的生產性資產不能流動是至關重要的,它們很難轉移或變現。因此,企業退出一個低利潤率的行業不是“自由”的,而是要承受資本價值的重大損失。一旦資產購置到位,將其轉移到別的產業或在二手市場上賣掉都將遭受很大損失。一項對航空業的研究估計,“流出該部門的資本只能賣到三分之一的價錢”。[7]近期一些破產的通訊企業則將它們的資產打兩折出售。由于資產不能自由流動,退出將使企業損失其投資資本中的大部分。需要注意,企業在利潤前景黯淡和產能過剩嚴重時離開該產業的動機是最強烈的,但這恰好也是該產業的專用資產價格在二手市場上處于最低點的時候,因為,此時這類資產的供給增加而需求大減。
最后,核心產業擁有的規模經濟范圍很廣,在很大的產出范圍內,企業生產得越多,其成本就越低,因此,營銷努力也越有效,融資的成本也更低。例如,通用電氣、福特汽車和IBM的總資產分別為4050億、2730億和880億美元。[8]這對于核心產業的競爭理論有幾個重要的含義:第一,隨著規模經濟的提升,固定成本上升而邊際成本下降,規模經濟的程度越高,則與激烈競爭相伴隨的邊際成本定價就越具有破壞性;第二,對于核心產業的重點企業而言,過剩產能的增加意味著單位產品固定成本的上升,產能如果達不到充分利用的話,產業就不可能有效運行;第三,參與核心產業競爭所需要的投資極大,因此,退出產業將會有重大損失;第四,由于最低的有效生產規模很大,少量的一些巨型企業通常就能夠給全球市場提供足夠的產能,這使得產業寡頭壟斷協定的建立和延續是可為的。
熊彼特的自然寡頭壟斷理論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新自由主義追求的無限制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內含的全面競爭大戰,將最終導致核心產業的毀滅。只要我們拒絕接受那些支撐新古典競爭理論的不合實際的假定,就能看到企業之間進行必要合作以維持價格顯著高于邊際成本,是核心產業存在和延續的必要條件,這就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為什么把這些產業稱為“自然寡頭壟斷”的原因;也是熊彼特為什么認為,美國經濟史上最重要的產業只有在其主要企業形成“相互尊重的競爭”之后,才能長期地存在下去;商業史學家錢德勒在其經典之作《規模與范圍》一書中,對此也有論述;[9]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商業史學家Louis Galambos最近提到,“全球寡頭壟斷就如同太陽升起一樣不可避免。”⑦
自然寡頭壟斷的企業必須相互合作,把價格維持在邊際成本以上,從而保證有足夠的盈余,才能避免虧損,同時也能為大型的資本品投資和技術進步提供資金。如前所述,規模經濟的存在,使那些占主導地位的少數企業的相互合作在操作上可行。對市場的控制力和相互尊重的競爭還提供了穩定的、有利可圖的環境,使企業能夠承受巨大的固定資本項目投資的風險。最后,企業的相互協定,對于避免大量過剩產能的出現至關重要。或早或晚,大量的過剩產能將促使一些處于困境的企業削減價格、擴張銷量,以降低因產能過剩所形成的過高的單位固定成本。然而,少數企業的降價行為最終將觸發價格大戰,因為其他企業也要維護其自身的市場份額。正如《金融時報》所言,“由于鋼鐵廠或芯片廠的巨額資本投入成為了沉沒成本,當需求減緩時,企業總是趨于在競爭中拼盡全力,最終卻只能沖向邊際成本這個最低點。”⑧受產能過剩的拖累,鋼鐵的近期售價為每噸200美元,明顯低于每噸260美元的生產成本。《商業周刊》報道了計算機硬件產業“在供給過剩和需求停滯環境下的一場無約束的價格大戰”。⑨企業試圖通過非正式的對資本積累節奏的調節,保持供給不要超過需求的增長,以避免產能過剩。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時代全球需求增長率的重大放緩,使得核心產業維持集體紀律以避免供給過剩的努力異常艱難。相比起來,企業之間達成如何分享新市場的協議是容易的,而在由誰承受損失和誰關閉工廠的問題上達成共識就不容易了。
熊彼特強調,自然寡頭壟斷的大企業之間的競爭也是激烈的,盡管通常它們競爭的手段盡量不采取影響行業利潤率的方式。它們通過削減成本的投資、技術和組織創新、市場營銷和分銷策略、開發新產品等手段來謀求高市場份額和產業主導地位。那些在長時間內仍不能降低成本和提升質量的企業,將受到更強大的競爭對手的攻擊。如果行業內的企業在長時間內都沒有實現足夠的成本削減,這將最終導致更高效率的新進入者的侵入,或是顧客會放棄它們并尋求其他替代產品。
熊彼特堅持認為,對于企業動態效率最為重要的競爭形式,并不是靜態的新古典理論所關注的價格競爭。“在迥然不同于教科書所說的資本主義現實中,有價值的不是(價格)競爭,而是新商品、新技術、新供應來源、新組織形式(如巨大規模的控制機構)的競爭,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質量上決定性優勢的競爭,這種競爭打擊的不是現有企業的利潤邊際和產量,而是它們的基礎和它們的生命。這種競爭是……在長期內擴大產出和降低價格的有力杠桿。”[10]盡管進入壁壘給了這些寡頭壟斷企業以較大程度的定價余地,但它們也不能讓價格和利潤率太高,否則將會吸引外來者的進入。因此,核心產業的競爭強度與效率之間的關系比主流理論所認為的要復雜得多。核心產業既可能陷入過度競爭所導致的破壞性價格大戰,又可能由于競爭的壓力太弱,不能刺激足夠的投資、技術進步和保證產業長期存續的成本削減。關于激烈競爭會摧毀核心產業的論點,顯然并不意味著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和相互尊重競爭的結合,就能保證好的績效。歷史告訴我們,現代資本主義市場只有處于有效的社會控制之下,才能實現長期的普遍繁榮。
引入馬克思的理論:破壞性競爭與長期產能過剩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提出核心問題了。為什么過去二十年里全球供給的增長不能隨著全球需求增長一起減速,從而消滅過剩產能呢?把馬克思關于競爭破壞性的觀點和熊彼特的自然寡頭壟斷及相互尊重競爭的理論相結合,帶來了一個有趣的答案。
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摧毀了大多數核心產業維持相互尊重的關系所必需的條件,長期產能過剩就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相互尊重的關系要得以維持,必須依賴長期的需求增長以及對產業內大企業數量的限制。全球新自由主義通過減緩需求增長而加大了產能過剩,通過消除競爭的國家間限制等政策,加劇了競爭的強度。結果就是本文所稱的“強制競爭”(coercive competition)的爆發,這導致了自殺式的定價,安全的寡頭利潤邊際的喪失,以及核心市場上日益脆弱的金融體系。
強制競爭的概念是理解長期產能過剩的核心。在相互尊重的競爭和需求充分增長的環境中,核心產業能實現高利潤,這是成熟工業化經濟體中的大型跨國企業為什么總是謀求行業主導地位的原因。然而,在戰后的發展歷程中,發達國家之間相互進入對方國內市場的障礙逐步消除,而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也試圖進入核心產業,并希望以此攀爬技術—生產率—價值增值的階梯。例如,經濟學家Robert Feenstra構建的美國進口商品滲入指數,從1970年的14%上升到1980年的31%。[11]每一波新進入者都使市場更加擁擠,使企業間的相互合作關系越來越難以維持。如果全球的總需求保持強勁增長,那么新進入者較容易融入到產業中去。在黃金年代,即使日本以及后來的韓國和臺灣開始發展和提升本國的出口,但由于得益于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對國際競爭的限制,北方國家的壟斷巨頭們還能夠維持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的關系。然而,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推行嚴重限制了全球總需求的增長,由于需求的停滯,有新企業進入就必須要有舊企業的退出,才能避免產能過剩。
為什么新企業要不斷進入既不賺錢又不穩定的核心產業呢?一個關鍵原因是,新興國家要想實現經濟發展,必須在技術階梯上一個梯級接一個梯級地爬升。它們無法從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品出口,直接過渡到汽車、電子和半導體的出口。政府因此必須鼓勵本國的企業進入核心產業,或通過設立公共企業來直接操辦。否則,就相當于放棄成長為一個工業發達國家的希望,而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在面對需求增長停滯和新進入者導致利潤下降時,為什么在位企業也不退出呢?新古典微觀理論沒能認識到,在位企業有充分的理由并不急于從無利可圖的核心產業退出。因為,它們有巨大的固定資本以及人力和組織資產,一旦它們被迫退出該行業,這些資產的價值將會遭受重大損失。考慮一下企業不退出的可能前景: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產業內生存競爭的結果是不可預料的,如果能夠提前知道哪些企業會在競爭中失敗,那么失敗者還可以早早退出,以鎖定損失,通常那些明顯比競爭對手弱小的企業也會選擇退出。但是,面對退出的巨大損失,大多數競爭者們還是會試圖留下來。只要能在競爭中存活下來,那些最后的勝利者將會消滅過剩產能,重新獲得寡頭壟斷權力,并獲得安全的、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潤。因此,退出所要承受的損失是確定的,而如果企業能夠在競爭中存活下來,就有希望保存其資產價值,并重新獲得占有壟斷資格和高利潤的前景,這樣一來,拒絕退出就常常成為企業的理性選擇。因此,產能過剩絕不是新古典理論所描述的短期現象。
還可以增加一個觀點來理解產能過剩為什么會長期持續。決定留下來的企業必須繼續投資,以應對行業生存環境的惡化,并增加在生存競爭中獲勝的可能。我的一篇分析競爭在馬克思主義投資理論中所扮演的復雜角色的文章,把這種現象稱為“強制投資”。[12]
要留在行業中,企業必須投資以利用由迅速的技術進步和全球市場一體化所帶來的遞增的規模報酬。投資還出于減少勞動力的需要,通過裁員、工程再造、對勞方的經常攻擊,以及增加對工人的直接監督和控制等。企業必須通過投資,采用最優慣行技術(best practice technology),降低成本和提升品質。在汽車和半導體等核心產業,采用最優慣行技術常常需要巨額的資本投入和擴大生產規模。它們必須投資于款式和型號的改變,以在時尚和潮流變化無常的市場中維持其份額。最后,為了進入未來有很高增長預期的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它們必須到這些國家內部進行投資。上述這些投資項目大多都是增加產能的,并由此制造了更多的過剩產能,盡管企業的投資動因并不是為了制造過剩產能。《經濟學家》發現,新產能形成背后的一個關鍵原因是降低成本壓力與全球化的結合,“在世界各地忙于建立工廠,僅僅只是制造了更多的產能。”⑩當然,在強制投資的過程中也有工廠關閉,但在需求增長停滯的背景下,其影響太微弱而不會對產能過剩的緩解起到多大作用。
熊彼特認為,相互尊重的競爭能夠導向他所堅信的資本主義內在的“創造性毀滅”機制。無疑,強制競爭有其創造性的一面,例如,它加速了廢舊資本的淘汰和新技術的引入,但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下,強制競爭的破壞性方面占據了主導地位,蓋過了其積極的方面。
核心產業中大量強制投資的存在,與我們在經驗觀察中看到的總投資放緩并不矛盾。社會總投資包括居民投資、公共投資、僅為增加產能的投資以及非破壞性競爭產業的投資等,所有這些投資的總額在過去二十年內顯著放緩,并限制了需求的增長。
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個破壞性的宏觀—微觀的辯證法在起作用。在全球新自由主義時代,總需求增長的停滯和長期總供給過剩不斷地彼此強化。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商品和貨幣跨境流動的障礙被逐步消除,全球競爭的激烈程度上升,而全球總需求的放緩,又造成普遍的產能過剩,使競爭程度進一步加劇。競爭越劇烈,企業就越是不得不減少投資支出、裁員、降薪、攻擊工會、并用低工資勞動力取代高工資勞動力,用臨時工取代合同工。商人和高收入利益集團給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削減社會福利和減少基礎設施支出,從而在不增加財政赤字的前提下,能夠對企業和富人實施減稅。政府在壓力下降低了對資本以及流動的熟練勞動者的征稅,利于他們從事跨國的商業活動。但所有這些舉措都進一步限制了全球總需求的增長,進而造成了更激烈的競爭,陷入了一個看起來無限向下的螺旋。
全球汽車產業的強制競爭
全球汽車產業為我們觀察這些競爭過程的運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汽車產業擁有巨大的經濟規模和固定成本。全球市場的緩慢增長趨勢,新的進入和有限的退出,造成了全球汽車產業大量的過剩產能。1999年《商業周刊》報道,全球四十大汽車制造商中,至少有三十家“負債累累且產能過剩:這個產業每年能夠生產的汽車比它能夠賣出去的汽車要多出2000萬輛。”①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認為,全球汽車業的產能利用率從1990年的80%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70%。[11]1990年代后半期,汽車產業巨額的固定成本和大量的過剩產能,消滅了全球除美國之外所有汽車市場上的利潤。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開發新車型和大型汽車廠運營所需的巨額固定成本,意味著汽車制造商將不得不維持或擴大其市場份額。”[12]《商業周刊》指出,這導致了“在過剩產能問題上的自殺式定價”。[11]更糟糕的是,2001年隨著建立在脆弱金融基礎上的美國經濟繁榮的逐步消退,以及美國企業在運動型乘用車(sport utility vehicle)和輕卡銷售上暫時壟斷地位的終結,美國的汽車市場也變得無利可圖。
盡管企業面臨產能過剩、虧損或微薄的利潤邊際以及大量的債務,它們卻仍不斷地在本行業大量投資。為了利用快速增長的經濟規模,投資是強制性的。據估計,當前最低有效生產規模的范圍,從每年200萬輛至驚人的400萬輛。福特、通用和戴姆勒—克萊斯勒都在亞洲投入巨資,盡管要經過8年的發展,銷售規模才能回到1996年的水平。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亞洲“已經變成一個拼消耗的戰場,三大汽車廠商都意在取勝”。[13]與此同時,本田和豐田在美國的產能自1996年以來已經增長了50%。[14]通用公司最近又在土星(Saturn)項目上投資15億美元,以試圖維持其競爭力并由此避免先前的50億美元投資打水漂。[15]戴姆勒—克萊斯勒、大眾和雷諾,計劃未來中期在墨西哥共同投資50億美元建立生產設施。[16]《華爾街日報》報道,“許多專家警告,如果汽車廠商們哪怕是完成了他們所宣稱的新工廠建設計劃的一小部分,亞洲和南美就將面臨巨大的過剩產能。”[17]所有的大型汽車廠商都在投入巨資開發新車型,這種代價高昂的行為被認為是維持市場份額所必須的。
以上大多都屬于強制投資,其主要后果就是在產業內持續地再造過剩產能和債務負擔,延續對工資和就業的向下壓力,以及造成對總需求增長的限制。
展望:全球規模的寡頭再壟斷化?
馬克思為我們理解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視角。他認為,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的平衡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全面的破壞性的競爭最終會迫使企業尋求相互尊重的和平與安全的關系。但反過來,過多的利潤和競爭壓力的長期缺失,又將導致低效率,進而導致國內外競爭者的侵入,重新引發激烈的競爭。下面是馬克思的一段話,這里的“壟斷”一詞應該被理解為廣義的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競爭、壟斷和它們的對抗,而且可以找到它們的合題,這個合題并不是公式,而是運動。壟斷產生著競爭,競爭產生著壟斷。壟斷者彼此競爭著,競爭者變成了壟斷者。……合題就是:壟斷只有不斷投入競爭的斗爭才能維持自己。”[13]
近20年來,快節奏的強制投資、微薄的利潤以及不斷攀升的債務負擔,使核心產業的企業出現了分化,一些企業衰落了下去,還有一些企業維持了相對的強者地位,盡管它們事實上也處于虛弱狀態之中。強制競爭終于開始篩選勝利者,當企業的數量降到足夠少的時候,它們就將試圖重建合作關系,以提升產業的利潤率。盡管技術優勢會對這一過程產生影響,但決定企業在這場生死斗爭中最終勝利的主要因素,則是它們錢袋的深度,而不是設計或生產的效率。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核心產業經歷了一場大規模的兼并與聯合的浪潮。2000年全球的兼并與聯合交易涉及金額為3.5萬億美元,約為1994年的6倍。2000年的跨境兼并交易涉及金額為1.1萬億美元,是1991年的13倍。[18]
結論
目前,全球核心產業的合并進程正處于一個無秩序和不確定的階段,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全球需求增長停滯的時期,當前的兼并運動能夠重建合作的競爭關系,使企業獲得寡頭利潤,從而克服破壞性競爭的壓力嗎?看起來,全球的總需求仍然受到那些造成破壞性競爭的力量的限制,除非全球需求增長有重大的起色,否則,企業試圖重建有效寡頭壟斷的努力將難以成功。而且,即使我們假定核心產業的企業之間的兼并、重組和聯合最終能夠重建有效的寡頭壟斷格局,還將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誰來管理這些全球超級企業集團,使它們的行為符合全球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目前看來,還沒有一個民主化建立和管理的國家或跨國政府機構,有能力和意愿來做這件事情,在未來的近中期也看不到此類機構出現的可能。
(附記:本文譯自James R.Crotty,“Why There Is Chronic Excess Capacity,”Challenge,vol.45,no.6,November/December 2002,pp.21–44,副標題為該文最初作為工作論文發表時所書寫。譯者向悅文,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校對者孟捷,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本文已經得到作者及原載期刊在中國大陸以中文發表的授權)
注釋
①Business Week,January 25,1999.pp69-118
②New York Times,November 16,1997,p.3.
③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30,1998,A17.
④Economist,February 20,1999,p.15.
⑤關于該過程如何在韓國展開的分析,參見James Crotty and Kang-Kook Lee,“Economic Performance in Post-Crisis Korea: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working paper no.23,2001,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UMASS,www.umass.edu/peri/research.html.
⑥Lawrence Summers,“The New Wealth of Nations,”speech presented May 10,2000,San Francisco,U.S.Treasury Department,www.ustreas.gov/press/releases/ps617.htm.
⑦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8,1999,B1.
⑧Financial Times,December 6,2001.
⑨Business Week,June 30,2001,p.32.
⑩Economist,May 10,1997,p.21.
[11]Economist,January 8,2000,p.58.
[12]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6,2000,B1.
[13]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8,1999,B1.
[14]Newsweek,February 4,2002,p.38.
[15]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20,2000,A4.
[16]Financial Times,May 24,2000,p.10.
[17]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4,1999,A1.
[18]并非所有的兼并都是為了重建失去的市場勢力。其中有許多是根源于股票市場上的壓力,當對其所在產業進行再投資以實現增長的做法不再有效的時候,企業則通過系列并購以維持其報告期收益。
[1]Samuel Bowles,David Gordon,Tom Weisskopf.After the Waste land:A Democratic Economics for the Year 2000[M].Armonk,NY:M.E.Sharpe,Inc,1991.
[2]Angus 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M].Paris:OECD Development Center,2001:126.
[3]United Nations,World Economic Survey[M].New York:United Nations,Various Issues.
[4]Joseph 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M].New York:W.W.Norton,2002,p.35.
[5]Lawrence Mishel,Jared Bernstein,John Schmitt.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1998-99[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362.
[6]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M].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0,(4):132.
[7]Valerie Ramey,Matthew Shapiro.Displaced Capital.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No.6755,October 1998,abstract.
[8]World Investment Report[M].New York:United Nations,2001:91.
[9]Alfred Chandler.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Capitalism[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0]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76[1943]:84-85.
[11]Robert Feenstra.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8,12(4):35.
[12]James Crotty.Rethinking Marxian Investment Theory:Keynes-Minsky Instability,Competitive Regime Shifts and Coerced Investment[J].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93,25(1):1-26.
[13]Karl Marx.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