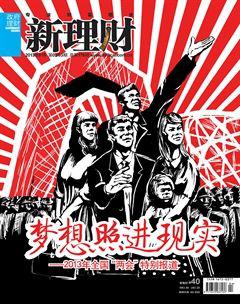二次“燃燒”
亓坤


與退休前逢年過節時門庭若市,拜訪的人絡繹不絕相比,官員退休后門庭零落,幾乎沒人拜訪,退休前后的強烈反差,讓這一部分群體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有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說:“花時間在你這拜年就需要獲得回報,投資要講究回報率,投資虧錢或者賺不到錢,那我還投資你干嘛,”如此一來,“人走茶涼”的現象很容易理解。原來高高在上、眾星捧月的老領導心中的落差不言而喻……
每年的1到3月份,是中國官員的“政治季”,此時也是新老官員的交替輪換季。到了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每個人都不例外要卸任。可對于一名長期忙于工作的高官來說,從崗位上一下子退下來,難免有些不適應,一下子閑著無事干,可能會有些無所適從。
退休以后干什么,是每一個官員不可回避的問題。
準備好了嗎?
對于退休的領導干部而言,能不能“正常降落”并“安全著陸”,能不能在退休之后仍然堅持為民本色,能不能抵制各種誘惑保持清白的人生晚節,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現在,“官員變學者”、“省長變農民”、“市長做商人”的現象應該視為“官本位”思想日益消亡的一個標志。也只有當更多的“官員變平民”成為生活常態,才能彰顯社會的進步。
同時我們也看到,官做的越大,似乎越不自由。有官員表示,其實這是一個喪失自我的過程,出門要秘書安排,講話要秘書寫稿,日程均由別人來定,沒有自我可言。日久必定疏于思考,或者思考也只限于如何讓自己生活得更加穩妥,而不是去想自己曾經有過的理想。欲望日漸強大,內心日益虛弱。有官員這樣告訴記者:“其實,當官的都不愿意退休,退休是無奈地被動選擇。”
很多官員表示,退了真不知道能干些什么!曾經的浙江省財政廳廳長,原中國財稅博物館館長,如今已經退居二線的老財政人,翁禮華表示:“只有有技能,才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如果只會做官,退下來的生活真是不好過。”
退休者要清楚的認識到,退休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個起點。美國多家大型企業的商務顧問,詹姆斯·奧特里闡述了做好哪些準備來迎接和規劃退休新生活,其中包括:決定你在余生中要成為什么樣的人,如何實現;重燃往日的友誼;留出時間發展內在的自我。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表示,目前中國退休保障分三個層級:第一層級是生活必需的保障,退休金、正式和非正式的養老金、企業年金和社會保險解決了這部分人的吃飯問題;第二層級是醫療照顧,這是最重要的保障。他關系到患病者能不能買到長期的醫療和生活照顧,目前中國的養老院不夠成熟,社區也不完善;第三層級是精神上的保障,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政府能力有限,就要發揮社會力量,由非政府組織來完成。當然,更重要的是退休的個人參與。
高官退休后,主要面對的是第三階段:如何做好精神保障。
多樣選擇
退休,顧名思義是退出與休息的意思。過去退休后,老同志多是種種花、養養鳥,帶帶孫子,頤養天年。而如今許多官員退休之后,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選擇繼續對社會發揮余熱。雖說“退居二線”,對一些官員來說,反而是新起點。
多年來的規律是,高級別的官員在卸任黨政職務后,多數到人大政協任職,有些到某協會或企業擔任要職。領導干部作為社會精英群體,長期在政府一線工作,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管理經驗和專業知識,在退離一線后,理應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繼續工作。最美不過夕陽紅,隨著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官員們的退休選擇也趨向多元化。
目前,許多官員根據自己的資歷、專長及愛好選擇退休生活。一些官員退休之后淡出政壇,選擇了自己喜愛的事情。有官員把學者作為自己的新身份。
當官時,因為工作繁忙沒有時間發揮自己的興趣愛好,退休后有時間了,可以做一些深入的理論研究。有官員說:“終于有時間讀讀以前想讀沒讀過的書,看看以前沒看過的影碟。翁禮華告訴記者,“現在自己退下來,發現時間越來越不夠用了,從周一到周五我都要到高校上課,看到學生對我的認可,我教得更有勁兒了。退休了比上班時候忙,但這是自己的愛好,盡管辛苦,卻樂在其中。”閑暇之余,他還苦心鉆研自己喜愛的古代財政歷史,講述中國財政史的《大道之行》就是他的大作之一。
翁禮華表示:“能為國家做點事,同時自身也能跟上形勢和時代發展,不會落后。”
現在退休官員進高校教書是一種趨勢。有人認為領導干部卸職從教,是“能上能下”的表現,這些退休官員,不但知名度高,而且見多識廣,親歷過許多重大事件,具有一般教師所沒有的實際經驗。他們在講臺上出現,大學生倍感興奮。
在中國,“發揮余熱”的退休官員越來越多,他們用自己的經驗和專長活躍于各行各業,同時新工作讓官員卸任之后的生活也變得豐富多彩。官員的余熱溫暖社會,也照亮了自己。
“搶手”高官
一次偶然的機會,與一位接觸過很多退休官員的療養院院長說起, 某官員在任職期間,默默無言,從未表明自己的想法,而退休后新聞不斷,連續多次“炮轟”中國體制的弊端,言語犀利,所指明確,讓人們驚嘆。這位療養院院長告訴記者:“之所以官員在任職期間,對中國體制弊端閉口不言,不在于他的膽量大小,而在于他當時所處的位置,長期受到了羈絆和牽制,有形與無形的壓力如影相隨。但這些官員退休后,不再是官員,他們的聲音只代表個人的看法。”
許多官員意識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狀態,對自己的退休生活有明確的目標,并通過相應的方式體現出來,因此一些退休官員,人雖然退下來心還沒有“退”下來,想方設法吃一頓“最后的晚餐”。官員雖然退休了,但是還有很大的權力資本,企業看中了官員的資源和關系,于是,醫藥協會、能源企業等都聘請退休官員擔任重要職位;上市公司也會聘請證監會前官員擔任高管。
我國是“官本位”的國家,越是高官,越容易被企業看中。一位企業老總解釋:“聘任官員的目的主要是發揮官員的“四余”,即余熱、余權、余威、余網。”對企業而言,這些都是很有用的資產。企業或協會在官員的公權庇護下,規避監管。同時,官員享樂其中,把協會當權力尋租自留地,當作永不退休的港灣。因此,許多高官退而不休,成為“搶手”高官。
當今社會,許多人把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利益,直接體現為權力、資本和權利的置換。退休官員手中的權力資本和聘任官員企業的商業資本一拍即合,權力資本需要商業資本來轉化為實際利益,商業資本也需要權力資本的保駕護航。
權力和資本如果要轉化為利益,操縱、影響制度、政策是一個既定的渠道,現在,有很多退休官員已經通過這個渠道獲得自己的利益。這時,聘請退休官員的單位和官員是一種“合作”關系。長期以來,這種特殊利益集團為維護各自的利益已經找到了快捷有效的路徑。同時這種路徑繼續蔓延的趨勢,大學里的學生畢業向往到政府做官,而現在出現了高官退下來出任大學的院長,今后這種情況如果多起來,面對有限的資源,平等競爭無從談起。
官德之鏡
卸任官員退下來,手上仍握有一定的權力資源,雖然我們相信多數官員的自律性,但是也不可否認一部分官員可能為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因此,退休領導干部隱性的“權力磁場”是法治社會應當考慮并加以限制的。目前職責邊界模糊不清,導致協會與公權部門形成“利益共同體”的觀點。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毛壽龍表示:“從政府退下來的官員進入企業后,利用自己熟悉的政府資源,為他所處的企業跟政府牽線搭橋,其他企業則難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樣就鼓勵企業去搞好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不利于企業的發展,所以要通過規則去改善整個行業的投資環境。”
同時毛壽龍認為,一方面要堵死官員經商下海的出路,另一方面要為他們開放一些領域,厘清哪些方面可以公開,給他們出路。我國目前對這些政府退休人員的工作和生活,還缺少相關的制度安排。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中規定,官員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顯然,法律條款并沒有專門針對地方退休官員進行從業限制,現有法規很難判斷某些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是否與其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而法律在規定從業限制監督主體的時候,更沒有考慮到懲罰退休官員違法從業的艱巨性。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說:“目前地方黨委、政府對在職領導干部監管相對較多,而對退休領導干部,幾乎沒有有效的監督規范手段。”也就是說,他們大多處在監督的真空中。這直接涉及并影響到社會公平能否實現的關鍵問題,所以必須由政府監察機構甚至是法律監督機關來具體執法。?因此,防止退休高官腐敗,不僅要從現任官員處著手,更要切斷退休官員的腐敗渠道。最佳解決方式就是建立健全退休官員從業限制制度,讓不同級別的官員在退休后受到與其權力范圍相適應的從業限制。同時有必要對退休領導干部的去向,作更明晰的制度規范。
由此,應借鑒一些發達國家對退休官員從業受限范圍的先進經驗。比如,美國對高官退休到企業兼職制定了嚴格的約束性法律。1978年,美國國會頒布了《政府行為道德法》,對政府官員離職后的從業行為作出了詳細規定;1989年,政府對該法進行修訂,頒布了《政府道德改革法》,將官員離職后從業行為受限的范圍,擴大到國會議員和國會高級官員,對行政部門官員離職后行為的限制條款也作了修改。該法規要求官員退休或離職后,可以到企業兼職,但是必須申報財產,連親屬財產也要申報,其目的就是為了強化監管。
鑒于此,今年全國“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提出,政府官員退休后不應該到行業協會擔任領導,不能讓協會變成第二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