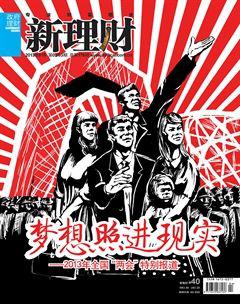讀懂“兩會”
何俊志

每年3月,全國“兩會”都會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高頻詞。在寬泛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兩會”看成是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簡稱;在嚴格意義上,“兩會”應該是指在中國大致同期召開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和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的簡稱。無論是寬泛意義上的“兩會”,還是嚴格意義上的“兩會”,都是在1949年之后逐步形成的一種相對穩定的政治模式。
模式的起源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作為建大綱的《共同綱領》。根據《共同綱領》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有關國家建設事業的根本大計及其他重要措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建議。
1954年12月召開的政協二屆一次會議則正式明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任務已經結束。但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仍然需要存在。
在經過了曲折的變遷之后,1982年的憲法再次確認人民代表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同時,在序言中還提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戰線組織,過去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今后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對我友好活動中,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的斗爭中,將進一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
由此我們可知,寬泛意義上的“兩會”是指:人民代表大會是作國家權力機關的國家政權機關;政治協商會議是作黨派和團體協商的統一戰線組織。
慣例的形成
根據筆者的考證,“兩會”一詞正式用來指稱人大和政協的全體會議,首次出現在1988年召開的人大和政協全體會議期間。但是,兩個全體會議的同期召開及其互動模式的初步形成,則始于1978年。
從表中可以看出,在1978年之前,人大和政協的全體會議并未同期進行。在1978年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有相當一部分會議是與政協五屆一次會議同步進行。而且,正是在這一期間,政協全體委員列席了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聽取和討論了政府工作報告、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報告及修改憲法的報告。
或許正是由于兩個全體會議都需要聽取政府工作報告、財政預算報告和經濟社會發展報告,客觀上需要將兩個全體會議置于同一議程之內,才能使“兩會”成為一種政治上的慣例。與此同時,政協先于人大召開全體會議的慣例,同樣也是在1978年的五屆一次會議時形成的。1998年之后逐步穩定的模式是,全國政協一般在3月3日開幕;人大則在3月5日開幕。在開幕式之后,全體政協委員都列席全國人大的全體會議,共同聽取國務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所做的工作報告。
功能差異與銜接模式
根據相關法律和章程的界定,人民代表大會是權力機關,人民政協則是統一戰線組織。前者是法定的立法和監督機關;后者則是黨派性的協商機關。但是,如果我們按照現代政治與行政二分的基本理論來觀察,就會發現,無論是人民代表大會還是政治協商會議,都不是體現國家意志執行的機關,而是一種體現政治表達職能的議事機關。作為政治表達的議事機關,二者都具有代表特定的社會群體,在公共平臺上表達政治意志的功能。所不同的只是,承擔表達功能的成員地位和表達途徑不一樣。
就成員性質而言,根據現行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所有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都必須依法通過選舉的方式產生,選舉產生的代表享有代表法所授予的某些特權,并承擔相應的責任。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則是依據政協的章程而協商產生,其權利和義務由政協的章程所設定。
除解放軍代表團的代表之外,全國人大的其他代表,都是以地域為基礎,由地方代議機關選舉產生,因此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以地域為基礎組成的代表團,就是全國人大全體會議召開期間的基本活動單位。而以黨派和團體為單位而協商出來的委員,在會議期間則以功能界別為組成單位。
根據憲法和全國人大組織法的規定,我們可以把全國人大的基本職能歸納為制定和修改法律、決定重大事項、任命官員和監督法律的實施。政協的章程則將政治協商會議的職能定義為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
在寬泛意義的“兩會”關系上,一些研究者曾經認為,人民代表大會主要是選舉民主,人民政協主要適應的是協商民主。人民代表大會也要協商,但主要是投票選舉;人民政協里面也有選舉,但主要是協商。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是選舉加協商的民主制度。另外有學者則認為,人民代表大會所體現的是關于國家政權的人大民主;執政黨的民主機制則體現黨內民主;以政協、多黨合作和基層自治體制的是社會民主。
在嚴格意義的“兩會”關系上,也有研究者觀察到,政治協商會議與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同時召開,其成員可以相當便利地接近官員。政協會議一般都比相應的人代會議更為活躍,很可能是因為它有較大比例的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
筆者也注意到,在執政黨的領導和協調下,“兩會”之間正在探討更加緊密的銜接途徑。這種銜接途徑除了表現為“兩會”同期召開期間的銜接機制外,還表現為全體會議閉會期間,各級人大常委會與政協常委會之間的工作溝通機制的多元化趨勢。
不過,無論是寬泛還是嚴格意義上的“兩會”之間銜接和互動模式,目前還在相當程度上處于探索期,有不少慣例的成分在內。無論是“兩會”的會期制度,還是開會與閉會期間工作制度,都還存在著較大的制度探索空間。
在“兩會”并行模式已經成為慣例的情況下,實際上也還存在著一些值得探討的問題。例如,在各級人大和政協之中,存有一些官員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政協委員。這些官員在“兩會”同期召開的情況下,到底應該參加人大會議還是政協會議,就是一個難以協調的問題。還有學者建議,將“兩會”提前到每年的1月召開,更有利于對政府工作和各種報告的審查。不過,在“兩會”大致同期召開的慣例作用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在開會和閉會期間逐步探討出一些更為多元化的銜接和互動模式,應該是一種可以預測得到的趨勢。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選舉與人大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