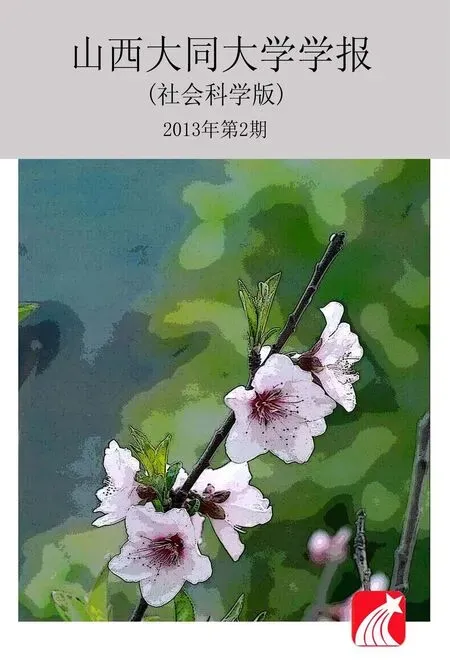唐弢書話:現代書話創作模式的成型
徐 敏
(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4)
唐弢書話:現代書話創作模式的成型
徐 敏
(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河北 秦皇島 066004)
唐弢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雜文和散文作家,他的書話創作被認為是現代書話成熟的標志并對后人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唐弢看重書話自身的文體特性,提出了四個“一點”的創作模式,在具體寫作中表現出豐富的版本學和掌故內容,提出獨到而精當的品評,傳達出醇厚的情感色彩。其現代題跋式的寫作為后人提供了摹仿的范本。
唐弢書話;四個一點;品評;抒情
唐弢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在多方面有突出的建樹。當年他獨具慧眼,關注新文學的版本問題,購買和收集了大批現代文學書籍和期刊。據統計,其藏書共有4.3萬冊,書籍為2.63萬冊,報刊有1.67萬冊。其中毛邊書和初版本就達到上千冊。關注新文學的版本問題,唐弢可以說是第一人。正如黃裳所說:“在四十年前,如果有誰提出新文學書也有版本問題,大抵是必然會引起哄堂大笑的吧。”[1](P221)“最先留心收集新文學史料,為研究奠定了基礎的,是阿英;但注意新文學出版物的版本,系統加以評論記述的,則不能補不首推風子(即唐弢)。”[2](P111)
唐弢愛書、藏書,又是新文學的親歷者,這些客觀因素奠定了他書話創作的優勢。唐弢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創作書話,其書話和對魯迅佚文的收集整理工作一道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史料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石,而且他的書話創作為現代書話體式的形成和成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實例。正如黃裳分析的那樣:“今天已成為顯學的新文學史料研究,繼起者的業績在許多方面已超過了前人,但《晦庵書話》仍有其歷史地位,是這一學術領域的開山之作。作為散文,‘書話’這一形式也是值得注意的。以簡短的筆墨,記事抒情,作者繼承的是古老的優秀文學傳統,使人想起的是陸游的‘放翁題跋’和黃蕘圃的藏書題識。回蕩多姿卻無空疏之病;網羅遺事,不離時代風云。所記三十年代前后反動派對革命書刊的封鎖、扣留、禁毀與世界進步力量的抗拒斗爭,都是文化史上不可磨滅的大事,也形成了《書話》觸目的特色。”[2](P111)
唐弢的書話不僅獨具特色,而且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直接帶動了其后一大批書話作品的出現。如趙景深于1946年在《上海文化》中以《書呆溫夢錄》為題,發表了一組現代文學書話。他在文后贅言:“晦庵的書話極富于情趣,有好幾篇都是很好的絮語散文,意態閑逸瀟灑,書話本身就是文藝作品。我因為喜愛它們,便每天從《文匯報》上剪下來保存。”[3](P2~3)散文家何為承認自己的作品近乎晦庵的書話,記敘與抒情兼而有之。他說:“我是《書話》的熱心讀者,同時又是《書話》散文的拙劣臨摹者。”[4](P405)當代書話創作大家姜德明也是在唐弢書話的引導下走上了研究新文學的正確道路:“到了40年代中后期,突然發現唐弢先生寫的關于新文學的書話,一下子頓開茅塞,好像找到了一位引我入門的老師。我羨慕他的藏書豐美,那些充滿魅力的版本一直誘惑著我。我采取的是笨辦法,循著他書話中提到的書一一去搜訪。讀唐弢的書話,打開了我的眼界,如讀一部簡明的新文學史。”[5](P2)徐雁“不意在讀了1979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增版了的《晦庵書話》以后,自己居然反其‘道’(“書可遇而不可求,書可愛而不可嗜”——筆者注)而行之,竟一度嗜之求之,并因此開啟了自己的藏書愛好。”[6](P1)唐弢的書話不僅在大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波及到海外。香港的黃俊東和林真就是在唐弢書話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新人。
唐弢創作書話并且是新文學史上直接用“書話”一詞來命名自己書籍的第一人。他的書話作品不僅是現代文學史料學方面重要的資料,而且在他的手中,書話這種文體在現代創作中真正成長、獨立出來。因此,對唐弢的書話展開細致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書話寫作歷程
唐弢于1945年春天開始創作書話,之后在抗戰勝利后、50年代中期、60年代上半期都斷斷續續寫過一些,一直到70年代末編定《晦庵書話》,再加上《唐弢文集》中的32篇,共計209篇。唐弢的書話創作不是一以貫之、一帆風順的,其中的曲折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艱難。
1945年6月唐弢在柯靈主編的《萬象》第七期上發表了十二段書話。不久因為柯靈被捕,書話創作中斷。到1945年末,因《文匯報》編輯的邀請唐弢再次動手創作此類作品,發表在副刊“文化街”上。之后寫的書話不僅在《文匯報》上發表,還登載在《聯合晚報》、《文藝復興》、《文訊》、《時與文》等報紙和雜志上。據唐弢自己說,其數量有一百篇的光景。后來因為書話內容得罪了一個“要人”而中斷。其書話創作的再次接續就到了1961年,開篇發表在1961年3月30日的《人民日報》第八版上。這次創作的因緣是《人民日報》的約請,當時唐弢還寫過一段“綴言”:“解放前后我曾寫過一些《書話》,于閱讀之余,把想到的事情隨手記下,給報紙做個補白,不過當時偏于個人興趣,太重版本考訂,沒有把《書話》寫好。倘能于記錄現代文化知識的同時,不忘革命傳統教育的宣傳,也許更有意義。”這段話體現了在新時代環境下作家的新興意識,其中可能也有作家對自己作品的一種委婉解釋。當這些書話新作陸續發表了二十多篇時,北京出版社請唐弢編集,他“覺得數量太少,舊稿又大都散佚,只能就手頭剪存的部分選改十幾段,合成四十一篇。”[7](P5)1962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書話》。這的確是一個小冊子,全書共七萬余字。封面由侯叔彥設計,“書話”二字為魯迅墨跡,左下方是“晦庵”兩字的朱文印章。《書話》出版不到一年,就印刷了第二次。第一版印數3萬,第二版印數為2萬。在第二版印刷時,因為“國內的輿論,對凡爾納突然提出責難,曾經出版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和《神秘島》都無法重印,《書話》也遭池魚之殃”,[8](P5)所以唐弢應出版社之請,用《閑話<吶喊>》一文替下了《科學小說》一文。第二版的封面由關景宇設計,淡底木紋,“晦庵”二字升了格,置于封面左上方,但變成了黑體,“書話”二字仍沿用魯迅手體,置于右下角。
唐弢書話的第三次結集出版于1980年10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取名為《晦庵書話》,“封面由裝幀大家錢君匋設計,典雅、素凈、淳美、奇巧,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扉頁的書名皆出自唐弢之手,全書24萬余字”[9]書中除收入了原來出版的《書話》外,還“收錄了《讀余書雜》、《詩海一勺》、《譯書過眼錄》和《書城八記》四個部分。前三個部分是全國解放前為書報雜志包括《萬象》在內而寫的書話。”[8](P4)《書城八記》寫于1965年,最早在“香港《大公報》副刊《藝林》上陸續刊載,談的是買書、藏書、借書、校書、刻書的掌故。”[8](P4唐弢將這本《書話》取名為《晦庵書話》,作者也直署本名。他在《序》中表示:“這并非王麻子,張小泉似的,要掛出招牌,表示只此一家,別無分出;倒是根據幾位朋友的意見,將全書內容變動一下,稍加擴大,收入其它幾個部分,因而有必要另取書名,以便和已經出版的《書話》區別開來。”[8](P3)
從唐弢書話創作的具體內容來看,基本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作家及其作品情況。唐弢筆下既有現代文學史上的大作家,如魯迅、周作人、茅盾、鄭振鐸、瞿秋白、郁達夫、郭沫若、許地山、王魯彥、聞一多、朱湘、梁遇春等,也有宋春舫、楊振聲、凌叔華、孫福熙、川島等一批現代文學史上較少談論的作家。唐弢談到的作品,有魯迅的小說、翻譯、版畫、序言,有劉半農的詩歌,王統照的詩歌,朱自清的散文,許地山的小說,茅盾的《子夜》和《春蠶》等。《晦庵書話》的《詩海一勺》欄目下收文章27篇,談的全部是詩作。除了創作外,唐弢還關注翻譯情況。《晦庵書話》的《譯書過眼錄》中收有文章54篇,談的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翻譯出版的各國文學,涉及近20個國家的約60位作家的作品。唐弢書話所談的第二個方面是當時文壇的一些掌故。他發揮了自己親歷的優勢,為讀者講述了當年的翻版書、禁書、“左聯”的斗爭情況等史實。書話內容的第三個方面是一些比較專業的知識,如圖書版本、藏書印、藏書票、封面畫及畫冊的裝幀等問題。
唐弢的書話創作顯示了他學識的廣博和研究的深入,不僅體現著作家的真知灼見,而且為中國現代文學、文學史、史料史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養料。
二、書話創作模式的定型
唐弢最初是以雜文創作登上文壇的,并因此與魯迅先生結識。但唐弢說自己更喜歡的是一些詩性的創作。他把散文分為三部分,“回憶往事,記述當前的生活,算是敘事散文;借一點因由,發抒隱藏在心底的感情,便是抒情散文,或曰散文詩;以議論為主,評騭社會,月旦文明,那就是社會雜感了。”“我自己倒是喜歡敘事散文和抒情散文的,并且花了較多的心力試寫過。”[10](P187~188)唐弢的書話可以說是他在敘事散文和抒情散文創作方面的一種創造性探索,既有對書話創作模式的總結,也體現出他創作的獨有特色。
從現代書話的創作歷程來看,20世紀30、40年代可以算是創作的成熟期。不僅有曹聚仁在名稱上首次提出“書話”一詞,更有一批書話寫作大家的出現,如魯迅、周作人、鄭振鐸、葉靈鳳、郁達夫、阿英等。他們的創作各具風姿,充分體現出書話寫作的靈活性和多樣性,也使得后人難以摹仿。而到了唐弢這里,他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壇上系統地、有意識地創作書話的第一人,在創作的主導思想和寫作體式上都有自己的見解,這些見解直接影響了其后的書話創作,并成為一種范式,為后人提供了可資借鑒、摹仿的范本。
首先,在書話的文體上,唐弢明確指出,書話應該屬于散文創作。他說:“我也曾努力嘗試,希望將每一段書話寫成一篇獨立的散文。”這種散文要具有自己的特點,即“書話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它給人以知識,也給人以藝術的享受。”[8](P5)唐弢對于自己的這個看法是非常認可的,在《林真說書·序》中他再度做了重復性的闡釋:“我反對有些人把書話僅僅看作資料的記錄,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以為它是散文,從中包含一些史實,一些掌故,一些觀點,一些抒情的氣息,給人以心地舒適的藝術的享受。”[11](P235)正因為把書話看作是散文,要求其能傳達出藝術的美感,所以唐弢也多次談到,“我以為書話雖然含有資料的作用,光有資料卻不等于書話。我對那種將所有材料不加選擇地塞滿一篇的所謂‘書話’,以及把書話寫成純粹式資料的傾向,曾經表示過我的保留和懷疑。”[8](P6)這樣唐弢就為書話劃定了文類——散文,確立了書話的文體,并明確指出一篇書話應該包括四個“一點”(一點史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這四個“一點”確立了書話在創作內容及創作手法上的風格,唐弢也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四個“一點”。所以趙景深對其創作的評價是:“晦庵的書話極富情趣,有好幾篇都是很好的絮語散文,意態閑逸瀟灑,書話本身就是文藝作品。”[12](P224)
其次,唐弢也指明了自己的書話創作是有來源的:“我寫《書話》,繼承了中國傳統藏書家題跋一類的文體,我是從這個基礎上開始動筆的。我的書話比較接近于加在古書后邊的題跋。”[8](P5)“中國古代有以評論為主的詩話、詞話、曲話,也有以文獻為主,專談藏家與版本的如《書林清話》。《書話》綜合了上面這些特點,本來可以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不過我目前還是著眼在‘書’的本身上,偏重知識,因此材料的記錄多于內容的評論,掌故的追憶多于作品的介紹。至于以后會寫成什么樣子,那是將來的事,不必在這里預告。”[7](P3)從唐弢的表述來看,其書話創作對傳統的題跋是有著積極的借鑒和繼承的。在此基礎上,又加入了他獨有的內容:即現代版本知識和現代文壇掌故。
三、書話創作的特色
唐弢具有自覺的書話文體意識,總結出了四個“一點”。在具體的行文中,他也是圍繞這四個“一點”而展開,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為現代文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一,豐富的新文學版本知識和文壇掌故成為書話的表現重心。
中國從鴉片戰爭之后,受到西方經濟、政治的極大沖擊,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放眼世界,學習西方的先進知識和理念。到了“五四”文化運動時期,科學、民主的大旗更是成為時代的風向標,向西方學習成為一種主流。經過了“五四”文化運動的振蕩,經過了對東西方學術的思考,從2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傳承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開始投身于古籍的整理、校勘上。在現代文學史上,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阿英、鄭振鐸、周氏兄弟等。與對古籍的搜集、整理的重視程度相比,當時的知識分子對于當代文壇,即當時的史實關注的程度較弱,當然這也和當代史不被看做歷史這種觀念有關。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本應該保存下來的資料、文獻被忽視遺落了。與這種大的風氣相對,唐弢卻對當代的文壇情有獨衷,他積極地收集新文學以來的各種書籍和雜志,把古代學者的版本學、校勘學、文字學等知識運用于現代文學史料的考稽辨析、研究和校訂工作上。因此,在他的書話中,對于所談的每一部作品的版本、版式、版次、裝幀等都有詳細的介紹。
其次,作為現代文學、魯迅研究的專家,唐弢所面對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即自己直接經歷過的,參與了的,有的還是親身為之奮斗過來的那段文學歷史。”[13]對這段歷史的親身體驗和直接把握,就為唐弢書話的寫作提供了真實的、豐富的掌故。通過掌故,讀者可以了解一部書籍的成因、書人之間的交往、得書的經歷等等,掌故的記錄本身就能增加文章的故事性、情節性,增加書話的可讀性和文學性。而唐弢在方面所占有的優勢讓他的書話不僅給讀者留下了強烈的印象,而且為新文學提供了大量翔實的史料,成為后學研究新文學不能忽視的重要遺產。
如在《守常全集》一文中,他回顧了編輯李大釗的著作從《文集》到《全集》再到《文集》,一直到解放后才出了《守常全集》這段曲折的出版史掌故,讓讀者體會到在政治高壓下出版業的艱難。《<子夜>翻印版》介紹了由救國出版社出的翻印版反而是《子夜》的全本,其裝幀、字形非常優秀。《藥用植物及其他》這部魯迅先生的譯本曾于1936年6月出過單行本,并且銷行很廣。這都是后人難以知道的史實。在《詩海一勺》的27篇文章中,唐弢為我們展現了很多珍貴的、甚至是已不能見的初版本,如《昨日之歌》、《紅紗燈》、《烙印》、《君山》等。
第二,“觀點”的精辟和“品評”的精當見出深厚的文學研究功力。
唐弢指出,書話寫作要有“一點觀點”,這個“一點觀點”就是對作家作品的一種評論。在這方面,體現出唐弢突出的才能和深厚的文學修養。
如在《朱自清》一文中,唐弢引述了葉圣陶對朱自清的評價。葉圣陶認為朱自清“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都有點兒做作,太過于注重修辭,見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寫《歐游雜記》、《倫敦雜記》的時候就不然了,全寫口語,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方式,雖然有時候還帶有一點文言成分,但是念起來上口,有現代口語的韻味。”[14](P20)唐弢同意葉圣陶的看法,不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覺得佩弦先生晚年文章偏于說理,倘論情致,卻似乎不及早年;不過思想成熟,腳步堅實,再加上語言上的成功,這些地方遠非早年所可比擬而已。”唐弢認為“在藝術上,語言是文學的根本問題,卻并不是它的全部問題。有些散文語言很好,甚至還很有個人特點,然而卻不一定都有情致。”而人們之所以更愛讀朱自清早期的作品,就因為這個道理,所以他提出“研究朱自清后期散文的語言,注意朱自清前期散文的情致,我們將會更清楚地了解朱自清的風格。”[14](P21)唐弢在文學品評方面,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能夠提出自己的觀點,有著自己的看法,對于散文如此精辟、獨到的分析,既顯示了他在文學研究方面的能力,同時也讓讀者深為佩服,這也是其書話之所以受到歡迎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唐弢書話的行文都不長,但他往往能在只言片語中準確地抓住作家作品的風格特征,在寥寥數語中揭示出作家作品的特色。凌叔華“以素淡筆墨,寫平凡故事,如云林山水,落筆不多,而意境自遠。可與丁西林的獨幕戲劇同觀。”[8](P185)川島的“文字清新婉約,情致纏綿,不脫一個真字”[8](P197)。而“新文人中頗多精于舊詩者,達夫凄苦如仲則,魯迅洗練出定庵,沫若豪放,劍三凝古”,[8](P281)沈尹默的舊詩則是“灑脫清麗的情調,貫穿著尹默全部詩作,把大自然看得既和平,又溫柔,此在詩人心中真是另一境界也。”[8](P280)在這些品評的文字中,唐弢并不多作闡釋和發揮,而是讓這些簡單有力的文字散見于他的作品中,到處如珍珠一樣在閃閃放光。
唐弢說自己的書話創作也來源于古代的詩話、詞話、曲話,這些評論就很帶有詩話、詞話或曲話的特點。當然,他的這種評點不是局限于作品本身,而是能夠和作家的經歷緊密結合,在知人論世基礎上的評點帶有了更多的歷史內涵和理論含量。他評價何其芳:“戰爭改變了許多事情、許多人,就我所知,改變得最多同時也就是進步得最快的要算何其芳。雖然作者說他有他自己的道路,但就所表現的看來,他確是從陰暗和寂寞里突然跑到陽光底下,由沉思而歌唱了。”[8](P271)三言兩語勾勒出了何其芳創作風格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變化,同時也指出了詩人人生道路的重大改變。
歷史的內涵加諸到傳統的評點上,體現出更有現代性的評論方式,更凸顯了唐弢的審美眼光和藝術識見與功力。
第三,“抒情”色彩的融入使得書話具有深厚的感染力。
唐弢對抒情散文非常喜愛,尤其推崇能夠傳達出詩的情緒的文章。在《茅盾雜文集·序》中,他寫到:“茅盾先生是不乏詩的感情的。他不僅寫過魯迅式的詩似的雜文,我還以為,他寫的散文,例如《賣豆腐的哨子》、《紅葉》等篇,那就完全是詩的了。盡管他自己稱之為散文,而這些篇什傳達給我們的幾乎都是詩的境界,一種引起凝思遐想的動人的詩的境界。”[15](P534)將這些品評移用于唐弢本人的作品,將更為恰當。唐弢的散文、雜文,甚至論文,都表現出他特有的詩情氣質。在創作書話時,他說:“我曾竭力想把每段《書話》寫成一篇獨立的散文:有時是隨筆,有時是札記,有時又帶著一點絮語式的抒情”。[7](P3)抒情因子的引入使得其書話富有了強烈的浸潤力和感染力。
在《童心》一文中,唐弢講述了和王統照之間的交往,回憶起抗日戰爭初期留居上海相聚小酌,快談古今的光陰。解放后,王統照又煥發了生命的活力,正是“恢復‘童心’之期,”也是他二人可能再歡聚的時期,但世事不如人意,“如今故人謝世,墓木且拱;往事如昨,而我已無法再踐‘樽酒論文’之約了。”[7](P19)對友人懷念的深沉慨嘆把讀者帶入了惆悵的境地。
《<沉鐘>之五》記述1944年時,唐弢為“阻止魯迅在平家屬將藏書出售”一事到北平,住在“西總布胡同錢泰大使寓所”,在東安市場買到了《<沉鐘>之五》,讀其中楊晦的《除夕及其他》。“各篇都用對話體寫,如獨幕話劇,而充滿散文詩氣息,深沉黯淡,令人心碎。”而“我讀此書時適在錢家二院,院有海棠一株,時正結果。晚風起處,海棠時時落地,一種黃昏的寂寞浸透身心,及今思之,猶悵惘不已。”[8](P209)文中記述了得書經過、閱書之感,在結尾收束處又刻畫了讀書之境,那種情緒的渲染非常深厚。不僅使唐弢和所評作者作品之間達到了一種共鳴,而且讀唐弢書話的讀者也能從中體味到那種醇厚。
唐弢的書話創作帶有明顯的個人風格,詩情非常濃郁。收于《晦庵書話》中的作品基本是按照他所提出的“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去實踐的,而且這種實踐漸漸變成了一種寫作模式。我們僅舉《山中雜記》一文來體會:
《山中雜記》一冊,鄭振鐸著,開明版,四十八開小本,封面印莫干山照片一,篆文“山中雜記”四字,大概出葉圣陶手筆。再版改作鉛字排印,封面紙變淺藍色,畫楊柳月。全書收散文十篇,第一篇為《前記》,說明由上海到莫干山的沿途經過,副題為“山中通信”,所以是書信的形式。其他九篇記山居生活,偏報導性,今年 (1946年)夏天,我們本有往莫干山計劃,振鐸擬作一月逗留,而人事栗六,終不果行,絡緯聲中,轉眼又屆秋令,勞生碌碌,此愿何日得償乎?[8](P220)
在這段文字中,從開頭一直到“偏報導性”,都是基本知識的介紹,包括作者、版本、裝幀、基本內容等方面,看起來頗近于中國傳統目錄學的解題。接下來提起曾和鄭振鐸相約的莫干山之行計劃一直未果。結尾則是“絡緯聲中,轉眼又屆秋令,勞生碌碌,此愿何日得償乎?”作家由一事聯系到人生,透露出人事匆忙、人世滄桑的情思,簡單的幾個字使得全文頓時具有了一種生氣,讀者也在“勞生碌碌”中發出深有同感的嘆息。
這篇文章的寫法可以說是古代藏書題跋書寫的現代版本。其行文的順序、方式非常接近,只不過唐弢談的是新文學作品,運用的是現代白話。在唐弢之后,他所提出的“四個一點”不僅成為對現代書話認識的重要結論,而且從寫作上也成為對書話的一種規范。尤其是上舉他的題跋式的現代寫法,影響了一批人的創作。且不說黃裳創作的多篇“擬書話”,就是在黃俊東、姜德明的書話創作中,我們也能看到唐弢書話的影子。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唐弢的書話寫作標志著現代書話創作的成熟,為現代書話提供了創作模板。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種成熟的創作模式一方面給后人提供了可資借鑒和摹仿的范本,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書話創作的多樣性。在80年代之后的大量的書話寫作中,除了黃裳、孫犁等獨特的存在之外,在姜德明、黃俊東等人的創作之后,我們已經很難欣賞到獨具個性的創作了。這也是書話發展到今天面臨危機的原因之一,值得我們深刻反思。
[1]黃 裳.黃裳書話·先知[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2]黃 裳.春夜隨筆·悼風子[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姜德明.現代書話叢書(第二輯)·序言[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4]何 為.何為散文選《小樹與大地》自序和后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5]姜德明.現代書話叢書·序言[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6]徐 雁.秋禾書話·書話因緣(代序)[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
[7]唐 弢.書話·序[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8]唐 弢.晦庵書話·序[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
[9]高 信.從《書話》到《晦庵書話》[J].當代文壇,1984(8):49.
[10]唐 弢.唐弢書話·生命冊上·序[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1]唐 弢.唐弢書話·林真說書·序[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12]趙景深.新文學過眼錄·書呆溫夢錄[M].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3]樊 駿.唐弢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J].文學評論,1992(4):6-20.
[14]唐 弢.朱自清·書話[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15]唐 弢.唐弢文集·茅盾雜文集·序(第9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
〔責任編輯 郭劍卿〕
The Book Chat of Tang Tao:the Confection of Book Chate Mode
XU M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Yanshan University,Qinhuangdao Hebei,066004)
Tang Tao is an important essay and prose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his book cha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dern sign of maturity an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to future generations.Tang Tao valued the book chat's stylistic features and made four“points".In his book chates,there are rich version of science and anecdotes content,unique and precise evaluation and the sweet emotions of color.On the other hand,his modern legends writing provides a model for imitation.
book chate of Tang Tao;four"points";evaluation;express emotion
I206
A
1674-0882(2013)02-0042-05
2013-01-28
河北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SQ126018)
徐 敏(1973-),女,山西大同人,博士,講師,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