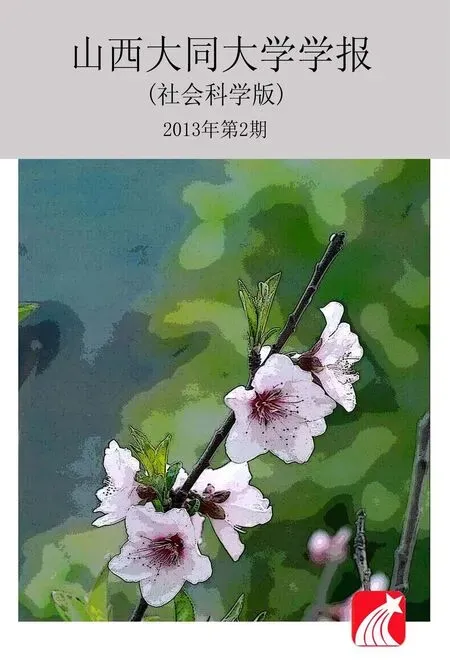論文學翻譯中譯者對文化預設的處理
——以《紅樓夢》的楊譯本和霍譯本為例①
楊麗華
(長江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論文學翻譯中譯者對文化預設的處理
——以《紅樓夢》的楊譯本和霍譯本為例①
楊麗華
(長江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紅樓夢》涉及中華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本文根據奈達文化分類法,以《紅樓夢》的楊譯本和霍譯本為例,比較分析兩譯本對文化預設的處理:楊譯本傾向于盡可能傳達原文的文化預設信息,霍譯本則傾向于消解原文的文化預設信息,兩譯本不同的處理策略主要受到譯者文化心理、社會文化語境和贊助人的影響。
文化預設;文學翻譯;紅樓夢
文化預設為預設在文化領域中的拓展,即交際雙方共同擁有的文化背景知識。根據奈達(Nida)的文化分類法,此共識性文化背景涵蓋了生態、宗教、物質、社會和語言五個方面。[1]處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文化預設,在溝通交流時就可以省去那些雙方已熟知的共識性文化信息。
在文學翻譯中,文化預設的處理對譯者而言是一個巨大挑戰。在文學作品創作過程中,作者通常認為其讀者擁有與他相同的文化背景知識,會省略那些無需加以言明的內容,許多文化預設便成了隱含信息。來自其它社會文化的讀者讀后往往不知所云,跨文化交際障礙由此而生。翻譯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譯者必須克服種種困難,盡全力詮釋出原作中的文化因素。同時,譯者也不能置讀者的接受于不顧,造成作品枯燥難讀。
我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目前有兩部傳播較為廣泛的英譯本:一為中國譯者楊憲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所譯,另一為英國譯者霍克斯(Hawkes)與女婿閔福德(Minford)所譯。下面擬就原著中一些典型的文化預設語句,按照奈達文化的分類法,從五個方面比較分析《紅樓夢》楊譯本和霍譯本對文化預設的處理。
一、《紅樓夢》兩譯本的文化預設處理比較
(一)生態文化 生態文化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中形成與發展,包括一個民族的地理、氣候等,不同地域必然有著不同文化。原作者與其讀者享有同一個生態文化,可不言明生態文化預設信息。但因為生態文化具有的地域獨特性,處于另一個文化背景的譯文讀者可能缺失此方面的預設信息。以《紅樓夢》第18回“對立東風里”詩句為例。由于中英地理的差異,“東風”在兩國度的含義完全不同。在我國,“東風”指春夏季節從東部海面吹來的暖風;而在英國,“東風”指秋冬季節從歐洲大陸吹來的寒流。楊譯注意到中英兩國在生態文化上的差異,將其譯為“the soft east wind”。譯者顯然采取了增譯法,在“east wind”前增加了“soft”一詞,由此向讀者言明了東風的可人愜意。此處的增譯法,既能夠使中國的生態文化特色得以保留,又能讓西方讀者不產生任何誤解。霍譯也認識到“東風”在生態文化預設上的不同,但霍譯將“東風”譯為“summer breeze”,抹去了東風在中國生態文化上的獨特性。
(二)宗教文化 宗教信仰,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督教文化為西方四大文化之一,曾在中世紀時期把歐洲結成一個整體,統治整個歐洲兩千多年,形成了西方特有的宗教文化。佛教是東方特有的宗教文化。在中國,長期以來釋、道、儒三教統治著人們的精神世界,影響著人們的思想,這種影響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文學來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宗教文化必然會在文學作品中有所體現。以第57回寶玉所說“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這句話為例。楊譯把其中的“阿彌陀佛”譯為“Amida Buddha!”,霍譯為“the Lord”。“阿彌陀佛”為梵文詞匯“Amitabha”的音譯,是大乘教佛名。誦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即“念佛”行為,可以用來祈禱平安幸福或感謝神靈。楊譯為“Amida Buddha”,使用了音譯法,保留了這一佛祖稱號的原樣。霍譯的“the Lord”,意為“感謝主”,“主”為西方基督教徒所信仰的神靈,原文的東方佛教文化變成了西方基督教文化。
(三)物質文化 物質文化體現為一個民族的日用物品、生產工具、社會設施和科學技術等方面。一種文化中極為普遍的東西,不一定存在于另一種文化中,且同樣的東西在不同文化中有時會引起不同的聯想,以第16回“那薛老大也是‘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這句話為例。中國的餐具一般使用碗、筷、匙、盤,炊具多用平鍋、炒勺,平鍋具有圓底內深的特點。而西方餐具一般使用刀、叉、碟,炊具多用平底煎盤或煎鍋。“碗”、“鍋”為傳統的中國飲食器皿。楊譯采用了直譯處理策略,譯“碗”為“bowl”,譯“鍋”為“pan”。霍譯卻用碟子“dish”代替了碗“bowl”,平底煎鍋“saucepan”代替了圓底平鍋“pan”。對這樣的簡單物質文化預設,其實完全可以采用楊譯的直譯處理策略,而較難把握之處,則不妨采用變通處理策略。
(四)社會文化 一個民族的傳統習俗和生活方式,社會活動的特點和形式,對個人、社會和階層的習慣稱謂等等都屬于社會文化的范疇。社會文化的身影在文學作品中,尤其在典籍中可謂無處不在。以第3回中的“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這句話為例。漢語的“老祖宗”是對長輩或年齡最大的親屬的稱謂。中國是一個崇尚“尊老敬老”的國家,常在姓氏前加“老”字,如“老楊”、“老王”,或在親屬稱謂前加“老”字,如“老爺爺”、“老婆婆”,以傳達尊敬之意。“祖宗”為家族中的長輩,暗含著權威與威望。“老祖宗”為《紅樓夢》中的賈母,稱其為“老祖宗”不僅指賈母輩分最高,且暗指她是賈府中眾所尊崇的最高統治者。楊譯將“老祖宗”直譯為“Old Ancestress”,揭示了賈母擁有的地位與權威,反映出了此稱謂中的預設文化心理,原作的社會文化習俗得以保留。霍譯將“老祖宗”變通處理為“Grannie”,而“Grannie”在西方可以稱呼所有父母的母親輩婦女,且不夠正式,過于隨便,對原文所暗含的輩分等級禮教風俗內容傳達得顯然不夠。
(五)語言文化 漢民族獨特的社會歷史與生活經歷在文化深層層面的沉淀,形成了漢語重整合、重含蓄、重暗示的語言文化特征,這在《紅樓夢》的語言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小說中俯拾皆是的典故、詩詞、對聯、成語,頻繁運用的雙關、委婉語等修辭手段,形成了頗具特色的藝術境界。對另一文化的讀者而言,可能缺失這些語言文化預設知識。以第76回黛玉、湘云中秋賞月聯詩時的詩句“銀蟾氣吐吞”為例。楊譯為:“The Silver Toad puffs and deflates the moon.”并對“銀蟾”作了注解“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folklore,the Silver Toad swallowed then spat out the moon,making it wax and wane.”霍譯為“Damp airs the silver Toad of the moon inflate.”原句中的“銀蟾”,出自著名神話“嫦娥奔月”,指月中蟾蜍。古人把云層遮月而過的現象,解釋為月中蟾蜍在吞吐云氣。對于這句富含文化信息的用典,楊譯用首字母大寫的方法譯“銀蟾”為“the Silver Toad”,表明“銀蟾”為專稱,并在下面附加注釋解釋了其文化淵源。楊譯文字簡潔利落,加注給譯文讀者提供了理解原文所需的文化預設信息,使譯文讀者能夠對中國傳統月文化有一定了解。霍譯僅把“Toad”視作專有名詞,未給出任何背景信息,態度上顯然有些粗心草率。
三、譯者文化預設處理的影響因素分析
由上述譯例,讀者可以發現兩譯本對文化預設處理的總體傾向是:楊譯主要采用音譯、直譯、增譯和加注策略,傾向于盡可能傳達原文的文化預設信息;而霍譯主要采用變通策略,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原文的文化預設信息。可見,對于相同的文化預設,兩譯者的處理存在著顯著差異。這種差異緣于譯者所受制的因素,可分為譯者自身因素和外在因素兩方面,前者主要指向譯者文化心理,后者主要包括社會文化語境和贊助人。
(一)譯者文化心理 楊憲益生于書香門第,自小熟讀四書五經等傳統經典,無限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其夫人戴乃迭女士為英國人,6歲前一直在北京生活,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后赴牛津大學攻讀現代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并獲得榮譽學士學位,22歲隨夫再次回到中國,此后便長居中國,人生四分之三浸濡于中國文化。楊氏夫婦具有厚實的國學素養,深深認同主體文化,促使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偏向傳達原語文化特征。《紅樓夢》在二人心中又貴為傳統經典名著,享有極高的地位。對于這樣的一部文化經典,他們傾向于采用直譯、增譯、加注等策略來彌補譯文讀者文化預設信息的缺失,譯本讀起來更像一部學術著作。
這樣的文化心理定位與霍譯顯然是大相徑庭的,霍克斯更多地是把《紅樓夢》視為一部充滿魅力的流行小說。他為書中琳瑯滿目的人物、跌巖起伏的故事情節所著迷,關注的是原文的娛樂性與藝術性。他在譯本序言中所明確指出,“對于這部小說,我的看法與他人不同。對于我喜歡的原文,在翻譯時不會考慮學術問題、學究問題。我只在乎如何向讀者展示這本書……使他們能從譯文中體味我所得到的樂趣。”霍譯后四十回的譯者閔福德,在就“《紅樓夢》翻譯研討會”致劉士聰教授的信中,也說道“無論是霍克斯還是我本人在著手這件工作時,并非把它作為學術活動,而是出于對原作本身的熱愛之情”。[2]
(二)社會文化語境 翻譯的取舍和結果不僅受到個人因素的左右,而且至始至終都受到譯者所屬社會文化語境的制約,此因素影響到楊譯和霍譯對文化預設的處理態度。
自從國外的堅船利炮轟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后,國人痛心地認識到國家的荏弱。一群先進的中國人試圖在西方能夠尋找到富國強兵之路,翻譯由此肩負了沉重的歷史使命。為了更有效地學習西方,譯者們反復強調譯文要“信”于原文,即要忠實地傳達原文內容,保留原作的韻味、風姿。改革開放后,學習西方的意識更為強烈。譯事重“信”的要求延續到現在,《尤利西斯》漢譯本就是典型代表。現有的《尤利西斯》兩譯本,都盡可能地如實傳達西方文化,凡是國人可能遇到的文化預設信息缺失之處都作了加注說明。楊憲益和戴乃迭在中國從事翻譯工作,毫無疑問要受制于中國文化規范的影響。所不同的是,楊氏夫婦的工作是將中華文化典籍譯成英文,他們擔負的責任是對外宣傳中華文化。楊氏夫婦對《紅樓夢》中的文化預設信息的忠實傳達,實質上就是傳統的忠實原則在譯本中的體現。
霍克斯為地道的英國人,處在與楊氏夫婦完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在近兩三百年來,西方社會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處于世界的話語霸權地位,對其它地區實行“文化一言堂”,“歐洲中心論”的觀念由此確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西方譯者通常采用“通順”的翻譯原則,極力追求譯文透明暢達,以致看起來不像譯文,譯文仿佛譯者本人的創作。這樣的翻譯蔑視他者文化,抹去了他者文化的差異。霍克斯生于長于這樣的文化體系,自難逃其影響。霍克斯曾說過他很清楚自己的譯法造成的巨大文化損失,卻又無能為力拒絕這種譯法,這恰恰表明了西方譯者及廣大的西方漢學家面對他者文化的糾結、困惑與無助。
(三)贊助人 另一影響譯者文化預設處理的重要因素是贊助人。此處的“贊助人”,可以理解為“某種權力(這種權利可為人或某個機構),它能夠對文學的閱讀、寫作和改寫施加影響”。[3]
楊憲益夫婦翻譯《紅樓夢》時的贊助人,無疑為當時的外文出版社。1952年,年輕的楊氏夫婦開始供職于該社,它在行政上隸屬于中國出版總署。出版總署曾明確規定外文出版社的職責是從事各類外文圖書的翻譯與出版,目的在于服務于國家的對外宣傳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楊憲益與夫人接受了外文出版社委派翻譯《紅樓夢》的艱巨任務。《紅樓夢》是一部蘊含豐富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典籍,如何通過譯本來宣傳中華文化,不僅是他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時也是一項十分嚴肅的政治任務。在楊譯本的正文前,不見譯者前言,而由外文出版社的出版說明取而代之。這充分地表明了外文出版社就是楊譯本的贊助人,影響了譯者的翻譯行為。
在贊助人方面,霍譯本的情況與楊譯本完全不同。首先,由于對《紅樓夢》愛不釋手,霍克斯主動地選擇《紅樓夢》作為翻譯對象,他本人就是翻譯的贊助人。為了能夠全力以赴地投入《紅樓夢》的翻譯工作,他辭去了牛津大學的教授職務,做了全職譯者。次之,《紅樓夢》霍譯本的出版商是企鵝出版社,作為贊助人,鑒于霍克斯在英國漢學界的威望,及出于對譯本發行量的考慮,給予了譯者充分的翻譯自由權。企鵝出版社作為英國最為權威的出版社之一,它的盛名使譯作還未面世就獲得了讀者的期待與信任,所以并不束縛譯者,“他們的影響正體現在尊重權威與譯者自由”。[4]
四、結語
在傳播中國典籍方面,楊譯本和霍譯本都作出了各自的貢獻,但就文化處理方面而言,楊譯略勝一籌。在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的今天,文學作品的對外譯介并不只是簡單的通過語言轉換輸出作品的過程,而是擔負著“文化傳播者”的使命。從長遠發展來看,楊譯更益于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對外推廣中華文化,促進文化的交流與發展。然而,霍譯也好,楊譯也罷,都不過是《紅樓夢》譯介歷程上的一個片段。霍克斯自身意識到“這個譯本會被替代”,[5]楊譯也因注釋過簡有待改善,它們的存在都是為了等待新的更好的譯本的到來。
①本文采用的霍譯本為Penguin Books 1973年版。楊譯本為外文社1978年版。
[1]Nida,Eugene.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Leiden:Brill,1964.
[2]楊憲益.漏船載酒憶當年[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
[3]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張南峰.中西譯學批評[M].北京:清華大學版社,2004.
[5](美)戴維·霍克斯.翻譯家戴維·霍克斯先生的來信[A].劉士聰.紅樓譯評:《紅樓夢》翻譯研究論文集[C].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 馮喜梅〕
On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Taking Two English Versions ofHong Lou Mengas Examples
YANG Li-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angjiang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434023)
Hong Lou Meng fully display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Based on Nida's cultural categorization,the paper illustrates how translators handle the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with examples from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by Yang Xianyi and Hawkes.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former tries its best to disclose the cultural presupposition of the original while the latter erasing it.Finally,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results from 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ors'own cultural psychology,social cultural context and patrons.
cultural presupposition;literary translation;Hong Lou Meng
H315.9
A
1674-0882(2013)02-0062-04
2013-02-23
長江大學外國語學院青年教師科學研究基金
楊麗華(1982-),女,江西臨川人,博士,講師,研究方向:翻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