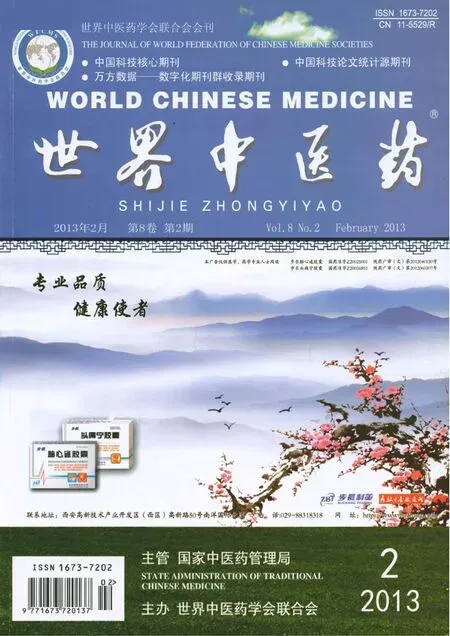中醫證候的結構化研究
孫喜靈 姜偉煒 張曉林 劉 琳 王斌勝 王云慧 劉孟安
(1 濱州醫學院(煙臺校區)中醫證候研究中心,煙臺,264005;2 煙臺市中醫醫院消化科;3 煙臺大學校醫院;4 濱州醫學院(煙臺校區)數學教研室;5 煙臺大學數學與信息工程學院;6 煙臺長恩醫院中醫科)
破解證候的動態演化規律,一直是中醫學理論研究中的關鍵科學問題之一。證候基礎研究領域的突破,既可以帶動中醫學基礎理論的創新,又可以促進臨證辨證論治水平的提高;而證候動態、多變、復雜的非線性結構,卻妨礙對其科學內涵揭示,所以破解證候高維高階的非線性結構,成了解決證候動態演化規律研究的難題。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和前期艱苦的研究準備工作,尤其是中醫學證候理論內蘊拓撲結構的發現[1],使證候動態演化規律的基礎研究顯露出突破的端倪。
1 證候動態演化規律研究面臨的難題
中醫臨床的優勢則體現在辨證論治的水平,而辨證論治的水平取決于辨證論治過程對應臨床病證的準確性。因而深入探析證候自身內在的演化規律和論治方劑藥物變化規律之間的關系,才能促進理法方藥對應臨床病證的準確性的提高。
近十幾年的研究表明,證候是一定時點與一定狀態的產物,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狀態的變化,證候有可能發生由此及彼的改變,在時與空兩個方面出現變動、演化、遷移和發展[2],表現出了證候高階、多維的非線性結構,造成證候的復雜性、多變性,使其動態演化規律的內涵難以被認識[3-4]。因此,破解證候的高階、多維的非線性結構,展現證候復雜、多變的全貌,揭示出證候動態演化規律的內涵,成為證候基礎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帶動中醫學知識創新的關鍵科學問題。
2 創新研究方法來破解證候內在結構的難題
近半個世紀來,運用多學科所提供的各種方法來研究中醫學,雖然在局部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對中醫學的發展沒有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究其深層次上的原因,在于中醫學內在蘊藏的數學機制得不到揭示[5],由此,出了現今應用復雜科學和數學方法研究中醫學的大趨勢,并且主要方向集中在中醫學的證候基礎理論研究方面。
證候理論內蘊拓撲結構數學機制的發現,揭示出每一個證候都有一個自然過程,而證候的自然過程又表現出了拓撲不變量,也就是證候自身癥狀的集合內,證候又可由不同癥狀的子集合體現出來,構成證候的主癥與次癥在證候具體存在形式的癥狀子集合中有一定規律性[6],并不是隨主觀簡單判定而定的,構成證候不同癥狀的子集合,是證候從產生、發展、變化到終結過程中癥狀出現先后規律的客觀反映。證候的拓撲不變量在疾病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五種基本存在形式[7],正好是證候內在演化規律的具體體現,是證候四個拓撲不變量第一次衍生的結果;證候的四個拓撲不變量的第二衍生出的子集合,展現出證候內在動態演化規律的全貌[1]。
基于證候的拓撲結構變化,考察證候從靜止不動狀態到演化變動狀態的全貌,可以推證證候動態演化衍生的子集合所對應的具體治法和方藥,來實現證候動態演化衍生子集合與治法和方藥精準對應,揭示出證候自身演化過程中不同子集合呈現出的論治規律,從而破解了證候研究面臨的難題,即把高階、多維的非線性結構的證候經過拓撲結構變化可以降階為一階、一維的線性結構。由此,通過對證候拓撲結構數學內涵機制的揭示,使復雜、模糊、多變的證候,變的簡單、直觀、定量,因而,可以使對證候的把握和認識,變的完整、可靠、精準了。這一直都我們在追求的目標。
以脾氣虛證候為例,脾氣虛證候的拓撲不變量經過變化,衍生出了608個不同的子集合,展現出了脾氣虛證候動態演化的全貌[1];即高階、多維的非線性結構的脾氣虛證候,經過拓撲不變量的變化,降階為608個一階、一維的線性結構。
3 揭示證候結構與理法方藥精準對應的規律
理法方藥對應的精準程度,直接決定著辨證論治過程對應臨床病證的準確性,反映著辨證論治水平的高低。而要對證候進行準確的把握和認識,就離不開的證候自身內在演化規律的闡釋和揭示。證候的自然過程中呈現出了拓撲不變量,證候的構成癥狀和體征的拓撲不變量有兩次衍生,從其子集合對應的治法和方藥變化中,可以看到證候自身動態演化的全貌和論治規律的展現。以脾氣虛證候為例,對脾氣虛證候論治過程中,隨著脾氣虛證候內在演化呈現出的608種不同的存在形式而變化的,對應著608個不同的治法和組方。
再以《中醫診斷學》中74個單一證候為例,基于證候理論內蘊的拓撲結構的理論,提出每一個證候的拓撲不變量,拓撲不變量經過兩次衍生,74個單一證候共可衍生42 萬多個子集合,展現出了每一個單一證候動態演化過程中的全貌。分析證候拓撲結構變化衍生出來全部子集合,可以闡明單一證候在動態演化過程中其子集合主癥和次癥的變化規律與對應治法和方藥的轉化規律,揭示出證候動態演化衍生的系列子集合與治法和方藥精準對應的科學內涵。
4 運用文獻和臨床數據實現中醫知識的創新
沒有知識創新的學科,學科的本身是不會出現發展的。中醫學的知識只有不斷出現的創新,才會促進中醫學自身的發展。基于證候理論內蘊拓撲結構的理論方法,運用證候結構破解的數據,可以進行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并帶動養生保健與預防知識的創新。
以脾氣虛證候為例,盡管《方劑學》中與脾氣虛證候相關聯的方劑有四君子湯、異功散、六君子湯、香砂六君子湯、健脾丸、參苓白術散、補中益氣湯、枳術丸、小建中湯、五苓散、二陳湯等11 首,且是最多的一類,但這些經典名方還遠遠不足以與脾氣虛證候的608種具體的存在形式相對應;反過來,又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正由于《方劑學》的方劑不足以與證候的具體存在形式相對應,這恰好給治則治法和方劑的創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和豐富的數據。
《中醫診斷學》中74個單一證候共可衍生42 萬多個子集合,對應著42 萬多種不同的治則治法和方藥,分析這42 萬多個單一證候動態演化衍生的子集合精準對應的方藥,再與方劑文獻梳理研究的數據相對應,篩選出方劑文獻數據中沒有記載的,可以實現方劑在知識上的創新。
理法方藥知識在理論上的創新,要為臨床患者服務所使用,還要經過臨床案例數據的篩選與驗證,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創新。通過大樣本的臨床案例數據,基于完整四診資料、全面辨證分析、準確治則治法、精準方藥對應的詳盡分析,再運用證候結構化的理論數據,通過古代名醫醫案和方劑證候分析的文獻數據,可以實現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
總之,基于證候理論內蘊拓撲結構的理論方法,進行證候動態演化規律的關鍵科學問題的系統研究,可以破解證候的高階多維的非線性結構,把復雜多變的證候經過拓撲結構變化降階降維成為一階一維的線性結構,實現對證候動態演化規律全貌的認識,揭示證候動態演化子集合的衍生規律與對應治則治法和方藥的變化規律;在證候結構化理論分析數據的基礎上,運用古代名醫醫案和方劑證候分析的文獻數據,通過臨床案例數據,可以實現理法方藥知識的創新,帶動養生保健和預防知識的創新,從而促進臨床辨證論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促進中醫學理論的發展。
[1]孫喜靈,張曉林,趙巖,等.中醫學證候理論內蘊的拓撲結構研究[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10,34(5):383-388.
[2]郭蕾,王永炎,張志斌,等.證候動態時空特征的復雜性及相應的研究思路[J].中醫研究,2006,19(3):1-3.
[3]郭蕾,張啟明,王永炎,等.證候規范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探討[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6,3(26):258-261.
[4]王永炎,張啟明,張志斌.證候要素及其靶位的提取[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30(1):6-7.
[5]高懷林,吳以嶺,賈振華,等.中醫證候量化診斷研究概況[J].江蘇中醫藥,2007,39(9):78-80.
[6]張曉林,孫喜靈.試論證的五種基本存在形式與不同治法方藥[J].中醫雜志,2005,46(2):91-92.
[7]孫喜靈,趙巖,張曉林,等.證候癥狀構成子集合演變規律的理論推證[J].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2008,32(4):279-281.
[8]趙巖,張曉林,孫喜靈,等.證候自然過程中自身內在的演變規律[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8,14(4):248-250.
[9]孫喜靈,劉琳,趙巖,等.試論證候有限空間模型中客觀存在的復雜證候群[J].中醫雜志,2008,49(7):581-583.
[10]張曉林,趙巖,孫喜靈,等.1589例冠心病心肌缺血患者復雜證候群及其分布規律.中醫雜志,2011,52(8):668-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