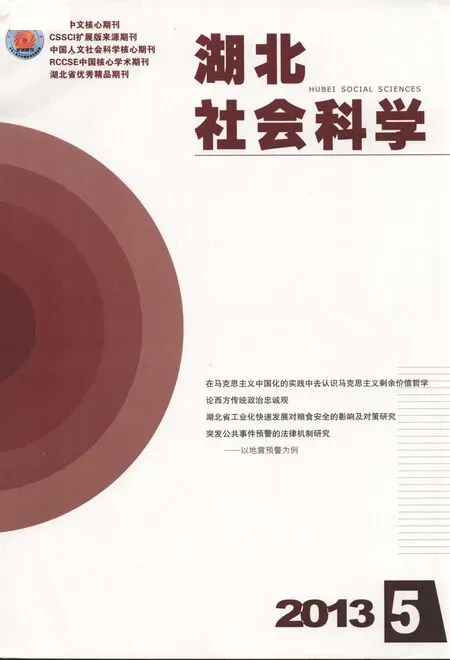載澤與清末立憲
鄧春豐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上海 200234)
以往學界對載澤的研究,多以《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為中心,對載澤在清末立憲時期的整體活動缺乏關注,其所著《考察政治日記》亦被人忽視。為彌補這一研究缺陷,本文主要對載澤在清末立憲時期的思想與活動做一鉤沉和評述。
一
面對日俄戰爭后日趨嚴重的統治危機,1905年7月16日,清廷決定派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1](p1)載澤(1868—1930),清王室宗公,初封“鎮國將軍”,后晉“輔國公”,為康熙第十五子允禑六世孫。他“留心時事,素號開通”,[2](p92)是官僚立憲派主要代表人之一,這是其能入選考政大臣的主要原因所在。
諭旨頒布后,載澤等考政大臣上奏表示朝廷此舉可“收富國強兵之效,大局幸甚,天下幸甚。”[1](p2)革命派認為“五大臣之出洋也,將變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臉,以蠱惑士女,因以食人者也。”[3]1905年9月24日,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帶領參贊、隨員,在北京正陽門車站“巳刻登車,正擬開行,陡聞轟震之聲甚為劇烈,并肩煙氣彌漫,窗欞皆碎。”[1](p3)他們遭到革命黨人吳樾的襲擊,載澤額角受微傷,紹英耳后發際及臂上受傷略重,隨員仆從亦有受傷。載澤能躲過此劫實屬萬幸,“其時,適值日本國內團公使之代理公使館二等書記官鄭永邦送行,澤公起身出外答送,遂免于危。”[4]清廷朝野震驚。慈禧“慨然于辦事之難,凄然淚下”,[5](p314)并“責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工巡局、督辦鐵路大臣等,確切查拿,徹底根究,從重懲辦,以儆兇頑。”[6](p2166)
對于革命黨人的此次“反滿”恐怖活動,輿論嘩然。《大公報》認為“我政府即迎其機而速行改革,以絕彼黨之望,宣布立憲。”[7]呼吁清政府“當此之際,更宜考求各國政府,實行變法立憲,不可為之阻止。”[8]《申報》指出“五大臣車站遇險,不足為新政之阻力,而反促成立憲之基礎。”[9]對清廷而言,“此后改革政體,實行立憲,其時期當必不遠。”[2]經此一劫,社會上要求清廷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呼聲反而愈發高漲。
最終,清廷派李盛鐸、尚其亨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前往各國考察政治。載澤、尚其亨、李盛鐸一行于1905年12月11日離京,1906年1月14日到上海,啟程前往日、英、法、比四國考察。他們在法國52天、英國45天、日本29天、比利時16天、美國游歷15天,考察完畢后,載澤、尚其亨于1906年7月23日回到北京。經過此次考察,他們認識到專制封閉是中國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國要富強,必須學習各國的先進經驗。載澤等派人將在四國考察情況譯纂成書,計67種146冊。這些書籍和資料使清廷最高統治者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更加了解,也增強了他們進行政治改革的決心。
二
通過出洋考察政治,載澤對資本主義文明和世界局勢的認識頗有見地。他分析中西治道之不同,“在我曰用中,在彼曰用極。”[10](p564)歐美列邦之所以強大,在于“往往萃十數國學者之研,窮數十百年之推嬗,以發明一名一物,成立一政一藝,不至其極不止。”[10](p564)中國的中庸之道在治國方面存在很多弊端,但能使人皆修勉于道德,舉國上下,同力一心。若我們能積極學習和利用歐美列邦“求乎至極”的治國精神,中國一定會經過變法維新而強大。為此他提出:“至于國勢民風,彼我之所同異,禮俗政教,有可以相襲、不相襲之故,可得而規度也。”[10](p564)鑒于中日兩國自近代以來的巨大差距,載澤指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富國強兵的效果,其根本在于教育普及。更重要的是日本不盲目效仿歐洲,而是注重和本國國情相結合,因此最終取得“以三島之地,經營二三十年,遂至抗衡列強,實亦未可輕量”[1](p6)之成效。作為由儒家傳統制度培養出來的專制王朝的大臣,能做出如此評價,其眼量已卓然高出頑固迂腐的守舊派。但他又提出:“夫法制、政教、兵農、商工,當因時損益,舍短取長,此可得而變異者也;倫常道德,當修我所固有,不可得而變異者也。”[10](p566)即使是作為當時比較激進的官僚立憲派,載澤對政治制度的改革依然保守,這一思想上的局限性直接影響到以后清廷實行政治改革的深度。
回國后,載澤被慈禧和光緒皇帝召見兩次,他和其他考政大臣“皆痛陳中國不立憲之害,及立憲后之利。”[11](p14)實行立憲不僅是政體的改變,更是國體和整個專制制度的改變。這將嚴重損害地方督撫們的既得利益,他們紛紛上奏表示反對,認為立憲“施之我國,則有百害而無一利。”[1](p108)載澤上《奏請宣布立憲密折》進行反駁,他指出立憲“利于國、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12](p27)“蓋憲法既立,在外各督撫,在內諸大臣,其權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優,于是設為疑似之詞,故作異同之論,以阻撓于無形,彼其心,非有所愛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權而已,護一己之私利而已。”[12](p27)此言倒不失為統治階級內部的有識之論。既然是政治體制改革,內外諸臣應當在權與利兩個方面向國家和人民做出相應的讓步,即使是最高統治者,也應如此。否則一切都將成為空談。輿論界對此反響巨大。有評論指出:“吾國之所得由專制而進于立憲,實以此折為之樞紐。”[13](p7)《北京日報》專門發表評論:“余深服澤公高見遠識,洞見隱微,且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近支王公,乃有此人,大清國其有賴矣。”[10]針對一些滿洲貴族反對立憲的謬論,載澤批判道:“謂滿人之言立憲不利者,實專為其一身利祿起見,決非忠于謀國。使其行排漢之政策,必至自取覆亡。”[11](p14)
憲政改革后君權是否會受到影響,是君主及載澤等考政大臣關注的焦點所在。為保證立憲工作的順利進行,載澤等官僚立憲派主張清廷可效仿日本,實行君主立憲。因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雖采用立憲制度,君主主權,初無所損。凡統治一國之權,皆隸屬于皇位。”[10](p575)就目前時勢而言,實行君主立憲有三大益處:“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漸輕,一曰內亂可弭。”[12](p28)后世學者多以載澤此言作為依據,批判清末立憲只是一場騙局。筆者認為僅以此點就全盤否定清末立憲有失偏頗,因為任何改革者搞改革都是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清朝統治者所進行的憲政改革亦然如此。綜觀載澤的立憲思想,維護君權是其核心,其所論并不完全正確,如說立憲后君權不受損害并不符合實際,所言立憲的“三大利”也未必會有那么大的效力。但其立論均從國家前途和大局出發,亦無狹隘的民族偏見,敢于同守舊的頑固勢力作斗爭,身為滿洲的宗室王公,其精神和膽識值得稱贊。
面對歐美諸邦及日俄諸國覬覦我國的險惡國際環境,對清廷而言,實行立憲已是刻不容緩之事。載澤希望統治者能堅定立憲的決心,為穩妥起見,他又提出:“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于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12](p29)戴鴻慈等考政大臣也建議清政府以十五年或二十年為實行立憲之期。地方督撫袁世凱、張之洞、周馥三人也主張十二年以后再正式實行立憲。1906年9月1日,光緒帝頒布《宣示預備立憲先行厘定官制諭》,正式標志著清末預備立憲的開始。清廷采納了載澤等人的建議,于1908年宣布經過9年預備后正式實行君主立憲政體。
最終,清廷選擇實行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政體的緣由眾多,既有官僚立憲派的積極爭取,更有日本出于政治滲透的考慮,在中國立憲問題上采取積極措施所施加的影響,更有滿清王朝出于維護自身統治的諸多因素在內,但載澤等官僚立憲派所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計自四大臣歸國以迄宣布立憲,才足一月,其間大臣阻撓,百僚抗議,立憲之局,幾為所動。茍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擊俗論,則吾國之得由專制而進于立憲與否,未可知也。故說者謂此次宣布立憲,當以澤公等為首功”。[11](p17)
三
在中國召開國會,制定憲法,實行君主立憲是朝野立憲派的愿望。面對不可遏抑的國會請愿運動,清廷于1908年8月27日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其中“君上大權”14條,“附臣民權利義務”9條,要點如下:
君上大權:[1](p58、59)
1.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
2.君上神圣尊嚴,不可侵犯。
3.欽定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
4.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會之權。
5.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
6.統帥陸海軍及編定軍制之權。
7.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使臣與認受使臣之權。
8.宣告戒嚴之權。
9.爵賞及恩赦之權。
10.總攬司法權。
11.發命令及使發命令之權。
12.在議院閉會時,遇有緊急之事,得發代法律之詔令,必得以詔令籌措必需之財用。
13.皇室經費,須經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之,議院不得置議。
14.皇室大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議定,議院不得干預。
《欽定憲法大綱》基本上以當時的日本憲法為藍本,[11](p11)而且在有關君主權力方面比后者更加保守,增加了議會閉會期間君主籌措經費的權力,對日本憲法中規定的臣民的遷徙、宗教信仰、通信、請愿等自由,均未提及。因此憲法頒布之后,遭到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和立憲派的猛烈抨擊,但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它的歷史進步性。憲法前言講到:“君主立憲政體,君上有統治國家之大權,凡立法、行政、司法,皆歸總攬,而以議院協贊立法,以政府輔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1](p57)這在保證君權的前提下,也體現了資本主義國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組織原則。“它所起的承先啟后的歷史地位,和積極的豐富立法經驗,對以后的中華民國的法制建設具有指導的意義。”[16](p221)載澤向清廷所推薦的日本式二元君主制,雖說是憲政中最為保守的一種,但較之完全的絕對的君主制,它又是一種歷史的進步。[17]這樣一部進步性憲法的問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載澤等考政大臣所宣傳的西方憲法思想的影響。清廷在整個預備立憲過程中,始終無法擺脫立憲與君權的矛盾纏繞,既想通過立憲以圖自救,又希望君上大權不受損傷,而其致命傷也恰在這里。清統治者頒布這一備受爭議的憲法,在憲政改革的道路上又往前邁了一步,同時也使自己陷入更為艱難的處境之中。
四
清末“立憲之根基,莫要于地方自治。”[9]五大臣在英考察時,有英議員提出對中國危害至深的鴉片問題,并表示:“若貴國果能禁種,英議院深表同情,亦議禁印度煙出口。”[10](p626)載澤認為鴉片危害中國甚于洪水猛獸,有能絕禁之者,功不在禹、周之下。今英議員有此態度,可見公道不泯,中國亦可借此逐漸收回中國關稅之主權。要解決好這一問題,他提出:“則非竭力創立地方自治不可。且地方自治成立,則立憲之根本已固,可漸圖收回既失之國權,內外并營,則鴉片之害,二十年內可望盡絕。”[10](p626)載澤對滿洲政府的忠心可鑒,對于中國未來的走向更是時刻掛記于心。
在其《考察政治日記》中,載澤詳細記載了英、法、比利時等國地方自治的情況。他對英國的地方自治深為贊賞,認為“至其一國精神所在,雖在海軍之強盛,商業之經營,而其特色實在地方自治之完密。”[10](p630)在他看來,“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條規嚴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財,供地方之用,故征斂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層折曲累,以隸于政府,得稽其賢否而獎督之,計其費用而補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孔之遺制,實為內政之本源。”[10](p630)通過載澤等出洋考政大臣的宣傳,再加清政府當時已經左支右絀的財政狀況,地方自治用地方之款辦地方之事的特征深得其心,清政府決定以地方自治作為立憲的基礎和富強的根本,地方自治在全國迅速開展起來。雖然這場運動最終并未完全達到改良地方政治之目的,清政府希望借此緩解統治危機的目的也未實現,但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
在清末立憲過程中,載澤是皇族中比較堅定的官僚立憲派。1911年5月8日責任內閣成立,他擔任度支大臣。皇族內閣成立后,清廷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載澤等上奏表示:“臣等均屬懿親,未便久充國務要職。合無仰懇天恩,俯鑒下忱,準將臣等即日開去國務大臣,另簡賢能分任要職。”[1](p600)他們奏請皇帝組織完全內閣,以確保立憲的順利實行。然而,革命的急風暴雨已經到來,載澤等少數官員的作為對于清廷而言亦是杯水車薪,清政府未能完成自身的緩慢演變,而被革命的滾滾洪流所吞沒。
在清末立憲這場改革運動中,作為考政大臣之一的載澤,其思想與實踐值得我們關注。君主立憲相對于封建專制制度而言,具有毋庸置疑的優越性和進步性。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遷推動著社會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面前,作為滿洲王朝的宗室王公,載澤“有心護國,無力回天”,他所期盼的“神皋區夏,振奮之機,會不在遠。”[10](p564)、“庶國勢進,聞實昭于天壤,傳永永而無窮也。”[10](p567)的目標終究未能實現。
[1]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9.
[2]鴿子.隱藏的宮廷檔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3]思黃.怪哉上海各學堂各報館之慰問出洋五大臣[N].民報第1號.
[4]澤公幸免炸彈之由[N].申報,1905-10-01.
[5]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2008.
[6]論捕謀傷出洋五大臣要犯[J].光緒政要,卷三十一.
[7]論出洋五大臣臨行遇險事[N].大公報,1905-09-26.
[8]電致駐日欽使[N].大公報,1905-10-14.
[9]論紳董對于地方自治之責任[N].申報,1905-09-30.
[10]載澤.考察政治日記[M].長沙:岳麓書社,2008.
[1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折[A].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鎮國公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折[J].東方雜志第四年臨時增刊.
[14]論立憲制度利于政府而不利地方官[N].申報,1906-09-09.
[15]附憲法大綱暨議院法選舉法要領清單[A].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C].北京:中華書局,1979.
[16]張晉藩.法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17]羅華慶.載澤奏聞立憲“三利”平議[J].近代史研究,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