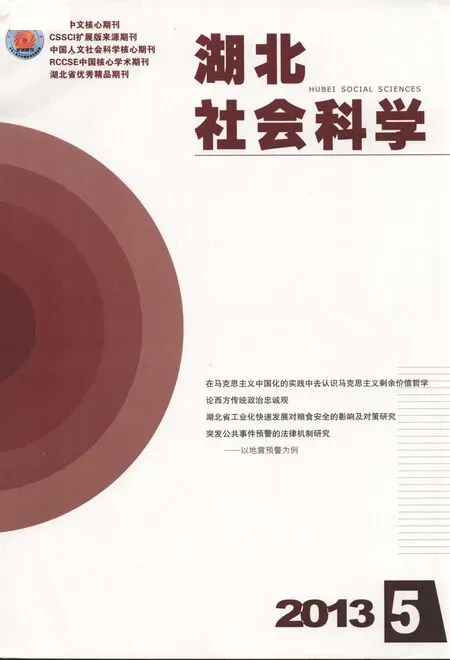方言自感詞“V人”的“表里值”及其情感偏向
王 耿
(華中師范大學 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9)
一、引言
自感詞即表達自我主觀感受的詞語,自感詞“V人”是這樣一些詞:煩人、怕人、嫌人、膩人、瘆人、氣人、冰人、熱人、毛人等等,這類詞有共同的類詞綴“人”,而且能產性強,形成了跨方言的“詞族”。關于此族詞的研究始于胡雙寶,他對文水話中的“V人”結構進行了總結,并描寫了能進入此格式的“V”的聲調分布情況。[1](p275)劉海章描寫了荊門方言中的此類詞。[2](p97)劉瑞明對 1984 年到 1999 年這十余年的“V 人”研究進行了綜述。[3](p59-62)此后,“V人”研究有了新的發展:此前大多數學者都認為“V人”族詞是動詞,而羅昕如通過“V人”的句法分布將其定性為形容詞。[4](p105-107)隨后,呂建國又區分了慈利話中名詞性的“A人子”和形容詞性的“V人子”。[5](p44-49)總體看來,關于“V人”的研究越來越充實,積累了大量的材料,但同時也遺留了一些問題。本文就以前人研究為基礎,通過跨方言的比對,揭示此族詞的形式、語義特征和分類情況,并對其情感偏向的原因做一番探究。
二、“V人”族詞的地域分布及形式特征
1.“V人”族詞的地域分布。
李榮主編 《漢語方言大辭典》中有26個方言點記錄了“V人”族詞,相關研究資料也涉及了8個方言點,涵蓋西南官話、中原官話、江淮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北方官話以及吳語、湘語、贛語、粵語、閩語、客家話等諸多方言區。這些資料中記載的“V人”族詞共計564個,當然,由于此結構能產性很強,諸方言中到底有多少個“V人”尚無法窮盡統計。
2.“V人”族詞的形式特征。
(1)類詞綴“人”的語音和結構特征。

從結構上看,有的方言中“V人”后還附加了一個成分,形成“V人X”結構,比如荊門、慈利方言附加“子”;商州方言附加“哩”;哈爾濱方言中有的“V人”后附加“兒”。本文認為這個附加成分有兩種性質:一是詞法成分,哈爾濱屬于兒化韻顯著的北方方言區,因此“V人”后有時附加“兒”,比如“打人兒(令人折服)、憐人兒、愛人兒”;荊門屬于“鄂顫區”,“子”是當地方言詞尾特有的顫音,念“[r]”。二是句法成分,比如“哩”是中原官話中一個特有的句尾語氣詞,而“V人”作為一個形容詞經常出現在句末,所以由于高頻因素的制約,“V人”和“哩”便被人們整體認知了。張成材指出商州方言中的“V人哩”是“造句現象”,同時也認為“V人哩”是一個“凝固結構”。[6](p84)
(2)變量“V”的音節特征及“本字”問題。
能進入“V”的大都是單音節詞,但不乏少量的雙音節詞,比如牟平話中的“絮煩人”,建甌話中的“纏聯人”,商州話中的“窩蜷人哩、森煞人哩”、慈利話中的“厭臺人子、膩刮人子、肉麻人子、挖苦人子、折麻人子”,保康話中的“不當人子”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V人”還存在著“本字”問題,即許多“V”沒有相應的書寫形式。漢字是意音文字,形、音、意之間本應有一定聯系,但許多“V”都只有讀音而沒有對應的本字,還有一些“V”是用同音字代替。胡雙寶的《文水話的自感動詞結構“V+人”》中就有12個“V”無法確定本字。有些學者也在做考證本字的工作,潘渭水編纂的《建甌方言詞典》中就根據古代字書探尋了本字,并且反映在詞條的釋義中,比如,痏人:使人發癢。痏,集韻宥韻尤救切:“說文顫也”;燹人:使人感到炙熱。集韻文韻敷文切:“火貌”。但是,由于古今音系的變遷,考本字工作十分艱難,所以大多數方言詞典對于部分“V人”只給出了讀音和意義。這雖然不利于方言詞典編纂以及跨方言交流,但由于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因此這些只有讀音的“V人”在各個方言區或方言點內部暢通無阻。
三、“V人”的語義分類及語用價值
1.“V 人”的語義分類。
方言中存在數量眾多的“V人”,因此變量“V”也是千姿百態,能進入“V”的有動詞性、形容詞性、名詞性語素。但是由于受到“V人”的管控,變量“V”有形容詞化的傾向。然而單看詞性無法揭示出“V人”的豐富內涵,所以我們從“V”的語義入手進行分析。
心理學認為,人類的心理、感覺、情緒等活動過程遵循兩個步驟:一是外在環境(刺激物)通過各種方式對人產生刺激,二是引起機體反應。這一過程也可以視為一個事件,用認知圖式表示如下:
刺激物→刺激方式→感受主體→刺激結果
自感詞“V人”中變量“V”的語義特征也可根據以上兩個步驟區分為三個大類,一是刺激方式類;二是刺激結果類;三是刺激物類。其中第一大類和第二大類的內部又可以區分出一些小類,我們來一一檢視。
I.刺激方式類。刺激方式必然跟動作有關,所以進入刺激方式“V”的一般都是動詞性語素。感覺是抽象的,不可摹狀,所以描寫感覺的詞語很有限,因此直接使刺激方式(動詞)進入變量“V”,通過“轉喻”來描摹主觀感受。人類的大腦里有一套轉喻認知機制,比如可以用“打二傳手”來代替“打排球”,同理,“刺激方式+人”在人腦中通過轉喻機制的運算,也可用來表達刺激的結果,比如“烤人”中的“烤”是一種刺激方式,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烤火”,從而產生一種炙熱的感覺。這一類詞語內部又可根據感覺主體“人”與刺激方式的主被動關系分為兩個小類:
a.被動類,指外界環境通過各種方式將刺激施加于人,這一過程中人是被動接受刺激的,比如:扎人、咬人南昌,蚊蟲叮咬引起痛癢的感覺、曬人、撩人建甌,招惹人、炙人、纏人建甌,小孩糾纏使人煩;襄陽,酒勁難退的感覺、跳人建甌,人被震得上下抖動的感覺等。
b.主動類,指人類主動發出某種動作,并受這種動作影響而產生某種感覺,這一過程中人既是刺激的發出者,也是刺激的感受者,比如:寫人、爬人、走人、挑人、耕人、搬人、找人、洗人等。據目前研究資料來看,這一類只分布于荊門、宜昌、襄陽等少數幾個方言點。由于刺激的發出與感受共用一個主體,所以這一感覺過程不如被動類那么典型,因此許多人看到這一類詞時并不能馬上獲知其意義,理解起來要結合語境,比如宜昌方言:
(1)書到底放哪兒去噠,好找人。(“找人”指尋物艱難而使人產生厭煩感)
(2)這畝田太硬噠,好耕人。(“耕人”指地難耕而使人產生疲憊感)
再如荊門方言:
(3)這座山太陡噠,真爬人子!(“爬人”指山勢陡峭而使人產生疲憊感)
(4)擔子太重噠,真挑人子!(“挑人”指擔子重而使人產生疲憊感)
“走人”、“洗人”、“搬人”、“剁人”等詞語的意思都可以類推理解。
Ⅱ.刺激結果類。刺激結果指人接受刺激后所引起的反應。對反應結果的描摹必然需要形容詞,因此進入刺激結果“V”的大多是形容詞性語素。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體接受刺激以后會產生感覺、知覺、情緒、情感等生理、心理反應,其中與“V人”族詞相關的有兩類,即“感覺”和“情緒”。所以刺激結果類又可分為情緒和感覺兩個小類。
c.情緒類。情緒是指人對外界刺激所產生的心理反應,以及附帶的生理反應,如喜、怒、哀、樂。在語義上凸顯“情緒”的“V人”如:養人忻州,討人喜歡、毛人武漢,令人生氣、愛人、恨人、愁人、急人、氣人、嚇人等。
d.感覺類。感覺是事物直接作用于感覺器官時,對事物個別屬性的反映。心理學對感覺的分類有幾十種之多,本文采取一般的分類方式,將感覺劃分為膚覺、味覺、嗅覺、聽覺、視覺、機體覺和平衡覺。其中膚覺、味覺、嗅覺、聽覺、視覺比較好理解,我們來看看機體覺和平衡覺。機體覺指機體內部器官受到刺激時產生的感覺,引起機體覺的適宜刺激是機體內部器官的活動和變化,接受機體覺刺激的感受器分布于人體各臟器的內壁,此類詞語如:脹人、膨人、撐人、憋人、醸人貴陽,油膩感等;平衡覺是反映頭部位置和身體平衡狀態的感覺,引起平衡覺的適宜刺激是身體運動時速度和方向的變化,以及旋轉、震顫等,比如我們會產生眩暈、惡心等感覺,此類詞語如:暈人、顛人。
Ⅲ.刺激物類。由于人類聯想和轉喻機制的作用,極少數的“刺激物”直接進入模槽,與“人”意合形成“N人”格式。這類格式中變量“N”所凸顯的語義是引起刺激的“事物”。雖然“N”和“人”沒有直接的語義關系,但是依然可以有自感義的解讀。這一類我們記為e類,如:藥人南通,有毒,煙人萍鄉,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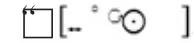
2.“V 人”的語用價值。
“V人”豐厚的語義內涵以及簡潔的結構形式賦予此族詞語旺盛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不僅表現在其廣泛的地域分布上,還反映在其龐大的數量上,更凸現在其強大的能產性上。由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有情感表達的需要,“V人”族詞語也跨越了方言的界限,在現代社會的言語交際中不斷地被新造出來,比如:
(1)問個很囧人的問題,18:00點是下午還是晚上啊?
(2)電視劇《桃花小妹》里的汪東城很電人。
(3)這種衣服好雷人。
(4)那游戲不知是哪個缺心眼的人想出來的,真糗人。
(5)好搞人!南非乘客誤按彈射按鈕彈出機艙數百米。
(6)這本書,頁面上沒有顯示缺貨,下單子時,系統才提示缺貨,很閃人啊!
以上語例都是通過百度搜索而來,其中“囧人、電人、雷人、閃人、糗人、搞人”這些流行語都用來抒發各種主觀感受。比如“囧人”表達了一種窘迫尷尬的感覺;“雷人、閃人”表達了一種出人意料、令人震驚的感覺;“電人”表達了一種深受吸引的感覺;“糗人”借用臺灣的詞匯,表達一種出丑時尷尬的感覺;“搞人”表達了一種被作弄時好笑的感覺。可以想見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個性的不斷解放,人們需要更多的表達自我感受,因此可以大膽預測,“V人”族新詞將越來越多的涌現出來。
四、“V人”族詞的情感偏向及成因
1.“V 人”族詞的情感偏向。
人類表達自我主觀感受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語音語調、特定句式,甚至音樂、美術,但最基本的還是描寫人類心理的諸多詞匯。學界一直很關注心理動詞、心理形容詞的研究。張積家、陸愛桃回顧了以往心理動詞的研究,將漢語心理動詞分為“認知”和“情意”兩類。其中“認知”對應于“經驗過程”,包含“感到、擔心、懷疑、記得、知道”等詞語;“情意”類包含“喜歡、熱愛、感動、愛、笑、激動”等詞語。[7]本文所討論的“V人”族詞語從語義上來看,表示的正是一種“情意狀態”。張、陸的文章又指出,表“認知”的心理動詞既不積極、肯定,又不消極、否定,但情意心理動詞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大類;左衍濤、王登峰對漢語情緒詞的研究表明,情緒有正、負兩個單極維度。[8](p56)那么,表情意狀態的“V 人”族詞語是否也存在著積極和消極的對立呢?研究“V人”的方言文章都很關注其感情色彩,有兩派觀點:一派認為各自方言中只有表示消極、負面意義的“V人”。還有一派認為所研究方言中還是存在少量含積極意義的“V人”。普通話中含積極意義的“V人”有:誘人、愛人、迷人、魅人、宜人、喜人、逗人等,它們在普通話“V人”族詞中所占比例為25%,比方言中積極“V人”所占比例稍大,但依然處于弱勢地位。
2.情感偏向的成因。
方言和普通話中的“V人”在感情色彩上呈現一個共性:消極意義的“V人”在此族詞中處于極度優勢地位。為什么會呈現這樣一個特點呢?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劉瑞明試圖從語言內部解釋這一問題,他認為“V人”負載的消極意義與處置式在明清時代的發展有關,而處置式一般含有消極意義。他的證據是平涼話中“把人V人的”句式可以同“V人”相互轉換。[3](p61)對于少量積極義的“V人”,劉文認為它們是從一般使動式演變而來。本文認為僅憑一處方言中的“把人V人的”句式不足以證明消極“V人”的優勢地位,要解釋消極和積極的不對稱,還得從語言外部尋找答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通過西班牙語、英語、墨西哥語等有關情感詞語的跨年齡層比較,認為情感詞語呈現出一種積極和消極的不對稱:表達消極情感的詞語所占比例(50%)遠大于表達積極(30%)或中性情感(20%)的詞語。他們對此提出了一個“信息反應(affect-as-information)”理論來解釋上述現象,這個理論認為消極情感反映了環境中的不安因素,往往伴隨著詳盡和系統的認知過程;積極情感反映了環境中安全祥和因素,伴隨著整體性的認知過程。另外,該理論認為調和、處理復雜情感的能力一直在發展且貫穿人的一生,因此消極情感詞項將在情感詞庫中占有主導地位。從年齡段來看,無論是在青年人還是老年人的詞庫中,消極詞項所占比例都是巨大的,且保持不變。[9](p266-284)這種傾向性通過觀察兒童也可得出。紐約州立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費雪在《身體覺察(body consciousness)》一書中也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常用的身體取向之字眼,多半是負面的,像是頭痛、緊張、害怕、生氣等,比方人們常把“我今天感到頭痛”“我怕嘛”或“我真的很生氣”這些說法掛在嘴邊,卻鮮少表達好的、正面的、愉快的跟身體有關的字眼。我們小時候開始學習與身體有關的社交行為時,多半是從負面的機會教育著手。因為只有在我們生病時,才會被大人細心耐心的詢問身體感受,比如“跟媽媽說,你哪里不舒服”、“肚子左邊痛還是右邊痛?”大人往往會循循善誘小孩將身體的不舒服講得精準一點。當小孩感覺愉悅、興奮、舒暢時,卻很少被大人要求具體形容生理的感覺。于是,久而久之,小孩的有關感受表達的負向詞匯就會慢慢積累,越來越多。
國外研究給予我們啟示,“V人”的不對稱性似乎印證了人類的情感共性。無論方言還是通語,消極意義的“V人”處于優勢地位可能是人類的心理基礎使然,人類對消極和積極情緒處理機制的不同最終造成了消極“V人”越積越多。那么,為什么普通話及某些方言中還存有少量積極義的“V人”呢?它們從何而來?很多語言事實證明,共時語言的面貌是各種規律博弈的結果,除了上述人類的情感共性在起作用外,人類的類推機制也在制約著詞匯的產生,所以作為一個表達情感的結構槽,“V人”偶爾接納幾個積極詞匯并不足為怪。
五、結語
從語表形式來看,“V人”中“人”的輕化或變調應是一個普遍規律;“V人”結構簡潔,能進入“V”的大多是單音節詞,但也有少量的雙音節詞;方言中有一些“V”只有讀音沒有書寫形式,需要語源學的進一步考證。從語里意義來看,“V人”語義內涵豐富,可以結合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并根據“V”的語義特征將“V人”分為三大類五小類。這一分類具有很強的周遍性和一定的預測性。從語用價值來看,“V人”豐厚的語義內涵以及簡潔的結構形式賦予此族詞語旺盛的生命力,使之在詞匯系統中大量繁殖。由于“V人”的能產性強,許多新詞在現代社會中被臨時組造出來,并在日常交際中發揮著巨大作用。隨著社會的進步及個性的不斷解放,人們需要更多的表達自我感受,因此可以大膽預測,“V人”族新詞將越來越多的涌現出來。
絕大多數“V人”的情感色彩偏向消極,其成因在于人類有特別關注負面情緒的心理共性,因此人類心理詞匯中表達消極情感的占絕大多數,“V人”也不例外。
[1]胡雙寶.文水話的自感動詞結構“V+人”[J].中國語文,1984,(4).
[2]劉海章.湖北荊門話中的“V人子”[J].語言研究,1989,(1).
[3]劉瑞明.方言自感動詞V人式綜述[J].漢字文化,1999,(3).
[4]羅昕如.湘語中的“V人”類自感詞[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5).
[5]呂建國.慈利方言“A人子”式形容詞和名詞[J].漢語學報,2008,(3).
[6]張成材.商州方言里的“形+人+哩”結構[J].語言科學,2003,(1).
[7]張積家,陸愛桃.漢語心理動詞的組織分類研究[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1).
[8]左衍濤,王登峰.漢語情緒詞自評維度[J].心理學動態,1997,(2).
[9]Robert W.Schrauf and Julia Sanchez.The Preponderance of Negative Emotion Words in the Emotion Lexicon:A Cross-generational and Cross-linguistic Study[J].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Vol.25,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