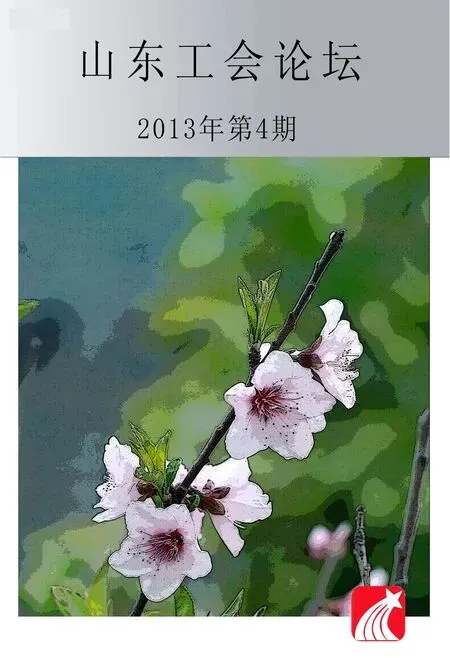論反壟斷法中寬恕制與私人執行的相關性
邵江禾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100088)
【法學新論】
論反壟斷法中寬恕制與私人執行的相關性
邵江禾
(中國政法大學,北京100088)
寬恕制與私人執行存在著立法價值的協同、制度功能的互補以及實踐效果的互斥的應然聯系。但基于實踐效果的互斥會對這兩種制度功能的發揮產生不利影響,歐美各國都會設立一系列配套制度以割裂此種聯系,這種先聯系后割裂的方式是兩種制度得以有效實施的路徑依賴。我國的寬恕制與私人執行制度并不存在此種路徑依賴,導致這兩種制度在實踐中無法發揮應有的效果,因此應然聯系的恢復以及實踐聯系的割裂應作為我國完善這兩種制度的方法。
寬恕制度;私人執行;應然聯系
一、寬恕制與私人執行的應然聯系
反壟斷法中的寬恕制度起源于美國,是由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在70年代末發展出的一種獨特的卡特爾調查工具,是“囚徒困境理論”在反壟斷法領域的適用。相較于反壟斷法百余年的發展歷史,發展不足40余年的寬恕制卻早已顯露鋒芒,被譽為“美國歷史上發現大宗商業犯罪的最為成功的制度”,引發世界各國的爭相效仿。[1]從寬恕制度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發現,其是法律賦予反壟斷執法部門在審查壟斷協議時享有的法定權利,存在于公共執行過程中。而私人執行是指受排除、限制競爭行為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市場主體向法院提起反壟斷訴訟。[2]因寬恕制度適用于卡特爾行為中,為保證邏輯上的對應,故本文所論述的私人執行亦限定于對壟斷協議提起的民事訴訟行為。
私人執行與公共執行是對應概念,而寬恕制度又是公共執行中的子制度,因此寬恕制與私人執行之間在邏輯上屬于并列關系。二者并非不存在交集,實際上無論是在立法價值、制度功能層面還是實踐效果上都存在著“互動”。
首先,私人執行與公共執行是反壟斷執法的兩種模式。私人執行直接對市場主體實現正義,實現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公共執行通過公權力的行使增加行為主體的違法成本。而寬恕制作為實現公共執行價值目標的最優手段之一,以嚴厲的法律責任為基礎,同時賦予執法機關對主動報告的經營者豁免的權利以達到分化卡特爾的目的,進而提高公共執行的效率。因此,寬恕制度與私人執行均通過對理性行為主體的最佳威懾,實現反壟斷法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立法宗旨。可以說,在立法價值層面上,二者是協同的。
其次,私人執行與寬恕制在執法主體上的差異,必然會產生制度功能的主體性偏好。美國國會將私人執行主體稱為“私人檢察總長”,該私人檢察總長在行使權力時難免會將自身利益的維護作為首要目標,更加關注反壟斷法的救濟功能,而公共利益的實現則成為私人權益保護的間接效果。若人人皆想獲得賠償和懲罰性報酬,則為尋找違法行為者而付出的資源還會出現浪費,雖節約了行政成本,但其是建立在司法成本激增的代價之上,這是私人主體偏好產生的極端效果。[3]同時,由于壟斷行為的審查需要耗費大量的行政資源,執法機關對輕微壟斷行為往往采取選擇性忽視,只有私人執行才可能對其進行規制。而寬恕制的制度設計在于優化公共執行的效率,通過分化行為主體,拓寬反壟斷法公共實施機構的信息和證據來源,節約行政成本,提高執法效率。這種立法原意造成了寬恕制在功能上產生了另一種主體偏好,即優化資源配置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私人權益救濟功能退居次位。但相對的,二者中任一種制度的主體性功能偏好恰恰是另一種制度的主體性功能缺位,即私人執行的主體性偏好可以彌補寬恕制救濟功能的缺位,寬恕制的主體性偏好可彌補私人執行對公共利益的忽視。當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這種主體偏好就能得以矯正。在此種情景下,可以說,二者在制度功能上是互補的。
最后,貝克爾和喬治·斯蒂格勒曾言,法律私人實施主體之間為爭奪從違法行為者手中獲得的賠償份額而展開的自由競爭,可以達到與最佳公共實施幾乎同樣程度的威懾效果。[4]但實踐效果往往并非如此,私人執行的發展會抑制寬恕制度功能的實現。這種抑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寬恕制度的有效實施是以公法責任產生的最佳威懾和法律責任的豁免為前提的。公法責任產生最佳威懾效應的同時也產生了最佳誘導效應,即嚴厲的公法責任的豁免誘導“囚徒”內部產生分化。由于寬恕制度減免的一般是公法責任,民事責任無法得到免除,導致公法責任產生的誘導效應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違法行為主體在此種情境下便會進行成本效應分析,若主動報告產生的豁免利益并不明顯大于不報告產生的損失(包括民事責任的損失),即寬恕申請成本過高,則制度的有效性就值得懷疑,因為主動報告還可能使行為主體在本行業中面臨名譽損失等無形資產減損。這種抑制在美國反壟斷法三倍賠償制度、連帶責任制度的作用下顯得尤為明顯。第二,執法機構基于寬恕制度而做出的裁決等相關文件可能成為私人執行的證據。一旦向反壟斷執法機構報告了卡特爾的事實及相關證據,依據禁止反言的原則,主動報告人即等于承認了從事卡特爾行為,在私人執行的訴訟程序中不得予以否認,面對私人的指控,其僅能就諸如原告的適格性、造成的損害或管轄權等問題提出抗辯。[5]第三,對受害者進行賠償作為得到豁免的前置條件亦會對違法當事人主動報告的積極性產生抑制作用。通過這三點的論證可以發現,私人執行與寬恕制在實踐效果上是互斥的。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私人執行與寬恕制具有以下應然聯系:立法價值的協同,制度功能的互補以及實踐效果的互斥。這種應然聯系于制度設計之時便內生存在著,相關國家在引進借鑒該制度時,理應產生相同的關聯。
二、國外對實踐效果互斥聯系的割裂
價值的協同、功能的互補對兩項制度都有促進作用,而實踐上的互斥卻會對制度的發展產生或多或少的抑制作用。為消除該負作用,世界各國都會制定相應配套措施將此種互斥聯系予以割裂。比較典型的諸如保密制度、懲罰性賠償的減免、連帶責任的免除、初步證據排除規制以及刑事責任的免除等。
1、保密制度。保密制度不僅僅是為了防止報告者受到集體排擠或經營上的干擾,同時也能防止行為人直接因主動報告而承擔民事責任。對于這一點,歐盟、美國和英國等國都有各自的規定,如歐盟在06年頒布的《關于見面卡特爾案中罰款的委員會的通知》(“The 2006 Guidelines”)第33條,英國《企業法》第9部分關于限制披露的規定等。
2、初步證據排除規則。根據美國《克萊頓法》的相關規定,若主動報告者與反托拉斯司達成寬恕合意,那么因達成的寬恕而產生的相關文件均不能作為日后民事訴訟中損害賠償的最初證據。
3、懲罰性賠償的減免。這一規定是指若主動報告者在滿足了法定條件后,可以對民事損害賠償數額在懲罰性基礎上予以減免,但仍應承擔相應的補償性賠償責任。
4、連帶責任的免除。該制度是指主動報告者在受到寬恕之前本應與其他卡特爾成員承擔共同侵權的連帶責任,但基于其主動報告行為免于對懲罰性賠償承擔連帶責任,但仍應承擔自身的補償性賠償責任。
5、刑事責任的免除。國外反壟斷法對卡特爾行為都規定了刑事制裁,當報告者滿足寬恕條件后,其本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即得到豁免,如美國分別對公司刑事責任以及個人刑事責任的豁免都予以明確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相關制度上采用了3、4、5項規則合并適用的方法。根據美國2004年的《反壟斷刑事處罰優化與改革法》的相關規定,在報告者獲得刑事豁免的前提下,只要其提供了實質性的合作,即可將其三倍賠償責任減為單倍賠償,同時免除其連帶責任。[6]這種規制方法的目的是在提高執法效率與私人權利救濟之間進行平衡。
結合第一、二節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寬恕制與私人執行制度的制定與運用過程中,遵循著這樣一種規律:即兩種制度在設立過程中存在著三種應然聯系,這是制度的先天性安排,但實踐效果的互斥聯系對制度的有效實施產生了損害,為了消除這種負作用必須制定一套制度將該聯系予以割裂。筆者認為這種“先聯系,再割裂”的規律正是寬恕制與私人執行得以存續并發展所應遵循的“路徑依賴”。
三、我國私人執行與寬恕制度的實然聯系
我國的《反壟斷法》也引進了私人執行與寬恕制度。①《反壟斷法》第50條體現了私人執行制度;第46條第2款體現了寬恕制度。除此之外,最高院于2012年5月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高法解釋》)對私人執行的舉證責任、訴訟程序作了明確;國家發改委于2010年12月頒布的《反價格壟斷行政執法程序規定》(以下簡稱《發改委規定》)以及工商總局2010年12月頒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禁止壟斷協議行為的規定》(以下簡稱《工商規定》)對寬恕制度進行了細化。
正如前文所述,我國引進的上述兩項制度亦應存在著該種應然聯系,但對我國現行制度進行分析時發現,立法價值的協同聯系是存在的,制度功能的互補以及實踐效果的互斥聯系卻被割裂了,這種割裂是基于制度的不完善而產生的。
(一)制度功能聯系的割裂
制度功能的互補是基于兩種制度的主體性偏好產生的,我國的制度下也存在著主體性偏好,但由于私人執行制度的威懾力不足,造成功能互補難以實現。私人執行往往通過民事訴訟以實現對受害者的直接正義,因此其中最為關鍵的便是原告資格、舉證責任以及損害賠償。
首先,在原告資格問題上,根據《反壟斷法》第50條以及《高法解釋》第1條的規定,有權提起訴訟的主體應是受到壟斷協議損害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理論上原告主體資格覆蓋全面,但在現實生活中,因卡特爾行為而受損害的往往是不特定多數人,他們所受損失金額較少。受害者在沒有較大激勵機制的作用下,考慮到訴訟成本和風險,往往使很多違法行為主體逃脫相應的民事責任。[7]這是兩種制度在功能聯系上割裂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舉證責任問題上,由于壟斷協議不僅包括明示的協議、決定,還包括默契型共謀,原告往往無法對此提出有效證據。《高法解釋》第7條已經明確對壟斷協議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的舉證責任應由被告承擔,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原告舉證困難的問題,有利于增強私人執法的威懾力。
最后,在損害賠償標準上,《高法解釋》的出臺并未帶來太大的改觀,其第14條規定仍將損害賠償限定于“填補責任”上。盡管將原告因調查、制止壟斷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計入損失賠償范圍,但相對于美國的三倍賠償責任以及違法行為人連帶責任的明確規定,我國的相關規定明顯激勵不足。
顯然,上述原因導致了私人執行威懾效應缺失,受害者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無法對寬恕制在私人救濟不足上的功能性缺陷形成互補。
(二)實踐效果聯系的割裂
實踐聯系的割裂是由寬恕制度與私人執行在具體實踐中的乏力造成的。
對寬恕制而言,其只有在最佳威懾的條件下才能產生實踐效果,而這種最佳威懾需要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的共同作用,但我國《反壟斷法》對于責任規定的缺陷致使寬恕制難以有效發揮。
首先,我國公共執行中的行政責任僅適用于企業。根據《反壟斷法》第46條的規定,壟斷協議行為的行政責任主要包括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和行政罰款。行政罰款是威懾力最大的行政責任,該法條同時規定了對違法經營者處上一年度銷售額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罰款,尚未實施所達成的壟斷協議的,可處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除美國《謝爾曼法》規定最高罰款數額為企業1億美元以下,自然人100萬美元以下之外,以銷售額的10%作為罰款征收標準已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在數額上我國遵循了國際趨勢。[8]但我國的行政罰款的對象僅限于企業,其理由主要是,企業實施限制競爭只是為了給企業謀取不正當的經濟利益,即便企業領導參與了該活動,他們實際也是代表公司行為。[9]這種理論忽視了企業的意志是由高管人員所表達,僅對公司處以罰款對企業管理人員難以形成有效威懾。有人認為對高管處以的罰款最終會被其轉嫁到公司,但在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下如股東代表訴訟,高管的這種規避策略將難以實現。[10]因此,對企業高級管理人員處以行政罰款是必要且可行的。
其次,我國對壟斷協議違法未規定刑事責任。刑事責任是寬恕制度得以實施的制度基礎,是最佳威懾效應產生的必要條件。相較于美國刑事責任的規定不僅適用于企業,而且對自然人也規定了可處10年以下監禁的刑罰,[11]我國《反壟斷法》對卻壟斷協議犯罪及其刑事責任只字未提,致使公共執行只能停留在行政責任上。
對私人執行而言,正如前文所交代,私人執行因主體性功能無法發揮,導致其在實踐運用中會遭遇各種阻礙。自《反壟斷法》實施以來,雖然私人反壟斷訴訟案件逐漸增加,但其中大部分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問題,卡特爾案件因舉證困難,受害者往往選擇知難而退。盡管《高法解釋》已解決了舉證責任問題,但由于原告資格的限制和激勵機制的欠缺,私人執行的威懾效應難以得到較大提升。
實踐效果的互斥應以寬恕制和私人執行在實踐中的良性運行為前提,任何一種制度功能的缺失都無法產生互斥效果。通過上述分析,兩種制度在我國運用時由于制度缺陷在實踐中早已自顧不暇,無任何余力再對對方產生影響,脫離了應然的發展路徑,造成了二者在實踐效果的聯系上產生了割裂,實際上成為了兩項完全獨立的制度。
四、我國應然聯系的建立與實踐效果聯系的割裂
如第二節所述,寬恕制與私人執行的有效實施是存在路徑依賴的,對其二者的完善應回復到正確的路徑上來,即先建立應然聯系,再結合我國國情將實踐聯系進行割裂。
首先,應然聯系的建立。寬恕制與私人執行的完善是應然聯系建立的必要前提,因此必須做到以下幾點:第一,盡快搭建起我國的反壟斷法刑事責任制度,且應細化為公司刑事責任與個人刑事責任;第二,將行政責任的適用對象擴展至單位責任人員;第三,在前兩項明確后,建立公司寬恕制與私人寬恕制。當公司獲得寬恕時,其職員同時獲得寬恕,而當公司決策層無法就申請寬恕達成一致意見時,職員個人可申請寬恕,此時公司與其他職員無法得到寬免,以此在公司與公司之間、公司與職員之間以及職員與職員之間形成一種博弈關系;[12]第四,將集團訴訟制度引人到私人執行之中,以行業協會或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代表受害者提起集團訴訟,以降低受害者面臨的司法風險;第五,確立適當的懲罰性賠償額。考慮到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美國的法定三倍賠償處罰力度過大,但雙倍賠償或酌定雙倍賠償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提高私人執行的威懾力。
其次,實踐效果聯系的割裂。實踐效果聯系的割裂應輔以一定的配套制度,對此可參考國外相應的配套制度,如美國將刑事責任的免除、實質性合作作為懲罰性賠償的減免和連帶責任的免除的前置條件,在提高執法效率與維護受害者權益的目標之間進行協調。此外,執法機構也不應當將在公共執法中獲得的證據或形成的文件、裁決提供給民事訴訟中的原告和法院,并且法院在裁量時也應將“獲得寬恕”作為裁量的要素之一。[13]
綜上所述,我國在寬恕制與私人執行制度的設立時應尊重應然聯系的存在,在實踐中應對互斥聯系予以割裂,通過“兩步走”戰略,使得兩種制度回復到正確的路徑中,使其發揮應有的制度功能。
[1]Commission Notice on Immuni ty f rom Fines and Reduc tionof FinesinCar tel Cases[2006]OJC298/17.
[2][7][9]王曉曄.反壟斷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47—348.353.359.
[3]丁國峰,畢金平.論反壟斷法之公共執行與私人實施的協調[J].中南大學學報,2012,18(1):81.
[4]Landes’Wil liamM.’RichardA.Posner.TheEconomic Structureof Tort Law[M].Cambr 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7.
[5][12]柳鐳.從美國經驗看我國反壟斷法寬恕制度的完善[J].西南石油大學學報,2013,(1):66.65.
[6]劉紅.寬恕制度對反壟斷民事賠償的影響及其對策[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12,(5):43.
[8]Anti trust Cr iminal Penal ty Enhancement and Reform Act of 2004(HR1086),15USC&1(2004).
[10]馬立釗,畢金平.反壟斷法中民事損害賠償對寬恕制度實施的影響[J].山東社會科學,2011,(10):79.
[11]Sherman Act,15U.S.C.&&1—2
[13]王先林.論反壟斷民事訴訟與行政執法的銜接與協調[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3):90.
(責任編輯:滕元良)
On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Forgiveness System of Anti-monopoly Lawand Private Enforcement
Shao Jianghe
ract:there are ought-to-be contacts between forgiveness system and private enforcement system,the collaboration of legislative value,the complementof institutional functionsand themutualexclusion of practicaleffect.However,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mutual exclusion of the practicaleffectwould adversely affect the two systems to exert functions,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w ill establish a seriesof supporting systems to split such links.Thisway,firstbeing contacted then being fragmented,is the path dependence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systems.The forgiveness system and private enforcement system in China have no such path dependence,so that in practice the two systems cannot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so the recovery ofought-to-be contact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practical link should be taken as theapproach perfecting the two systems.
ords:forgivenesssystem;private enforcement;ought-to-be contact
D922.294
A
1008—6153(2013)04—0057—04
2013-05-17
邵江禾(1990-),男,浙江衢州人,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