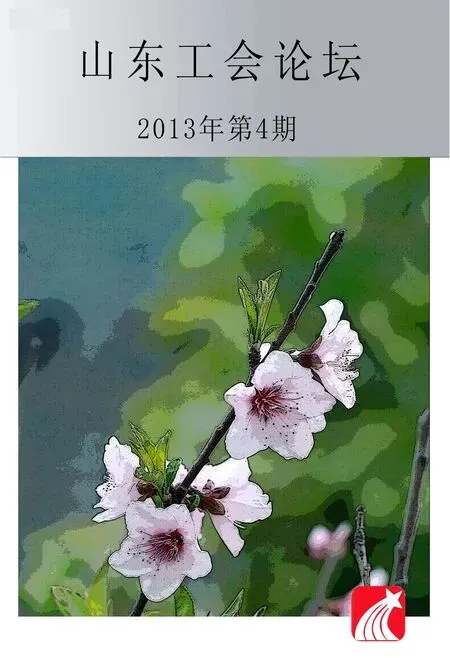試論卡爾·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
——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文本解讀
李靜
(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安徽合肥230601)
試論卡爾·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
——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文本解讀
李靜
(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安徽合肥230601)
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提綱》是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作品,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探討了人的本質問題。《提綱》是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區別并超越前人的重要學術作品,其關于人的本質理論揚棄和超越了二元分離和對立以及還原主義等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更為深刻地指出了人的社會關系本質,是對人的本質更為現實、全面、科學的創新。同時,馬克思發現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從而抓住了“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真正發現了人的完整本質。簡言之,馬克思的人的本質理論,就是從人的社會屬性看人的本質并以實踐活動實現人的本質。
馬克思;人的本質;社會屬性;實踐;《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一、《提綱》對于解讀人的本質的意義
卡爾·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是其整個理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人的本質理論是馬克思形成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支撐點;人的本質理論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和解決關于人的一切問題的基本方法和思路;人的本質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確立起改造社會的價值目標的重要理論依據[1]。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等著作中都對人的本質進行了探討,但是《提綱》作為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哲學相區別的第一個文獻,更能體現馬克思成熟時期的思想。因此要分析馬克思的人的本質理論就需要對《提綱》進行文本解讀。馬克思的《提綱》寫于1845年布魯塞爾,但在其生前并未發表,而由弗里德里希·馮·恩格斯整理作為《費爾巴哈論》的附錄發表。《提綱》是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唯物主義思想的前期作品。雖然《提綱》全文不足一千五百字,但是其學術價值卻是巨大的。恩格斯對《提綱》便有很高的評價,認為這是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是非常寶貴的。雖然《提綱》沒有系統闡述出馬克思的全部思想,但是作為“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提出了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許多關鍵之處,在這其中就包括了關于人的本質的理論。《提綱》的出版對于人的本質理論來說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提綱》是馬克思的人的本質理論區別并超越前人的重要學術作品。《提綱》中關于人的本質理論,是人在社會關系中的制約性和創造性形成了人與社會關系的互相指涉、相互規定和相互闡釋,也正是這種“解釋學”循環,才使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揚棄和超越了二元分離和對立以及還原主義等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2]。并且,《提綱》重要的意義還在于,馬克思對費爾巴哈人的本質理論進行批判的同時,更為深刻地指出了人的社會關系本質。正是馬克思那一句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宣布了一個新的哲學時代,馬克思哲學新世界的初始地平線就是在此出現的:這就是對人類主體、人類社會實際及其觀念的歷史的、現實的、具體的限定[3]。馬克思所界定的人的本質是不同于費爾巴哈所提出的抽象的人的本質,是對人的本質更為現實、全面、科學的創新。
二、從人的社會屬性看人的本質
馬克思吸取以往哲學家們的研究成果,揚棄他們的錯誤,從社會關系中探討人的本質。《提綱》就是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定義的文本體現,“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于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撇開歷史的進程,把宗教感情固定為獨立的東西,并假定有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的個體;2、因此,本質只能被理解為類,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聯系起來的共同性。”(《提綱》第六條)
費爾巴哈把神的本質歸結為人的本質,用人的本質去說明神的本質。但是他所說的人主要是自然的、生物學意義上的抽象的人,是處于“你”和“我”關系中的人,而他所謂的人的本質就是從“你”和“我”這些單個的人中抽象出來的共同性和統一性[4]。費爾巴哈雖然較之前的哲學家關于人的本質認識有一定的進步,但是仍有不足。他對人的本質的理解脫離了人的社會性,把人的本質僅僅歸結為理智、意志、感情等,這就把人的本質看成是單個人自生來便具有的共同特征的抽象生物。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費爾巴哈的“類”不過是“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人純粹自然地聯系起來的共同性”。雖然費爾巴哈力圖超出僅從人的自然屬性考察人的局限,也承認了人的社會性,但他所認為的“社會性”主要是“你”“我”之間感情交往的相互依賴性,并不是一個以社會物質生產為根基的概念,是空洞抽象的概念。
而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在單個人中,而是在各種關系中,在社會關系的總和中。他認為人的本質的范疇包括了人的社會屬性,只有把人放在一定的社會生活關系中才能真正理解人。他強調社會屬性對于人的重要性,主張從人的社會屬性來看人的本質,而不是局限在自然屬性中,更不是將社會意識視為人的本質。馬克思批評費爾巴哈從來沒有看到真實存在著的、活動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僅僅限于在感情范圍內承認“現實的、單獨的、肉體的人”。所以,費爾巴哈沒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會的產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個人,實際上是屬于一定的社會形式的。在馬克思這里,人的社會學涵義更加豐富、深刻。他不僅指出人是相互依賴的,并且從社會物質生產、人的生存方式來看相互依賴。馬克思理解的人的本質是建立在現實性即生產勞動基礎上的各種關系的總和。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評價費爾巴哈所作出的貢獻時說,費爾巴哈創立了真正的唯物主義和現實的科學,因為費爾巴哈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成了理論的基本原則[5]。雖然,費爾巴哈所定義的人的本質是從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角度入手的,但是費爾巴哈的人是“以自然為基礎的現實的人”,而馬克思的人則是“以社會為基礎的現實的人”[6]。費爾巴哈雖然也強調人的社會性,但遠沒有馬克思所所提出人的社會性深刻。在《提綱》中馬克思批判費爾巴哈把人的本質認為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提出在現實性上,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個著名哲學論斷為考察研究人的本質提供了科學的判斷方法,表明人的本質是需要置身于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中予以考察的。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理解基于現實性的社會關系,將人的社會屬性納入人的本質,是他對人的本質認識的重大飛躍。
三、以實踐來實現人的本質
馬克思提出人的本質理論即“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里的“在其現實性”上意指什么呢?對這句話的解讀就需要參考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指出,如果在考察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等等時把人的存在的這些社會形式看做人的本質實現,看做人的本質的客體化,那么家庭等等就是主體內部所固有的質[7]。人的本質的實現,是指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等社會形態或社會形式,而這些社會形態或社會形式就是人勞動實踐的產物和表征[8]。人作為社會中的人,盡管只能在一定的社會中才能發揮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然而卻不能僅僅把社會性看成人的本質,脫離人的實踐活動無法真正理解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
費爾巴哈雖也使用過實踐這個詞匯,但是他所指的實踐與馬克思的實踐有著本質區別。費爾巴哈把實踐看作是猶太人的利己主義活動,而不是如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的實踐、革命的實踐[9]。馬克思就直接在《提綱》中指出,費爾巴哈的錯誤在于他把人的本質絕對化、抽象化,而這一錯誤的根源又在于“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提綱》第一條)且馬克思還批判了舊唯物主義忽視了實踐的重要性。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做到對“市民社會”的單個人的直觀。(《提綱》第九條)顯然,舊唯物主義的直觀性、淺表性的問題,正如費爾巴哈一樣,沒有把人的活動當作對象性的活動去看待,不了解實踐本身的意義。
而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任何人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從事一定的社會活動。社會活動不能由單獨的個人進行,它本質上只能是社會性的實踐活動,在實踐基礎上形成和發展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從此解讀出,正是人類所具有的參與具有創造性的社會活動的能力,根據某種計劃對“外部”自然界施加影響的能力,使人類與其他生物相區別,而這種能力就是勞動,也就是實踐。人是社會的主體,社會中的一切關系都離不開人,沒有人的實踐活動就沒有生產力,沒有人在實踐活動中創造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也就沒有生產關系。人以實踐作為自己的存在方式和活動方式,也就是以社會關系的綜合所構成的“歷史境況”作為自己的生存背景和活動條件[10]。
理解人的本質是基于現實性上,把握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以實踐活動實現人的本質。馬克思的高明之處就在于:發現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從而抓住了“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真正發現了人的完整本質[11]。因為脫離實踐活動無法實現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只能處于抽象、空想狀態,無法實現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本質。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現實性上,通過實踐活動才能實現人的本質。
四、結語
《提綱》這個文本非常重要,通常被視為馬克思哲學思想基本成熟的標志,它是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哲學劃界的第一個文獻,提及了馬克思許多重要的理論。對《提綱》的文本解讀雖不能了解馬克思全部的思想理論,但是《提綱》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馬克思思想的系統表達,因此解讀《提綱》是可以極大幫助我們理解馬克思的理論思想的。當然,由于《提綱》的全篇僅有十一條提綱性的簡明文字,因此對《提綱》的解讀就需要結合馬克思其他著作才能較準確地理解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對《提綱》每一條解讀的同時,應結合馬克思在寫作時期主要的思想及其他著作,只有結合《提綱》寫成的同時期其他作品及時代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馬克思的理論。
每個人思維角度的不同也意味著每個人所理解的馬克思理論的不同,正是不同的解釋者對馬克思理論的解讀,才豐富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進步。且作為解釋者,我們并不是馬克思本人,因此無論我們再怎么努力也無法完全代表馬克思的思想。但是這并不能成為我們放棄解讀馬克思經典文本的借口,作為馬克思這樣的哲學家,解讀其經典文本的過程也是促進我們人文社會科學前進的過程。
[1]趙甲明,吳倬,劉敬東,王峰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專題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66.
[2][10]周志山.馬克思社會關系理論及其當代意義[M].濟南:齊魯書社,2004.116.114.
[3]劉懷玉.馬克思哲學關鍵環節的歷史原象——從《未來哲學原理》到《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J].河北學刊,2006,(6).
[4]歐光南.論馬克思對費爾巴哈人的本質屬性思想的批判繼承與超越[J].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8,(12).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58.
[6]李俊波.馬克思對費爾巴哈“抽象的人”的批判[J].學理論,2011,(10).
[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50.
[8]章海山,羅蔚,魏長領.斯芬克斯現代之謎的破解[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34.
[9]龐小云,艾延琳.論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實踐觀及其意義[J].新學術,2008,(3).
[11]楊耕.為馬克思辯護——對馬克思哲學的一種新解讀[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405.
(責任編輯:王友才)
A811.2
A
1008—6153(2013)04—0168—03
2013-05-16
李靜(1988-),女,四川宜賓人,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