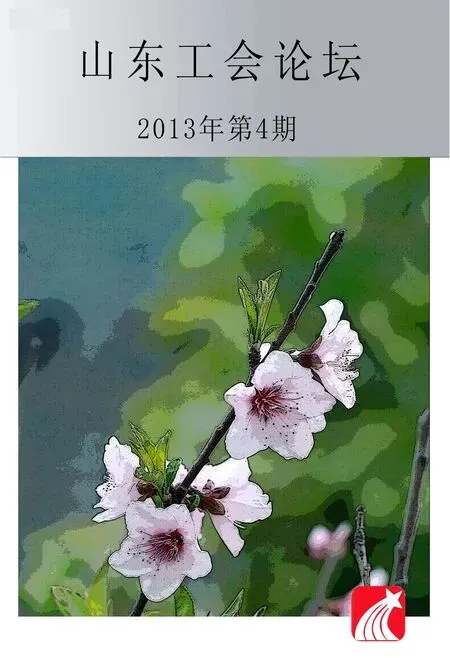黃庭堅書法美學中的禪宗特征分析
李囡楠
(濟南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山東濟南250300)
【社會科學綜論】
黃庭堅書法美學中的禪宗特征分析
李囡楠
(濟南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山東濟南250300)
黃庭堅是書法大師,為宋代四大書家之一,是一個將禪宗發揮到高深境界的典型文人居士。針對當時因襲古人的風氣,黃庭堅受禪宗思想啟發,以禪悟書,勇于創新,所創作的草書開辟了一個新天地。黃庭堅草書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其對禪的參悟,禪宗思想對其書法美學的影響非同一般,“觀韻”、“絕俗”隨之成為他主要的書法美學特征。
黃庭堅書法美學;禪宗思想;美學特征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北宋詩人,書法家,詞人,江西修水縣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進士,為宋四家之一,是宋書尚意的重要人物。曾任葉縣尉、北京國子監教授、校書郎、秘書丞等職,作為宋代卓越的書法家,他的書法成就主要表現于其草書和行書中,《李白憶舊游詩草書卷》、《諸上座帖》等是黃庭堅晚年草書代表作。
黃庭堅書法初期師從宋代周越,后又受顏真卿、懷素等人影響,逐漸形成自己的書法風格。黃庭堅不是一位單純的官吏和藝術家,更不是一位單純的書法家,在其六十一年的歲月里,他是一個將禪宗美學發揮到高深境界的典型文人居士,他亦禪、亦官、亦詩、亦藝,追求儒佛合一,將其深厚的學術修養、險惡的仕途沉浮感受與高深的佛學修養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心無旁騖地將人間冷暖凝注筆端,為后世留下一座充滿禪宗思想境界的草書藝術的豐碑。
一、禪宗思想對黃庭堅的影響
黃庭堅家鄉在洪州府分寧縣(今江西省修水縣)高城鄉雙井里。他的父親黃庶中過進士,仕途并不順利,只做過邊遠地方的小官,但為人剛直不阿,在黃庭堅十五歲時死在任上,對黃庭堅以后的為人影響很大。黃庭堅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小時候常去河邊放牛。疼愛他的舅舅家里藏書很多,他得以飽讀詩書,為以后的學術修養打下了基礎。童年時期黃庭堅就已顯露出過人的才華,讀書能一目五行,讀過幾遍詩書就能默誦,被人們稱作神童。《宋史》《黃庭堅傳》載:“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名聲始震。”可見黃庭堅在文學上的造詣很深。
黃庭堅自幼受到佛學的熏陶。他的家鄉附近有座南禪寺院,祖母仙源君是虔誠的禪宗門徒,常到南禪寺院參禪拜佛。黃庭堅小小年紀就有慧根,“少喜學佛”,七歲時便能作出《牧童》詩句:“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垅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算盡不如君。”后來,黃庭堅仕途不順,在政治上屬于元祐黨人,政治生命和北宋王朝波譎云詭的政治變革始終交錯在一起,個人命運同王安石變法及其后的新舊朋黨斗爭休戚相關。腹有才華的他卻偏偏數度被貶,不斷身處逆境,長期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一度被貶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后又被貶到更偏遠的戎州(今四川宜賓)。他先后兩次喪妻,生活上受到沉重打擊。種種不如意使黃庭堅心灰意冷,竟戒酒色肉食,發誓不再娶妻,將志向轉移到了參禪與治學之上。遭貶后的黃庭堅饑寒交迫,連老百姓都很同情他的遭遇,可他卻若無其事,無絲毫垂頭喪氣之意,照樣談笑風生,每日里把心思都用在了研讀詩書和練習書法上。他對安慰他的人說:“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者乎?”人們聽后十分敬佩他的安貧樂道。
在飽嘗人間冷暖、看透世事無常之后,他對禪宗的領悟進一步加深。他自己看淡功名利祿,凡事泰然處之,脫凡超塵。他自認為自己已是“似僧有發,似俗無塵,作夢中夢,具身外身。”禪宗思想認為人生如夢幻,隨緣任運即是解脫,生與死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宣揚一切隨緣,看淡世間的名利,凡事不可強求,強調自我的心理調節才能解決現實中一切苦難和問題。在黃庭堅的詩詞中也多表現出冷靜、恬淡、“物外之賞”、“平常心是道”的人生態度。“主人心安樂,花竹有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人們讀其詩詞猶如行走在荒郊野外,猶如行走在通天大道之外的偏僻幽徑中。禪宗“隨緣自適”的思想給飽經憂患的人生帶來了沖淡平和、怡然自得的情趣。雖然黃庭堅一生中有過無數的痛苦、矛盾,但正是由于他對禪宗的執著、癡迷、領悟,才幫助他驅散心中的迷霧,克服物質上的苦難,解除精神上的巨大包袱,達到常人無法能及的藝術境界。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禪宗教義與老莊哲學有契合之處,親近自然,希望從自然中吮吸療養傷痛的乳汁,來擺脫世事的枷鎖,獲取心靈的解放。黃庭堅的參禪悟禪,深刻影響了他的書法創作。
二、黃庭堅書法美學中的“觀韻”特征
禪宗是典型的中國式佛教,是中國佛教的實踐派,又稱宗門。在宋代,禪宗開始流行開來,普遍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也成為了許多失意人士的精神寄托,禪宗思想隨之逐漸進入書法領域。宋朝重文輕武,文人地位很高,藝術觀念和形式也面臨著變革,文學上宋詞取代唐詩成為主流;美術上文人畫蓬勃興起;書法上一大批書法家不甘于囿于前人的陳規,爭取形成新的風格,給書壇帶來新的氣象。清朝文人在歸納中國書法發展史說,“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這里說的“意”和“禪”有密切的關系。而“禪”和黃庭堅書法的關系,則集中體現在他的“觀韻”之上。
在黃庭堅書論、題跋中,他多次論述到“觀韻”。“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仿佛。”(《題絳本法帖》)“凡書畫當觀其韻。”(《題摹燕尚父圖》)他的書法深受禪宗思想影響,“觀韻”成為他突出的書法美學特征。關于“韻”,在黃庭堅之前已有人論述過。曹植《白鶴賦》中提出“聆雅琴之清韻”,也許是把“韻”引入藝術領域的開始,這時的“韻”還是指音樂的節奏和韻律,是一種與情感相關的對音樂形式美的感受。魏晉時期,“韻”被用來形容人的氣質、精神品格及外在的風度,如“拔俗之韻”、“風韻邁達”等等。南齊的謝赫在《古畫品錄》開始將“韻’引入在繪畫領域,把“氣韻生動”列為繪畫“六法”之首。“韻”的含義逐漸豐富起來,主要用來形容藝術形象的傳神寫照,也指人的情感因素參與進來,藝術形象或具體的物象形體所呈現的一種審美狀態。錢鐘書也指出: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韻”之謂也。曰“取之象外”,曰“略于形色”,曰“隱”,曰“景外之景”,曰“余音異味”,說豎說橫,百慮一致。[1](p1312、1352-1365)黃庭堅書法美學中的“觀韻”,是強調書法作品要有“意”、“有余意”,也就是要有無盡的表現力,追求別致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意”。禪宗講究領悟、頓悟,“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不講究用語言文字來傳經布道,不講究用具體的物象色彩來表達深奧玄遠的佛理,禪宗這種含蓄、蘊藉的表達方式直接影響了書法創作。
黃庭堅要求書法家要擺脫工拙法度的束縛,追求字外有字,境生象外,以有限的筆墨線條組合形式來表現無限的情感追求、豐富的藝術含蘊和崇高的境界,留給觀賞者無盡的聯想、意蘊和啟迪。唯有如此,才能在有限的線條內“觀韻”、“暢神”,才能在有限的形式內體味到無限的意義,這樣的書法作品才可謂具備了藝術表現力,才達到了“韻”的境界。黃庭堅認為書法美的最高境界即“韻勝”而“無法”。要達到這一境界,首先必須有藝術積累和修養。黃庭堅打通禪書界限,“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以禪喻書,將“字中有筆”喻為“禪家句中有眼”。這也說明黃庭堅草書的成熟還得益于其對禪的參悟。黃庭堅認為書法須自然天成。“余寓居開元寺夕怡思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張旭、懷素基本上是酒后作書,進入忘我迷狂狀態,作品能夠出神入化。
而黃庭堅的書法不加雕琢修飾,隨“意”而行,重心輕物、重意卑法、重神遺形,結構上中宮斂結,長筆四展,既能“密不容針”,又能“寬可走馬”,不僅給人張弛有道、剛柔并濟、渾然天成的暢神之感,而且整幅作品充溢著徐徐神韻,字體結構自適,大小左右,疏密徐疾,都各得其所,猶如天成,觀之如極目海天一色,如星布蒼穹,如滿山春色,如散仙興會,偉岸、豪放而不失恬淡、嫻靜、優雅。黃庭堅進入非理性狀態不靠飲酒,靠參禪妙悟而進入揮灑自如之境,一切從個人平和的心境出發,提筆揮灑的決不是那種懷才不遇、世事無常的苦痛與憤懣,而是一種高山流水、春來花開、順其自然、沖淡平和、無為而為的豁達情懷,從而把揮毫潑墨變成心靈自由的“有意味”的形式。他的草書既能縱橫跌宕,大開大合,聚散收放,也能從容嫻雅,行云流水,真得禪宗妙理,體現了“觀韻”的審美理想,開辟出中國草書的新天地。
三、黃庭堅書法美學中的絕俗特征
除“觀韻”之外,“絕俗”同樣是是黃庭堅書法美學思想的核心。
針對當時因襲古人、人們爭相模仿晉唐法帖的書風,黃庭堅發出“絕俗”的吶喊,要求世人不要一味泥古。“法”束縛了創新的精神,他的吶喊可謂發人深省。“《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而不害其聰明睿圣,所以為圣人。不善學者,即圣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2](p796)《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
黃庭堅對各種各樣的“俗”都深惡痛絕,要求書法家首先要做“不俗之人”。而要做到不作俗人,不作俗書,則“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他認為人要想脫俗,心就不能不牽于外物,要想妙于筆,首先要妙于心。“書如其心”,一個人心不如人而欲書過人,只能是南轅北轍。黃庭堅認為,一個人練習書法,勤學苦練,師法大家,可謂有法之法;而博覽群書,有學識,妙于心,方能豐富心靈,擴充才情,棄俗從雅,從而書中有意,筆端含情,興之所至,意得趣生,別構靈奇。可見,以“妙心”代學識、才情是提升書法品格、醫治“俗書”、擺脫工匠習氣的良方。
蘇軾說:“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3](p42)在當時宋代書法追求超越前代書法宗師的背景下,禪宗思想給宋代書法提供了追求創新、破除陳規、棄俗從韻的精神動力。禪宗明確規定自己的禪法是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念”要對萬事萬物都不產生貪戀或放棄的念頭,“心不染境”,在念念之中排除一切雜念妄想,不產生固定的好惡、美丑觀念;“無相”是反對執著各種名相、境界,無有實體,無所執著,不能執著于一切法相;“無住”是于心無事,于事無心,是對世界和周圍事物不執固定的見解和有所取舍的特定的心理趨向。這些思想強調勇于創新,不墨守成規,強調“隨心所欲不逾矩”,強調藝術的自由創造和個性的發揮,為“絕俗”奠定了理論基礎。
“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周星蓮在《臨池管見》中贊賞黃庭堅的“絕俗”:“黃山谷清癯雅脫,古澹絕倫,超卓之中,寄托深遠,是名貴氣象。”正如黃庭堅本人在《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中所說:“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品藻譏彈。”可見他在書法藝術中已經達到了自由的境界,他的一家之法即是無法之法,這種很高的書法境界,不是常人能夠達到的。他要求于人的不僅僅是精湛的技巧,更要有深刻的人生體驗,達到藝術最根本的生命終極關懷。[4](p175)
黃庭堅書法美學思想是寶貴的藝術遺產,深入研究他的書法美學不僅有利于我們全面認識、評價中國書法史,感受他的書法美、人格美、氣度美,而且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傳承中國書法藝術。
[1]錢鐘書.管錐編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9.
[2]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本漢.歷代書法論文選[M].
[3]黃賓虹文集·書信集[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9.42.
[4]姜壽田.中國書法批評史[M].北京:中國美院出版社,1997.
(責任編輯:馬銀華)
J292.1
A
1008—6153(2013)04—0163—03
2013-06-17
李囡楠(1983-),女,山東東平人,濟南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藝術教育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