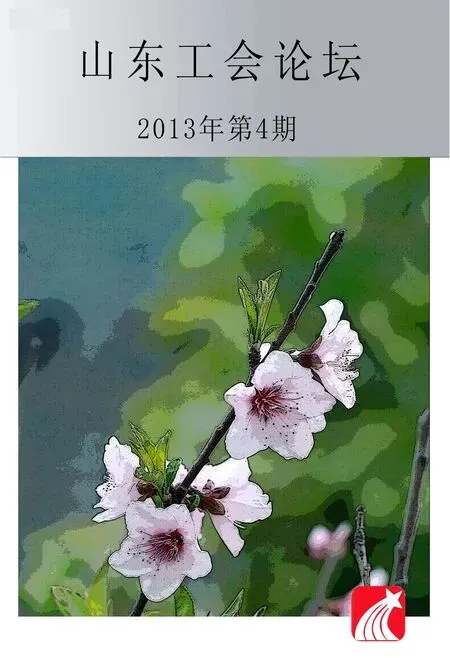放逐與守望
——新世紀以來小說中知識分子整體形象分析
趙紀娜
(山東管理學院,山東濟南250100)
放逐與守望
——新世紀以來小說中知識分子整體形象分析
趙紀娜
(山東管理學院,山東濟南250100)
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受到社會轉型的深刻影響,中國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本文按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不同劃分為四種類型:即權力的狂熱追逐者形象、金錢的盲目追求者形象、信仰失落的自我放逐者形象和理想的堅守者形象,從而全面分析這一特殊群體。
知識分子形象;社會轉型;精神追求
中國知識分子素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化傳統。知識分子的前身在古代社會被稱作“士”,他們具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責任感與正義感,在他們身上展現的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觀念。
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特殊群體,有著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因而一直以來成為作家重點塑造的形象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崛起,我國社會進入到了一個重大的轉型期。尤其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了政治、文化等社會各方面的變遷。在這一社會背景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困境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他們或適應,或惶惑,或忍受,或墮落,呈現出多樣化的整體形象。分析新世紀以來我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類型:
一、權力的狂熱追逐者形象
古代“士”具有天生的清高、骨氣與正義,他們胸懷天下,嚴以律己。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及其弟子為代表的儒家成員就是士階層的典型代表。在世人眼里,知識分子是為真理而生的,不畏權貴,不畏金錢。有人稱知識分子是“良知和公正的堅守者、歷史和社會的批判者、思想和精神的開拓者、真理和智慧的傳播者……權力和邪惡的囚禁者。”[1]無論在普通百姓眼里,還是知識分子自己的信仰追求中,知識分子似乎是正義、公平、真理、骨氣的代言人。但在當下社會中,由于理想的失落、生活的無奈、內心的壓抑等各種因素,迫使知識分子不得不放下清高,低下高昂的頭顱,轉化為一種對權力的狂熱追求,把無職無權的無奈變為對名利的追逐與獲取。在描寫知識分子的小說中,我們經常會看到這些場景。
在閻真創作的小說《滄浪之水》中,有著良好家教背景的主人公池大為和其父親一樣,正直,有良知。他自身好學努力,在學業上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工作不錯,被分到了省衛生廳。初涉官場的他固守著傳統知識分子的價值觀,不會靈活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不注重揣摩領導所思所想,任憑自己敢說敢當。小說中的馬廳長、晏老師、丁小槐、小莫等表面上對他尊敬,卻處處為難他。甚至,學歷比他差很多的丁小槐不久在仕途上也超過了他。他卻一直堅持“我不能欺騙自己,也無法說服自己”。兒子出生、生病住院、上幼兒園等無不刺激著池大為,使他一次次懷疑自己過去的做法,懷疑自己憤世嫉俗、耿直剛強的知識分子性格。后來,他徹底向現實社會妥協,妥協后的自己卻痛苦不堪、備受煎熬。他取得了世人認為的“成功”,獲得了一種虛擬的尊嚴和現實的利益,但是卻丟失了自己的靈魂和自我,變成了赤裸裸的物質至上主義者。從這部小說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知識分子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的蛻變。
史生榮創作的《感謝小姐》中的教務處老科長伍子清也是一個典型。他為了爭到副處長這一職位,不擇手段,并竭力拉攏教務處古處長和學校吳校長。后來,伍子清的“陰謀”得逞,大家都如愿以償。這背后正是池大為所說到的是“虛擬的尊嚴和真實的利益”這只無形的黑手在起作用。
在新世紀以來的許多小說中,我們看到許許多多為權力不擇手段的人物形象,他們是社會中知識分子的某種代表,不惜犧牲榮譽、尊嚴、正義這些本應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最起碼的準則,甚至是生命,成為權力的狂熱追逐者。
二、金錢的盲目追求者形象
“安貧樂道”是我國知識分子一種傳統的立身處世的人生哲學,他們不為五斗米折腰,過著世外桃源般的清淡生活,相比于豐厚的物質生活,他們更加注重在精神層面有較高的追求與境界。但進入新世紀以來,面對社會的大轉型,面對社會上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帶來的巨大沖擊,部分知識分子也受其浸染,把追求物質享受當成了他們的人生目標。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邱華棟的《教授》。小說主人公趙亮是一所大學里的經濟學教授。他留學歸來,獲得博士學位,成為著名的經濟學家。在小說中,趙亮被學生們稱為“叫獸”,主要是因為與教授諧音,意味著他是整天叫喚的野獸——在課堂上、電視上、研討會上叫著,他游刃有余地穿梭于課堂、電視、研討會,奔波于政界、商界和學術界。他習慣開著自己那輛漂亮的銀色寶馬轎車,出入各種高檔場所,他住大房子,養玉鳥、蟒蛇等,過著令普通人仰慕的奢華生活。小說在描述這種讓外人艷羨不已的生活的同時,更是以當下的社會現實和信息烘托和塑造了這一大學教授的新知識分子形象。進入新世紀以來,像趙亮這種教授并非個例,他的出現也并非偶然,和這一時期社會大變革中出現的種種弊端密不可分。在作者邱華棟看來,趙亮的悲劇意義在于,在一個欲望和物質的時代里,他無法把握內心的平衡和自己生活的重點。[2]
作家劉士釗創作的《物質生活》中,主人公韓若東是一個被稱為“詩歌瘋子”的天才詩人。他愛上恩師的女兒喬其,而老師卻不愿意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怕女兒受物質之苦。韓若東陷入了無愛境地,開始了物質世界里的追逐、打拼。后來,他終于與喬其結婚,并不顧一切地攫取財富,最終被金錢變成了魔鬼。物質生活的過度追求像一柄利劍,刺穿了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毀了他的一生。
通過這些知識分子形象,我們更加看清了這個時代的喧囂和痛苦、熱鬧和寂寞、繁華和貧困、富足和匱乏,以及物質世界對心靈的煎熬和擠壓。
三、信仰失落的自我放逐者形象
知識分子往往被人們認為是精神的向導,在現實生活中充當先知先覺的角色。他們有自己的信念、理想和思想,他們傳經布道,堅守道義,維護正義。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社會急劇變革,知識分子無論是生存狀態,還是精神狀況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困惑,昔日的理想主義熱情和烏托邦精神早已被現實所埋沒,坐而論道的冷靜與潛心問學的從容也已漸成追憶。在這種狀況下,一些知識分子耐不住寂寞,放棄了理想,成了任由信仰飄泊失落的自我放逐者。
如陳應松在《魂不守舍》中塑造的主人公王開,是一名文學碩士、著名編輯、記者。但他專事于尋求性愛刺激,在幾個女人之間周旋。在這種性愛的快感面前,他的身體與良知都受到審視,在金錢與肉欲面前,他的精神萎頓、頹廢,以至消解,這是知識分子迷失自我的生動刻畫,發人深思。除此之外,一些小說還從學術腐敗方面來著重表現知識分子的道德下滑。如南翔的《碩士點》、《博士點》:為評上碩士點、博士點,教授們想盡一切辦法,違背大學精神去媚俗。青禾的《夏教授的學術生涯》中的夏時令為評副教授發表妻子的文章冒充,為申報碩士點利用女助手典娜的關系。曹征路的《大學詩》中,刻畫了廖星凱們為了“申博”利用師生舊故在評委要人之間奔走游說,請客送禮,阿諛奉承,卑躬屈膝,甚至花大價錢請來中介公司進行市場操作。“大家都這樣做,你不遵循這類潛規則,可能會遭封殺。”《所謂教授》中劉安定發表文章要署上朱校長的名字。《角力》描寫有的學院縱容學術腐敗,有的系公然集體購買版面發文章,有的系領導私自改動教學立項主持人,嚴重干擾職稱評定的公正性。[3]
在社會、家庭乃至個人多重因素的影響下,這些小說家筆下的知識分子都不同程度地陷入肉體與道德的放縱中。他們曾經被譽為社會道德的看護者和守候人,在時代無情的壓榨和感染下卻走向反面。欲望的惡性膨脹,使他們變成了徹底的色情狂、性玩弄者、婚姻和家庭的背叛者,這一切最終帶來的是失敗,是幻滅,是悲劇。
四、理想的堅守者形象
“窮且益堅,不墮青云之志”。知識分子中也不乏道德守望者,不管外界多么紛繁復雜,他們都“不合時宜”地堅守道德底線,決不同流合污。
如曹征路的《大學詩》中歷史系副教授馬同吾便是一位性情中人,因講真話遭解聘,在衛生間用剃刀把自己的睪丸割了下來。《漩渦》中作家塑造的靳老先生,堅守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品格,孜孜不倦,傳道授業解惑,不誤人子弟,不出賣靈魂,踏實做人,認真教書,維護著教育的神圣尊嚴,守望著自己的精神“麥田”。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中能夠反映這一主題的作品還有許多。《桃李》中藍教授的保守顯然沒有讓藍娜成為一個傳統的女孩,她身上洋溢的青春氣息、對現實生活的熱愛以及對純潔的愛和美的追求都是當代女大學生獨特的精神寶庫。對于愛情和婚姻她有自己絕對獨立的觀念。她需要錢,但并不放棄自己的尊嚴。格非在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創作中,不斷描繪出知識分子獨有的烏托邦理想。他2004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力作、“人面桃花”三部曲之一——《人面桃花》,以及2007年1月出版的“人面桃花”三部曲之二——《山河入夢》無不表現出知識分子獨有的那份執著。
作家許春樵的中篇小說《知識分子》,敘述主人公鄭凡在碩士畢業后,逃離了大都市上海,扛著一個蛇皮口袋到了K城。他的到來一方面是懷著古代文學和現代夢想,另一方面是與網名叫“難民收容所”的約定。在K城,他的生活壓力相比于上海小了很多,但是在這里他的知識分子尊嚴卻受到物質的考驗。同學黃杉被女大款包養,舒懷的女友因為物質需求而背叛,舒懷因失戀殺人被槍斃。這些都讓鄭凡體會到了“男人掙不到錢,在家里老婆面前都沒有自尊!”的悲哀。他放下了尊嚴,拼命兼職掙錢,但在這種情況下,他一直堅守自己的底線,讓人欣慰的是在一個物質至上的環境中,他卻寧愿辛辛苦苦掙家教輔導的血汗錢,也不低下頭為曾經犯過強奸罪的老板寫一部傳記;即使自己的生活窮苦潦倒,卻在鄉親病重時,從自己積攢的辛苦錢中拿出兩萬元來救人;當要偷他錢財的小偷受傷時,他依然用老父親為他買房子的錢,為小偷墊付醫藥費和住院費。
在這些小說中,我們看到一個個有著錚錚鐵骨和意志不屈的知識分子,不為物質改變自己的情操,從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物質時代正直知識分子情懷的堅守者。
可以欣慰的是,雖然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面臨著真實而又殘酷的生存環境,他們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經受著巨大的痛苦和掙扎,但在一系列文學作品中,我們仍能見到在金錢和權力面前,繼續堅守知識分子人格、操守和信仰的藝術形象。他們沒有隨波逐流,沒有喪失斗志,相反,以一種“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高尚情操向世人展示知識分子的崇高氣節,因而令人敬仰和尊重。
[1]蘇中杰.知識分子天職:囚禁權力和邪惡[J].雜文月刊(選刊版),2008(06):18.
[2]卜昌偉.小說《教授》:再現大學教授聲色犬馬生活[N].京華時報,2008-11-10.
[3]張紅艷.困境突圍中的悖論[D].濟南:山東大學,2007.
(責任編輯:馬銀華)
本文為山東省高等學校人文社科研究計劃項目《新世紀以來小說中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形象解讀》(項目編號J10WD5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I207.42
A
1008—6153(2013)04—0166—02
2013-05-15
趙紀娜(1983-),女,山東沂水人,文學碩士,山東管理學院人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