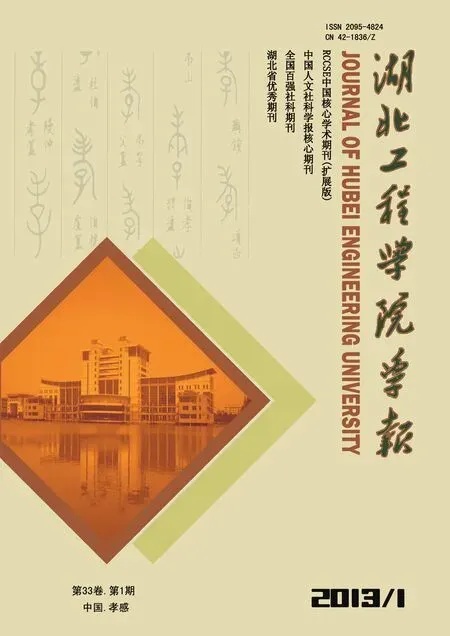老子“不尚賢”與墨子“尚賢”的比較及其意義
杜高琴, 徐永安
(湖北汽車工業學院 人文社科系,湖北 十堰 442002)
老子生活的春秋時代,雖然“禮崩樂壞”,但是各個大小諸侯國為了鞏固和擴充自己的利益,紛紛招賢納士,卻也開創了歷史上第一個人才濟濟、各逞其能且自由流動的局面,相應的用人理論也紛紛出爐,以墨子的“尚賢”論為其中的代表。《墨子·尚賢》曰:“故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他提出了“進賢”、“事能”的主張,并將“尚賢”視為“為政之本”。[1]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歷史上的“盛世”大都與注重選拔使用賢才有關。中國人早已形成了治理國家必須倚重賢能的理念,因而同時代的道家創立人老子提出的“不尚賢”的相反主張,似乎顯得不入潮流,不少學者對其多有詬病。比如任繼愈先生認為:“老子反對當時流行的尚賢主張,反對新事物。他主張愚民,認為人民的頭腦越簡單越便于被統治。這和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是一致的。”[2]有的研究者認為:“《老子》是以批判者的姿態,戴著斜視鏡去看問題的。它固然發現了別人(法治者、尚賢者)所沒有發現的問題。但令人遺憾的是,它由此徹底全面地否定了法治和尚賢本身。為了免去‘盜賊多有’,索性根除法治,為使民不爭,干脆不尚賢。這是因噎廢食的消極辦法。”[3]這樣的評價未必接近老子的本意。我們通過比較老子的“不尚賢”與墨子的“尚賢”予以說明。
一、老子的“不尚賢” 與墨子的“尚賢”在對象上是一致的
墨子認為賢人必須“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即賢人必須具備三個條件:道德高尚、能說會道、學識淵博,其中“德行”被排在第一。老子的《道德經》講的就是自然與社會、人倫的道德,通觀《道德經》,多處論及圣人之道,也論及普通人的為人處事之道,無不是以高尚的道德為第一要旨,配以簡潔而有效的處事方法。與墨子賢的內涵相比,除了“辯乎言談”之外(老子講究“行不言之教”),其他內涵沒有沖突,且老子的賢在道德層面顯然更加高于墨子的賢,這就是比之于天道的道德——“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天道對萬物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故治國者或圣人對民眾也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老子的“不尚賢”斷不是“尚不賢”。
二、老子的“不尚賢” 與墨子的“尚賢”在目標上是一致的
墨子尚賢是為了幫助“今者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漢書·藝文志》說:“道家者蓋流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面南之術也。”[4]“君人面南之術”,當然也是為了幫助君王達成治理好天下之目的。從《道德經》的謀篇結構亦可見其立論以治國為首要:其首章講天地之“道”的深奧玄妙,但本質上可以“無”與“有”的辯證關系把握;第二章則推及“道”的現實表現——美丑、善惡、大小、長短等是相對存在的,圣人應該明白這個道理,“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提出“無為”思想;循著“無為”思想,在第三章提出了“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的“使民”方略,亦即治理國家的“圣人之治”, “不尚賢”則處于諸治國方略之首。
三、二者關于賢才的來源有共同之處,但表述的重點不同
墨子看待賢才,打破了身份等級的限制,“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這顯然是一個歷史的進步,順應了時代與社會的發展要求。老子的言論,也包含了這種思想,只是沒有墨子直接與激進。老子筆下的圣人不是生來就有的,而是向天地之道學習的結果——“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同時,老子也提出了普世性的處世之道,“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這些同樣是天地之道在人類社會的表現,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通過不斷地學習自然的道德精神(《道德經》充滿了這種學習的比擬描述),百姓之中可以產生賢才,賢才進而可以成為圣人。因此,說老子的思想否定尚賢,想實行愚民政策,是不符合他的哲學思考的。只是老子更加注重民眾罷了——畢竟在任何時代,能成為賢才、圣人的是少數,治理好其他大多數人,才是保證社會穩定的基礎。更何況,那個時代的語言中,“民”并不特指普通老百姓,而是一個與“官”相對的寬泛所指,相當于現代語的“人們”,或者是“人類”。
四、二者的差別在于“尚賢”的方法和程度
墨子強調對待賢才要“富之,貴之,敬之,譽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即賢才通過獲得財富、地位、榮譽、權力,讓其他的人都看見、知道成為賢才的好處與權力,并且產生“敬”、“信”、“畏”的認知心理,從而使得國家安定。而《道德經》中,老子提出圣人采取“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的方式治理好天下,讓民眾在感受不到,也不會想到追求過分的物質利益和欲望,不存在對統治者畏懼的情況下,淳樸自然地生產、生活。“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的自然就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此則天下太平之象。“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當百姓們沒有心計沒有欲望(民風淳樸),那么少數自作聰明的人也就不敢放縱自己的欲望了,從而達到“為無為,則無不治”的效果。
但是老子似乎沒有說到賢才的待遇,不過《道德經》的有些內容包含了這個問題:“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圣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明白圣人也有正當合理的利益。不過與墨子不同的是,在他看來,既然是賢才,其具備的道德境界就不會先講“私”,而是遵循天地之道,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甚至用不著思考“私”的事情,因為賢才得到應有的待遇是毫無疑問的。比起墨子,在如何對待賢才、賢才如何影響百姓與治理好天下這些問題上,老子的思維顯示了更高的道德水準。
五、從字義到語義看老子“不尚賢”的本質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從字義上來看老子“不尚賢”的完整意思。實際上,“尚”字含“增加,超出”之義,古文中如《孟子·公孫丑(下)》中,有“今天下地丑德齊,莫能相尚……”[5],現今所言“時尚”等亦有其痕跡。結合老子的思想,因此“不尚賢”就是“不突出賢才”,“不標榜賢才”——讓賢才順其自然地發揮他的作用,不要過多地關注他,就和其他人一樣,都是做自己該做的事。可見老子并不反對“尚賢”(如任繼愈先生所認為的“不推重有才干的人”),而是提醒統治者,過分突出賢才,讓人看到的是賢才得到的富貴榮祿,從而引起利欲之心,并不擇手段去爭奪,會帶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與矛盾,反而背離了“尚賢”的初衷。畢竟,使民眾都無爭名奪利之心,都能致力于自己的生產與生活,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這要比侯王得到幾個賢才重要得多。這也是老子“無為而為”思想在治國與用人領域中的表現。
老子的“不尚賢”表現出了對人性惡的深刻洞察力與防范之心。老子的深刻除了源于超出他人的豐富學識、獨特哲學思辨力之外,還與他史官的身份有關——他可以在一國的朝堂之上,記錄國家大事,冷眼旁觀世事人情,體悟治國、用人的道理,從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并推及天下。這樣的政治實踐活動是其他人望塵莫及的。
《道德經》崇尚的“無為”、“自然”、“不爭”,既是天地之道,也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故而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老子的“不尚賢”要比墨子的觀點更具有哲學思維的深度。老子的“不尚賢”是“無為而為”的“尚賢”,是“自然而然”的“尚賢”,是“為而不爭”的“尚賢”,是“尚賢”的最高境界。
六、老子“不尚賢”對社會和諧的意義
現代心理學的研究證明老子的“不尚賢”思想的科學。心理學家把小孩子分成甲乙兩組,甲組小孩每次幫人揀東西之后,都會得到一個小玩具;乙組小孩幫人揀東西之后,卻沒有什么獎勵。過了一段時間,再取消甲組小孩的獎勵,甲組小孩就會不再愿意無償幫助他人;而乙組的小孩卻依然出于天性(自然)樂于幫助別人。這就是“過度尚賢”的壞處。
當下我們生活的時代,毫無疑問是一個重視人才的“尚賢”時代,但是也存在“過度尚賢”的問題。作為制度性問題,它存在于我們的應試教育制度中,并滲透到家庭教育、社會的價值認知等多個層面。
上世紀70年代末恢復高考制度,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事業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急需的各種人才,中國和平崛起三十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教育在培育輸送人才方面可謂功不可沒。但是,應試教育的各種弊端也隨著時間的積累而日益凸顯,并對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還是“為振興中華而讀書”的話,那么這種積極的理想主義精神色彩現在所剩幾何?在學歷高低基本上劃分出人的社會地位和利益等級的現實下(“過度尚賢”),追求學歷,恐怕早已淪為以獲取最大利益為目的的手段了(許多人正是看到“賢才”得到的利益),因此,為了考上大學,有多少父母不是從小學就開始,全力關注孩子的成績和分數,而忽視了綜合素質、道德修養和人生理想的培養。只要有可能,就是花上更多的錢,也要擠上大學的“末班車”,乃至傾盡家財也要送孩子出國留學。還有多少人愿意進入技校、職校學習一門謀生的技能,去普通的勞動崗位實現人生價值呢?做一個普通的勞動者不再是一種價值觀,而是一種不得已的無奈選擇。當一個幾歲的孩子說出自己長大了的理想是要當個公交車司機時,立即換來媽媽的一記耳光和“沒出息”的責罵。這一事件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它所折射的正是社會存在的急功近利、一夜暴富、成名成星的價值取向。當我們失去了對勞動的肯定,對普通勞動者地位的尊重,社會毫無疑問會潛藏巨大的危險。而當下社會存在的價值觀失衡與扭曲,與“過度尚賢”的價值導向有關。
“過度尚賢”也對我們的干部考核制度產生負面影響。政府在選拔、任用、考核干部時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是新時期干部工作的根本指導方針,它兼顧了德、才、能,即“賢”的人才標準。但當以學歷為參照,限定某種學歷只能升遷到某級職位成為潛規則時,就會導致許多本可以安心做好本職工作的人,不得不分心分神謀求高學歷。于是,也催生了官場中以權力、金錢與教育資源相交換的“學歷腐敗”。
“過度尚賢”催生的功利傾向在高校也有表現。我國的論文產量世界第一,但創新性不足,引用率很低,甚至出現了某些高校領導、教授抄襲、剽竊他人學術成果的事件,在國際上造成惡劣影響。高校的人才流動,博士占主流,相比引進碩士生,博士的待遇包括一些過度利益,從而也引發了一些人的名利之心,出現了獲得博士學位后向校方“要官”,否則就跳槽走人的現象。為了謀利有人造假學歷——2012年媒體披露的廈門大學外聘教授博士文憑造假事件表明:造假者實際上是有科研、學術能力的,并且“工作是認真負責的”。但如果她沒有這個假博士文憑,就不可能進入“人才”行列,獲得廈大講座教授以及后來的全職教授的職位。[6]我們肯定不能容忍造假這種不道德的行為,但同時更堪憂的是我們的人才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
正因如此,老子的“不尚賢”思想對調節、化解“過度尚賢”所積累的問題,對我們從用人制度方面進行反腐倡廉、建設和諧社會有著積極的啟示意義,而從根本上改變應試教育制度具有首要意義。從各級義務教育開始,取消學校分級、班級分級,逐步消除不同區域間學校在資金、師資、待遇等資源配置方面的差異,改變以升學率為核心的教學體制和資源配置,真正體現教育民主、教育平等,真正形成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培養模式。倡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多元化的人才觀,推廣“勞動光榮”的基本人生價值觀,使我們的制度既能激發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又使人們不爭不貪,安身立命,呈現自然、和諧,充滿創造活力的社會圖景。
[參 考 文 獻]
[1] 孫詒讓.墨子閑詁[M]//諸子集成:第4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25-29.
[2] 任繼愈.老子新譯[M].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66.
[3] 宋錦銹.《老子》的用人思想[J].錦州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4] 漢書[M]//二十五史: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94:166.
[5] 焦循.孟子正義[M]//諸子集成:第1冊.上海:上海書店,1991:154.
[6] 佘靜.廈門大學造假女教師遭辭退[N].廈門日報,2012-07-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