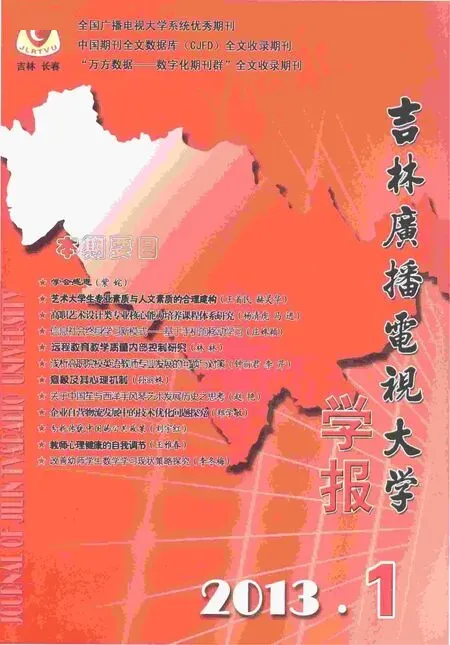詞語訓釋在古代漢語文選課堂中的有效教學
戴曉園
(徐州中等專業學校,江蘇 徐州 221000)
引言
古代漢語是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必修課和工具課,這門課主要以古代書面語作為教學工作的重點內容,而教學目的,則是為了培養該專業的學生正確的閱讀和理解古代漢語文言書籍。
古代漢語的教學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一個是通論,另一個是文選。其中,通論主要是指和語言文字有關的理論知識,它主要講授古書、音韻、詞匯、語法、文字等基本內容知識;而文選的內容,則將先秦的典范作品作為主要的授課內容。一般情況下,通論和文選的學期授課比例是1:1,有時候,通論的授課時長會略高于文選,但絕大多數情況下,通論和文選的授課課時不會產生太大的差別。從通論和文選的課時比例可以看出,文選在古代漢語教學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文選中,又以詞匯最為重要,這是由于詞匯是一個民族語言文化長期發展的產物,它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歷程及民族特點,因而,對于中國古代語言詞匯的學習和研究,能夠很好的把握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中所產生出的政治、經濟、文化精髓[1-3]。
在漫長詞匯發展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出古今異義詞,給古書的閱讀和古文獻的考究,帶來一定的困擾,因而,研究文選中的古語訓釋,是十分必要的。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牢牢把握詞語訓釋的重要性,并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引導學生對于文選中的詞語進行正確的訓釋。
一、利用古文獻閱讀,開展詞語訓釋的教學工作
古代漢語的學習,一個重要點就是對于古代詞匯的學習,只有掌握足夠多的古代漢語詞匯量,才能夠達到研究古代漢語文選的目的。詞語訓釋是古代漢語教學工作的重點,做好詞語訓釋教學工作,可以采用閱讀古代文獻的方式來完成。古代漢語的語言,大部分儲存在經典的文獻資料中,因而,對于歷代經典文獻資料進行研讀,關注其中的整理、注釋內容,能夠有效的幫助學生獲得較為豐富的詞匯知識。因而,可以引導學生對于經典的古文獻資料進行閱讀,在閱讀的過程中,幫助學生較好的完成詞語訓釋的學習。
二、利用學習評價,開展詞語訓釋的教學工作
一門課程的學習,有開始、經過、結束等多個過程,古代漢語文選也要經歷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在古代漢語文選的教學過程中,可以采用學習評價的方式,對于教學過程和教學效果進行測評,進而了解詞語訓釋的學習質量。
美國著名學者魯姆提出了學習評價理論,將學習評價理論劃分為診斷性評價、形成性評價、終結性評價等三個評價類型。古代漢語文選的教學工作,可以采用學習評價的方式,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診斷性評價,應用在古代漢語文選教學工作中,可以包括以下內容:對于詞語在文中選擇的意義把握、對于原有的知識儲備的情況把握,檢測原有的知識儲備能否適用于新的知識的學習、能否進行正確的詞語訓釋。
形成性評價,主要應用在教學過程中,這一評價可以為學生提供較有意義的信息,并能夠結合所存在的問題,做出及時的調整,以達到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強化教學效果的目的。
終結性評價,主要應用于課程結束之后。主要是對于整個課堂教學結果,進行較為客觀的總結和評價,以檢測教學目標是否達到。終結性評價,對于學生而言,是一個舊的自我學習過程的終結,同時也是新的學習過程的開始。
三、利用訓詁學知識,開展詞語訓釋的教學工作
古書之所以難度,就在于古書中存在著諸多的古今異義詞和難解詞。古今詞匯的發展變化,給古籍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古書如果不經過詞語訓釋,是很難達到通曉其義的目的。
1.牢牢掌握訓詁學常用術語
訓詁學中,有專門的術語,與其他的語言形成一定的區別。每一個術語都有固定的用法,例如,對文、散文、析言、渾言、讀若、言、謂、曰等,只有形成對于這些術語的把握,才能夠較好的把握詞匯的意義。
鳥部:“ 鳥,長尾禽總名也”。 段注:“ 短尾名佳, 長尾名鳥, 析言則然, 渾言則不別也。”又《說文·走部》中:“走,趨也。”段注:“《釋名》:‘徐行曰步, 疾行曰趨, 疾趨曰走。’此析言之。許渾言不別也。”《說文》:“ 革, 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段注:“ 皮與革二字,對文則分別, 如秋斂皮、冬斂革是也。”散文則通用, 如《司裘》之“ 皮車”即革路,《詩·羔羊》:“‘革猶皮也’是也。”
2.將古書用字和以聲索義與推求語源相結合
以聲索義,就是根據聲音,來推斷字的意義,而主要的推斷對象就是假借字和同源字。之所以對于假借字和同源字采用以聲索義的推斷方式,是由于這兩種字體,都是以聲音作為主要的聯系紐帶,因而,可以利用聲音,對于它們的詞義做出推斷。在文字的發展過程中,不斷的產生出新的字、詞;往往新詞是在舊詞的基礎之上產生的,一個舊詞的詞義不斷的發生引申變化,從而分化而形成一個個的新詞,這些新詞都出于同一個母體,因而,若干的新詞之間,具有語音相近或者相同、意義相通、而字形不同的特點,從而構成了具有一定的可追溯性的新詞。同源詞是指出于同一個詞族的詞語,這些同源詞之間具有聲音相同或者相近的特點,因而,可以依據這個對于同源詞在聲音一定的基礎上,進行意義的推定,從而形成對于新詞的詞義的重新界定。基于這種分析,可以使用以聲索義,并結合古書用字和推求語源的方式,來達到認識古字的目的[4-5]。
例如,對于假借字的聲訓的研究,一般是采用本字解釋借字。《荀子·天論》:“老子有見于詘,無見于信。”楊倞注:“信讀為伸。”《漢書·賈誼傳》:“非亶倒縣而已。”顏師古注:“亶讀曰但。”《漢書·晁借傳》:“ 風雨罷勞, 饑渴不困。”顏師古注:“罷讀曰疲。”以上三例中,“信”、“亶”、“ 罷”為借字,而“伸”、“ 但”、“ 疲”為本字。
又例如,“休”在古代的意思是“喜,美”的意思。《詩豳風破斧》:“ 哀我人斯, 亦孔之休。”鄭箋:“ 休者, 休休然。”。《詩小雅菁菁者莪》:“ 既見君子, 我心則休。”《國語周語》:“ 為晉休戚。”韋昭注:“ 休,喜也。”毛傳:“休,美也。”清代學者王引之對于“休”的解釋是:“休休即欣欣, 語之轉也。”對于“休”的古代意義的理解,可以通過對于讀音的追源性解讀,而獲得,“休”的語源是“欣”,從而加深了人們對于“休”的古義的理解。
3.將語境與以形索義相結合
在訓詁學中,有“形訓”一詞,就是通過字形來推斷詞的意義,也就是以形索義。會意字、指事字、象形字之間,都有著之間的聯系。因而,通過字形,能夠了解字所記錄的詞素或者是詞的意思。對于這類字,形訓的作用體現出說明、揭示字的本義。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雖及胡耇, 獲則取之, 何有於二毛?”句中“獲則取之”一般容易理解為“抓住了就俘虜他”,就很容易將“獲”與“取”看做是同義詞,用的是它們的常用義,似乎很容易理解;但二者之間,采用了連詞“則”,表示遞進的關系,與古代漢語的同義詞連用習慣不相符合。因而,采用以形索義的方式,來對于“取”和“獲”的確切意思進行探究。“獲”根據古代形體字的解釋,是“獵得禽獸”,引申為“得到,俘獲”的意思;而“取”,在古義中,是“割去敵人的耳朵,以降服敵人”,割去敵人的耳朵,是為了記功。因而,在對于“獲”和“取”的本義理解之后,就很容易對于這句古語,做出新的解釋,“對于年紀特別大的敵人, 抓住了( 如果不降服) , 就割下他們的耳朵”。
但有時,在文選中,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其所使用的詞語,并不是使用其本義,而是采用了該詞的引申意義,并且,這種情況大量存在。針對這種情況,就要采用以形索義的方式來確定具體的語義,在多種語義并存的前提下,可以采用以形索義與語境共用的方式,來增加語義的準確性。
以形索義,所篩選的是詞語的本義,對于詞的本義的了解,可以更好的掌握詞的引申意義,從而為增加詞的意義的準確性判斷提供保障。另外,對于詞的本義的探尋,也可以甄別出于本義無關的其他的假借義。
當然,詞的本義的探尋,并不是簡單的事情,可以依靠其他的輔助性的手法,例如對于字形的綜合應用,從而在文選中,較好的把握詞的本義;也可以根據詞在文選中的具體的語言環境,挖掘出詞在語句中的意義[6]。
結語
總之,古代漢語的教學工作中,詞語訓釋是掌握古今異義詞的重要方式,通過對于詞語訓釋的學習,能夠有效的掌握古代漢語中的各種異讀詞語,從而獲得較好的古代漢語學知識。對于詞語訓釋的教學,可以通過古文獻閱讀、學習評價、訓詁學知識等多種方式,達到既定的教學目的,讓學生能夠有效的掌握古代漢語的基礎知識,完成既定的教學目標。
[1]何書.試論古漢語動詞詞義裂變式引申[J].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07,(05).
[2]郭在貽.訓詁學[M].北京:中華書局,2005.
[3]洪誠.洪誠文集[A].訓詁學[C].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4]周大璞.訓詁學初稿(修訂版)[M].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5]許威漢.訓詁學導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6]蘇寶榮,武建宇.訓詁學[M].北京:語文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