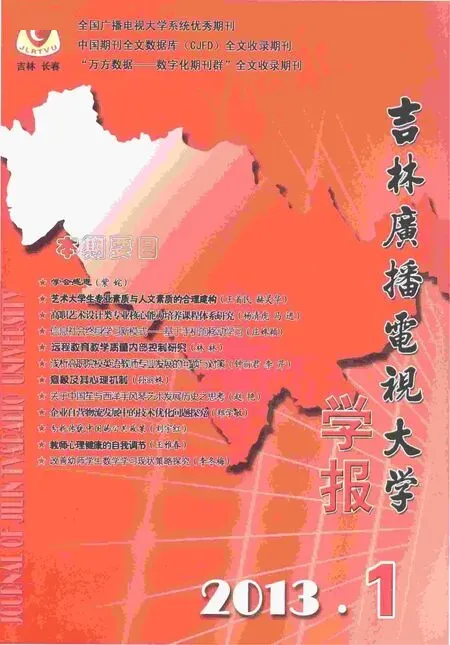踵事增華:淺析當代二人轉藝術的文化發展
仵宏慧
(吉林師范大學博達學院,吉林四平 136000)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形成各色地域文化。二人轉藝術便是依傍在東北這片白山黑水下孕育而生的一門傳統地方戲曲藝術。這種帶有濃郁地域文化色彩的民間藝術,在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后,時至今日已呈現出其獨有的藝術魅力,風靡大江南北。二人轉以其風趣幽默的語言、靈活的藝術表現形式,熱熱鬧鬧的走進了百姓生活,為廣大北方群眾所喜聞樂見。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環境的改變,對公共娛樂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大,傳統單一的表演模式已經不能滿足觀眾的需求,二人轉的創新改革勢在必行;同時,隨著越來越多的表演藝術者投身于這項地方戲曲事業中,二人轉表演人才層出不窮、新人輩出,為二人轉藝術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青年表演藝術者們為二人轉注入了很多時下的流行元素,從心理上讓中青年觀眾產生了認同感和趨同性,給在生活壓力逐漸增大的當今人們以精神上的紓解,而使得二人轉也悄然地開始成為年輕人釋放壓力、緩解情緒的一種娛樂方式。本文主要從解讀當今新型綜藝娛樂二人轉入手,剖析當代二人轉藝術的文化轉型成因,闡釋當下流行的“娛樂型”二人轉迎合廣大欣賞者的受眾心理,進而發掘整理二人轉藝術的文化特色和藝術魅力,使其在中國地方藝苑這片沃土上更加茁壯成長,開出最絢爛的花朵。
一、與時俱進的二人轉——迎合觀眾與市場需求的發展之路
眾所周知,東北地廣人稀,知識文化傳播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二人轉以其走鄉串鎮的游走表演形式,在產生之初便肩負起了鄉井道德傳播的重責。樸實的關東人,勤勞善良的本性,質樸真誠的生活,以及老鄉們相互幫扶的美德亦被編入二人轉的唱詞中,廣為流傳。在傳統的二人轉中隨處可見警示后人、寓教于樂的道德教育,既有如小帽《婆媳頂嘴》、《砍柴郎》等在插科打諢、風趣幽默間闡釋了質樸的道德倫理觀念,也有正劇 《包公斷案》、《馬前潑水》等借戲說歷史來警喻世人。新中國建立后,二人轉藝術延續傳統道德教化傳播作用,并融合了新時期的政治文化精神,大批創新曲目層出不窮,如表現農村生產合作社的 《豐收橋》、《柳春桃》,擁軍優屬劇目 《給軍屬拜年》等,更成為帶有鄉土氣息的社會文化傳聲機。
而今,隨著社會生活環境的改變,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大,傳統單一的地方戲二人轉已經不能滿足觀眾的欣賞要求,特別是八零后、九零后的年輕觀眾群的加入,更對二人轉的表演內容有了新的要求。二人轉必須調整表演內容和表現方式方能夠符合現代觀眾的審美欣賞品味。故此,近年來的二人轉表演開始關注有悖社會公德、貽害社會的一些社會生活中的不良陋習,編撰曲目,在嬉笑怒罵中諷喻世人。如《愛情十等人》,雖然言語鄙陋、言語略顯粗俗,但卻將當今社會諸多陋習展現無遺,讓人們在娛樂之余看到沾染不良習氣、沉迷墮落之人的生活丑態,為人們敲響道德的警鐘。同時,二人轉藝術來源于鄉野,內容上自然是以貼近東北廣大農民的生活為主題。故此,在曲目的創作和編排上,以農村百姓喜聞樂見的身邊人、身邊事兒為題材,以風趣幽默且通俗易懂的語言,闡釋著莊戶人最質樸的生活哲理。如趙鏡和孫晶表演的《戲說人生》借由莊家人做事、交友等多方面生活側面入手,展現了發展中的東北農民在保有樸實憨厚的同時也學會了自我保護,帶有了警示世人的作用。
二人轉帶有濃厚的喜劇色彩,以詼諧幽默的戲謔語言、生活化的原生態演繹常常會逗引得觀眾捧腹大笑,并以其通俗易懂、雖俗亦美的大膽夸張的表達方式迎合了廣大群眾的審美情趣。近年來,這種藝術表演形式通過調整表現內容,擴大受眾群體,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時兼容并包,已逐步從農村步入城市,并受到了城市居民的喜愛。這源于二人轉的表演與時俱進的插入了許多當下流行元素,擴大欣賞人群,加入年輕人喜愛并關注的焦點內容,迎合接受者的欣賞口味,產生了類似于綜藝表演式的 “娛樂型二人轉”。同時,也崛起了一批新型的為觀眾所喜愛,乃至于達到了街頭巷尾無人不知的二人轉新星,如小沈陽、沈春陽、劉曉光、王小虎、王小利等。這些立足于本山文化傳媒集團的強大宣傳媒體之下,躥紅于大江南北的新時期 “轉星”,更擴大了二人轉的受眾群體。如轉星小沈陽的 《明星夢》,以及他與妻子沈春陽合作呈現的 《陽仔演笑會》產生了一些引領時尚的流行句:“想你想的一到白天我就睡不著覺啊!”、“我在三亞看雪景!”等已成為街頭巷尾的流行語。同時,異軍突起的本山傳媒集團旗下的劉老根大舞臺,更成為了傳播傳統二人轉的最佳平臺。如今的二人轉逐步走上了各大劇院和綜藝晚會,更成為辭歲迎新的春晚上不可或缺的新年視聽大餐。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二人轉的特有表演形式為“一旦一丑”搭配演出,丑角在二人轉中不僅僅是作為襯托旦角的輔助性角色,而是二人轉的靈魂和快樂源泉。丑角以詼諧幽默的說口、滑稽可笑的表演,給觀眾帶來極大的喜樂感。東北人特有的憨直的個性被夸張的演繹出來,“二虎巴登、口無遮攔”的一股腦兒展現出來,惹人發笑。這種輕松幽默的表演,緩解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壓力,在精神上得意隨性的釋放。同時,丑角往往會爆出一些稍顯粗俗,違反常規且帶有辱罵意味的言語。這些語言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為自我所壓抑的。誠然,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在一定意義上 “罵臟話”可是得到另類的宣泄,帶來別樣的心理情緒滿足。正如寧國利在《“污言穢語”二人轉》中指出的:“二人轉的臟話具有情感功能,無實際意義所指的臟話,主要目的是宣泄情感,比如憤怒、不滿、郁悶等。”①除此之外,二人轉也會呈現出一些性愛內容,表現出與道德倫理相左的反叛情緒,這些葷段子、黃笑話將“高尚的、崇高的、超我的東西降低到肉體層面。”②不僅彌補的是個別觀賞群的潛意識性空虛和性幻想欲望的滿足,更在一定程度上將很多平時生活中因道德束縛不敢呈現出來的“粗口”借由丑角的表演酣暢淋漓的宣泄出來,因為:“二人轉之所以一定要這樣做,目的很簡單就是在獲得一個暢所欲言的活潑形式并通過它消解等級、破除規則、從而達到狂歡效果。”③所以,二人轉中常常出現拿人調侃、辱罵他人的諷刺性話語,特別是當今的娛樂型二人轉中更是加入辱罵上司、調侃同事、錯拍馬屁的橋段,借由相互調侃和攻擊,使得觀眾在嬉笑之余,也釋放了自己心中積壓已久的負面情緒。特別是在表現卑鄙小人出盡洋相的時候,那帶有調侃味道的另類表演,更增加了幾許讓忠厚老實人可以大肆宣泄的氣悶情緒。二人轉在表現小人物們的日常生活,是老百姓們的家長里短,在其中不乏針砭社會陋習,積習已久的小惡被放大化。反思性雖弱,但足以平衡調整心態,對人的精神淺層發生作用。
二、異彩紛呈的二人轉——靈活多樣的表演
二人轉起源于民間的游走藝人表演,屬于曲藝中的走唱類,是以東北大秧歌為基礎,同時吸收了東北大鼓、蓮花落、評戲等多種曲調糅合而成,高亢嘹亮。故此,才有了“大秧歌打底,蓮花落鑲邊”的說法。同時,二人轉還加入了走場、身段、舞蹈,吸收了民間舞蹈,耍扇子、手絹等技巧,博采眾家之長,以舞蹈和歌唱敘述故事、表演人物,在嬉笑怒罵間演繹人生百態。
近年來,二人轉在表演形式上更是推陳出新,在保留傳統劇目的同時加入了很多流行表演元素,轉化為一種綜藝表演形態,即所謂的“說唱扮舞絕”樣樣精通,融說口、歌舞、小品、絕活等多種元素為一爐的更為符合多層次人群觀眾審美需求的綜藝表演會。具體而言,首先從表演形式上來看,不在局限于單純的對口唱,而是融入了很多小品味道表演穿插其中,同時融入流行音樂的演唱,并同時保留傳統的絕活項目,使得觀眾在欣賞時目不暇接,激起濃厚的觀賞興趣。其次,現下的二人轉表演者們往往非常注重和觀眾們的互動,或邀請觀眾直接參與,或直接向觀眾要掌聲,炒熱現場氣氛。如小沈陽的《陽仔演笑會》中,小沈陽的:“掌聲接,謝謝!”有效的承接了過場中的冷場現象。這種獨特的話語模式穿插于表演之間,直接打破了觀眾和讀者的“第四堵墻”,互動較多,氛圍活躍。自從安托萬于1903年4月1日 《巴黎評論》發表的 《布景漫談》中提出了“第四堵墻”的概念后,就從理論和實踐上要求戲劇舞臺表演藝術更關注觀眾的情感體驗。二人轉很好的處理了表演者與觀眾的互動,充分地利用各種表演手段有效打破了表演者與觀眾的“第四堵墻”,不僅觀眾可以走上了舞臺,二人轉表演者還會主動邀請觀眾參與互動游戲,調動了觀眾的參與性,表演中間穿插一些搞笑橋段,比如對明星的戲仿,引得觀眾發笑。這些表演形式,讓觀眾不僅僅作為舞臺之下的旁觀者,也可以參與到表演之中,給觀眾們帶來不同于傳統戲曲欣賞的別樣情感體驗。除此之外,當下的“娛樂型二人轉”常常會加入很多隨性的非敘事話語。如趙本山的:“這怎么整的!”劉流的:“那必須的。”已經成為這些轉星的標志性話語。這些看似是特定的二人轉表演者所獨有的口頭禪,往往會更加加深觀眾對表演者的表演作品的印象。同時,這種語言的放縱隨性,也打破了官方語言給觀眾帶來的拘謹感,正如巴赫金所言:“它們是一種暢所欲言的活潑形式。”④
通過表演手段和表演形式的轉變,本來就是有說有唱、載歌載舞,本來就有絕活展現的二人轉在增強小品般的說口和表演,融進現代舞的成份后,再加之增加雜耍武打動作,有效地避免一味地唱給觀眾帶來的審美疲勞,將觀眾的壓力釋放出來。特別是一些諷刺性的語言,甚至略帶人身攻擊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滿足欣賞者的趣味需求。從單純的扮丑以娛樂觀眾,到與觀眾互動,讓觀眾主動參與其中,不僅僅在掌聲中呈現這種互動形式,也以邀請觀眾參加進來的方式,拉近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距離,徹底打破了觀眾與表演者之間的距離。自此,我們看到二人轉為了求發展,經歷了多種形式的創新。如今的“娛樂型二人轉”不僅在曲目上,針對傳統的戲曲劇目而進行劇本和曲調再創作;同時,加入了小品、歌舞、笑話等多種新型表演形式,表演者多才多藝,說學逗唱樣樣精通,真正做到“二人一臺戲”,給觀眾帶來精彩紛呈的視聽享受。
二人轉本是一種極富地方特色的表演曲種,為廣大東北觀眾所喜聞樂見。時至今日,加入了新型元素的二人轉正朝向綜合型方向發展,應運而生的“娛樂型” 二人轉,更是在傳統二人轉的基礎上,與時俱進的加入了符合年輕人心理期待的流行元素和減壓元素,使得其適應人群逐漸擴大,為二人轉藝術的發展進一步開拓的市場。民間化的語言、生活化的表演,散發著濃郁鄉土氣息,無不讓觀眾耳目一新。新星二人轉節目更是新奇絕美,讓觀眾時而提心吊膽,時而捧腹大笑,盡享“娛樂二人轉”的獨特魅力。繼承老一輩二人轉藝人們的優秀傳統,逐漸摸索新經驗,在當下環境中,一步步走出屬于地方藝術的發展之路。正所謂:“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⑤民間戲曲藝術更需如此。”希望二人轉這個從東北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孕育出來的地方戲曲奇葩,能夠枝繁葉茂,花團錦簇盛放于中國戲曲的百花園中。
注釋:
①②③寧國利.“污言穢語”二人轉——淺析二人轉的“狂歡”語言[J].戲劇文學,2011,(3):64.
④[俄]巴赫金.李兆林,夏忠憲譯.拉伯雷研究[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3.
⑤(梁)蕭統 著.(唐)李善 注.《文選》.中華書局.2008:11.
[1][俄]巴赫金.拉伯雷研究 [M].李兆林、夏忠憲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奧]弗洛伊德.論創造力與無意識[M].孫愷祥譯.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
[3]吉林省地方戲曲研究室.二人轉傳統劇目匯編.第一輯.1980.
[4]孫惠柱.第四堵墻:戲劇的結構與解構 [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5](梁)蕭統.文選[M].(唐)李善注.中華書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