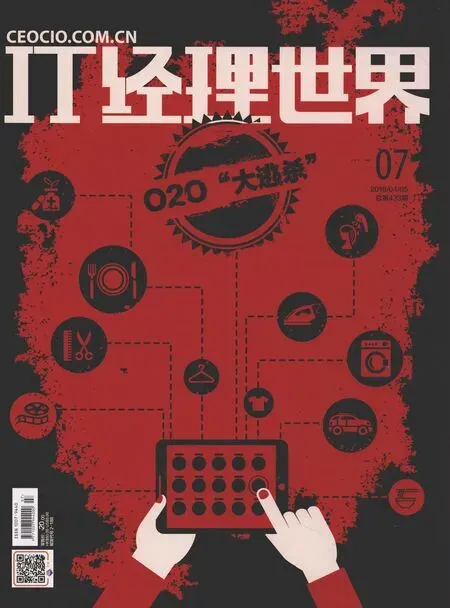“三分之一”定律
汪丁丁
楊格是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家,他研究“帶有隨機過程的博弈學習”,現在很有名,可能得到諾貝爾獎。不論如何,我要介紹的政治學,與他的研究密切相關。
想象一群人,他們使用兩種貨幣進行交易,金幣和銀幣。每一個人每天早晨出發之前,在口袋里裝一些貨幣,在扁擔里裝一些商品。游戲規則:每天從早到晚,每一個人只能攜帶一種貨幣,金幣或銀幣。而且規定不能以物易物。楊格的社會仿真,從最簡單的情形開始,他假設這群人最初是使用金幣的,但有一個極小的概率,例如,千分之一的概率,會有人攜帶銀幣(偶然的錯誤或故意要創新)。這樣的隨機性可能導致的后果是:這個偶然帶著銀幣出門的人遇到的大多是只有金幣的人,于是無法交易。那些帶著金幣的人晚上回到家里想起第二天要帶何種貨幣的問題,很自然,會有一些人從第二天開始帶銀幣出門。銀幣擴展的過程,開始的時候非常緩慢,可能需要等待兩年,才有第二個人偶然攜帶銀幣出門。但它引發的心理效應是可以累積的,直到某一天,相當多的人攜帶銀幣出門。然后,楊格發現,當攜帶銀幣的人數占了某一比例之后,有一種“雪崩效應”,人們開始迅速從金幣改為銀幣。這樣的實驗,他做了成百上千次,結論是:哪一種貨幣成為“本幣”,依賴于隨機沖擊的效應,或遲或早,當前流行的本幣一定會被“顛覆”。楊格這一發現,被稱為“輪流顛覆”定律。多年之后,大約2006年,《科學》雜志發表了哈佛大學一位年輕教授的報告,標題是“三分之一定律”。大致所言即楊格的輪流顛覆定律,只不過,更精確一些,他發現我們反復提及的那一“閾值”,通常就是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如果制度誘使壞人的數目增加到占總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則出現向壞人發展的雪崩效應。反之亦然。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直到中期,例如1997年以前,為城里人供應食品的農民不懂得造假或懂得但不愿意造假。為什么突然就有了這樣多的造假農民?楊格的“輪流顛覆”定律,在特定的制度里,“好人”越來越少(持有金幣的人越來越少)直到某一閾值,然后“壞人”迅速增加(雪崩效應),以致大多食品都是假冒偽劣的。當然,也可有另一方向的顛覆:最初敢于供應優質食品的農民,引發了一連串的偶然事件,直到某一閾值,然后“好人”突然增多,雪崩一樣地增多。輪流顛覆,楊格發表的數據表明,“輪流”是什么樣的周期?完全無法確定,沒有周期性,只有“隨機”顛覆。我們能預言的僅僅是:壞人占統治地位的時期不可能無限長,同樣,好人也不可能永遠占統治地位。甚至沒有好壞之分,只有制度與人性的協調與不協調之分。人是可以變壞的,如果制度迫使他壞。壞人也可以變好,如果制度迫使他好。現代人性的強烈可塑性,是現代社會理論的一項基本假設。所以,不要簡單認為一個人壞,于是就永遠壞。以及一個人好,就永遠好。正確的態度是考察與人互動著的制度的各種性質。
一個好孩子被送到一個壞幼兒園里,迅速可以變為壞孩子。這是從海外留學回國并且帶著孩子的中國家長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以致他們見了面就要提起這件事,以致他們許多人無法在國內繼續工作,只能返回海外去找一份工作——為了孩子。最近幾年,甚至沒有留學體會的國內家長們也紛紛要送很小的孩子去海外讀書,高中生,初中生,小學生,然后是,可預期地,幼童,或干脆在海外出生——為了孩子。
難道沒有人想過改變制度嗎?例如,改造一個壞的幼兒園?或新建一所好的幼兒園?或幾位家長聯合教育自己的孩子(上海“孟母堂”的實驗)?當然可以,我周圍就有這類家長,而且他們也有能力這樣做。但很艱難,因為官方的各種管制條例與審查——夾雜著腐敗,最終,你受不了折磨,干脆一走了之。
留在國內或在國內生孩子,我明白,讀者當中很多屬于這類家長,你們面對的第一難題,就是“三分之一定律”。你的孩子教養很好,不論以四書五經的倫理標準衡量,還是以百科全書的知識標準衡量,都非常優秀。然后呢?你敢不敢送他上幼兒園?你知道那里的老師有意無意地常常引導孩子弄虛作假阿諛逢迎爾虞我詐,總之,誘使孩子們成為將來無惡不為的人。我們的學校和我們的醫院一樣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