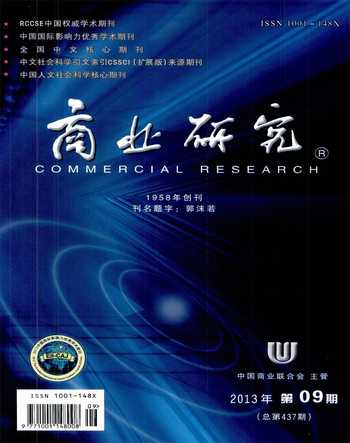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理論:分析與詮釋
高景芳 王永強(qiáng)
摘要:在關(guān)于國(guó)家起源的諸多理論中,“社會(huì)契約論”對(duì)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讓渡有一定的理論解釋力。根據(jù)社會(huì)契約理論,個(gè)人為了保障和維護(hù)那些在契約中得到公認(rèn)的(包括財(cái)產(chǎn)權(quán)在內(nèi))的權(quán)利而建立了國(guó)家;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需要國(guó)家來作保護(hù)人,而國(guó)家需要公民讓渡的財(cái)產(chǎn)來維持運(yùn)轉(zhuǎn)。該理論有助于國(guó)家和公民正確認(rèn)識(shí)、行使和履行各自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
關(guān)鍵詞: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理論;社會(huì)契約論
中圖分類號(hào):DF4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收稿日期:2013-03-29
作者簡(jiǎn)介:高景芳(1974-),男,河北河間人,河北科技大學(xué)文法學(xué)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經(jīng)濟(jì)法學(xué);王永強(qiáng)(1978-),河北衡水人,上海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法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jīng)濟(jì)法學(xué)。
基金項(xiàng)目:國(guó)家社科基金重點(diǎn)項(xiàng)目“保障農(nóng)民權(quán)益對(duì)策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08ASH009。 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讓渡是指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向受讓主體的移轉(zhuǎn)。根據(jù)受讓主體的不同,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讓渡可以分為向其他個(gè)體的讓渡和向國(guó)家的讓渡。前者如通過買賣合同移轉(zhuǎn)財(cái)產(chǎn),后者如通過稅收和征收實(shí)現(xiàn)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移轉(zhuǎn)。本文所謂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讓渡特指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向國(guó)家的移轉(zhuǎn)。
一、社會(huì)契約:“讓渡”的理論基礎(chǔ)
“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凡是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就有‘國(guó)家”[1]。“國(guó)家的出現(xiàn),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成就”[2]。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法律體系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假定以國(guó)家的存在為前提。因此,關(guān)于國(guó)家理論較為深入的探討有可能真正實(shí)現(xiàn)對(duì)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解析。而在關(guān)于國(guó)家起源的諸多理論中,較有代表性者乃“社會(huì)契約論”和“階級(jí)斗爭(zhēng)論”。其中“社會(huì)契約論”對(duì)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讓渡理論有一定的解釋力。
(一)社會(huì)契約論
“社會(huì)契約”思想無疑來源于“契約”。“所有它的營(yíng)養(yǎng)則完全來自法律學(xué)的純理論”[3]。荷蘭思想家格老秀斯最早提出國(guó)家起源于契約的觀念。他認(rèn)為國(guó)家是“一群自由的人為享受權(quán)利和他們的共同利益而結(jié)合起來的完整的聯(lián)合體”[4]。英國(guó)思想家霍布斯從他的人性觀和自然法學(xué)說出發(fā)提出,既然自然狀態(tài)如虎狼之境悲慘可怕,出于人的理性驅(qū)使,人們要求擺脫它而尋求有組織的和平生活,就相互訂立了一種社會(huì)契約,“把大家所有的權(quán)力和力量托付給某一個(gè)人或一個(gè)能通過多數(shù)的意見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gè)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從此“按約建立的國(guó)家”便產(chǎn)生了[5]。根據(jù)霍布斯的理論,國(guó)家是人們通過社會(huì)契約創(chuàng)造的,君權(quán)不是神授的,而是人民轉(zhuǎn)讓的、托付的。英國(guó)另一位思想家約翰·洛克也試圖以自然法學(xué)說闡明國(guó)家的起源。他用那種雄辯的語(yǔ)言說:“任何人放棄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會(huì)的種種限制的唯一方法,是同其他人協(xié)議聯(lián)合組成為一個(gè)共同體,以謀他們彼此間的舒適、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穩(wěn)地享受他們的財(cái)產(chǎn)并且有更大的保障防止共同體以外任何人的侵犯。”“當(dāng)這些人這樣地同意建立一個(gè)共同體或政府時(shí),他們因此就立刻結(jié)合起來并組成一個(gè)國(guó)家”[6]。作為社會(huì)契約論的集大成者,盧梭將國(guó)家起源于契約的理論作了最為系統(tǒng)的闡述。在他看來,社會(huì)契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要尋找一種結(jié)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維護(hù)和保障每個(gè)結(jié)合者的人身和財(cái)富”,“每個(gè)結(jié)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quán)利全部都轉(zhuǎn)讓給整個(gè)的集體”[7]。霍布斯、盧梭所謂“權(quán)利轉(zhuǎn)讓”,其實(shí)就是“權(quán)利讓渡”的另一種表達(dá)。
總結(jié)古典自然法學(xué)家們對(duì)于國(guó)家起源的觀點(diǎn),他們一個(gè)共同的認(rèn)識(shí)是,國(guó)家起源于處于自然狀態(tài)的人們向社會(huì)狀態(tài)過渡時(shí)所締結(jié)的契約;人們通過平等協(xié)商和相互合意組成國(guó)家,并將其部分權(quán)利讓渡給國(guó)家,在這一讓渡過程中,權(quán)利便轉(zhuǎn)化成為權(quán)力。在這份社會(huì)契約之中,人們約定:讓渡給國(guó)家的權(quán)力是用來為國(guó)民提供公共服務(wù)的。而在這份讓渡給國(guó)家的“權(quán)力清單”中,一定包括了國(guó)家對(duì)公民財(cái)產(chǎn)的征收權(quán)。
關(guān)于社會(huì)契約論的評(píng)析
“社會(huì)契約論”自其提出,即招致不斷地批評(píng)。英國(guó)保守主義者伯克就認(rèn)為, 如果國(guó)家是一種社會(huì)契約的話, 那么也是各代人之間的一個(gè)契約。 這一觀點(diǎn)實(shí)際上否認(rèn)了社會(huì)契約的理性創(chuàng)造國(guó)家說,而趨向于把國(guó)家視為一個(gè)歷史發(fā)展的自然產(chǎn)物,是由特定的環(huán)境、條件、性格、氣質(zhì),以及人民的道德、民俗和社會(huì)習(xí)慣所決定的。而另一位著名的英國(guó)思想家弗格森則明確指出,“國(guó)家的建立是偶然的, 它確實(shí)是人類行動(dòng)的結(jié)果, 而不是人類設(shè)計(jì)的結(jié)果”。此后還有歷史法學(xué)派的批判、功利主義學(xué)派的批判,以及實(shí)證主義學(xué)派的批判。所有這些學(xué)派或人物都從不同角度證明了社會(huì)契約論的不能成立[8]。
其實(shí),“國(guó)家起源無論是靠契約還是靠武力,產(chǎn)生一個(gè)有活力的政治結(jié)構(gòu),都是一個(gè)漫長(zhǎng)的創(chuàng)新制度組織的過程”[2]。任何一種國(guó)家理論都不是對(duì)歷史的描述和真實(shí)再現(xiàn), 而是一種探求性解說。“它們都以人類的、非歷史的、無法證實(shí)的狀態(tài)作為他們的基本假設(shè)”[3]。社會(huì)契約論只是證明國(guó)家發(fā)生及其合理性的模式或話語(yǔ)之一。人類歷史(包括婚姻、家庭、私有制和國(guó)家的起源)自有其本來面目,不同的學(xué)者就不同的領(lǐng)域、甚至在同一學(xué)科領(lǐng)域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得出的結(jié)論都可能有所不同,應(yīng)該各有其歷史合理性與歷史局限性,需要辯證地看待。
二、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理論的提出
(一)“讓渡”的概念
讓渡,意思就是讓出移轉(zhuǎn)。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向國(guó)家的讓渡, 從字面上理解,就是把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出移轉(zhuǎn)給國(guó)家。在現(xiàn)代契約社會(huì)中,權(quán)利的讓渡是社會(huì)行動(dòng)者相互關(guān)系中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公民權(quán)利的讓渡,是國(guó)家與公民關(guān)系成立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從而也是國(guó)家公共權(quán)力與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成立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理論是對(duì)傳統(tǒng)理論的繼承和發(fā)展,是適應(yīng)時(shí)代發(fā)展要求的新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觀。
(二)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理論與社會(huì)契約理論的關(guān)聯(lián)
政府要履行自己的職能,就不可能不擁有相當(dāng)?shù)闹錂?quán)和強(qiáng)制權(quán)。但公民的人身和財(cái)產(chǎn)絕對(duì)不能成為政府權(quán)力支配的對(duì)象。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政府才能干涉公民這方面的權(quán)利。在任何社會(huì),都存在上述的“例外情況”,關(guān)鍵是如何基于法治的觀點(diǎn),從保護(hù)公民權(quán)利出發(fā),審視和把握這種“例外情況”。
社會(huì)契約論,從“契約”出發(fā),解釋國(guó)家的產(chǎn)生,并進(jìn)而將國(guó)家的權(quán)力解釋為人民權(quán)利的讓渡。“人們聯(lián)合成為國(guó)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hù)他們的財(cái)產(chǎn)”[6]。在這一理論下,國(guó)家征稅的權(quán)力、對(duì)公民財(cái)產(chǎn)征收的權(quán)力都可解釋為公民權(quán)利——主要是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讓渡。而階級(jí)斗爭(zhēng)論,強(qiáng)調(diào)國(guó)家是一個(gè)階級(jí)壓迫另一個(gè)階級(jí)的工具,因而無法容納“讓渡”理念。按照社會(huì)契約理論,國(guó)家的征稅權(quán)、征收權(quán)等對(duì)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剝奪(一般性限制亦復(fù)如此)可以解釋為在社會(huì)契約下公民對(duì)于自己的財(cái)產(chǎn)被剝奪或限制的同意(以法律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從而可以消除其違法性。而如果按照階級(jí)斗爭(zhēng)理論的國(guó)家觀,既然國(guó)家是階級(jí)斗爭(zhēng)的工具,那么,國(guó)家作為暴力工具對(duì)于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剝奪或限制就根本無需公民自己的同意,更談不上所謂“讓渡”。因此,將內(nèi)涵有“自由、平等和權(quán)利”的社會(huì)契約論作為理解財(cái)產(chǎn)權(quán)與國(guó)家權(quán)力之間的關(guān)系,可能更有助于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保障。
當(dāng)然,我們?cè)谠鐣?huì)契約論解釋財(cái)產(chǎn)權(quán)保障問題時(shí),亦須記得:“任何有關(guān)國(guó)家權(quán)力來源的論證,都不是實(shí)證的現(xiàn)象描述,而是一個(gè)純粹的理論訴求,它表述的是人類控制國(guó)家權(quán)力的理想和追求。”“它并不是描述一個(gè)事實(shí),而是在塑造一種信仰。正是這種信仰,使人民得以從舊國(guó)家時(shí)代的暴力陰影中走出,使權(quán)力得以和文明、進(jìn)步、人權(quán)等先進(jìn)理念相連接”[9]。 “社會(huì)契約的國(guó)家學(xué)說, 主要是對(duì)秩序正當(dāng)化的一種論說方式, 而不是這種秩序的建立方式”[8]。“人類社會(huì)是否確系在某一時(shí)期通過訂立契約而形成的,那無關(guān)緊要。不論歷史形成過程如何,人類社會(huì)一形成即具有類似契約的性質(zhì)”[10]。如果人類不能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制定法則并服從制定的法則,人類的幸福倒是真的不可想象。
三、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的必要性:國(guó)家是“必要的惡” 托馬斯·霍布斯設(shè)想的自然狀態(tài)是社會(huì)契約論者分析國(guó)家起源的起點(diǎn)。在這種狀態(tài)下,沒有法律,沒有人與人之間的權(quán)利界限,任何人都生活在“貧窮的、孤獨(dú)的、污穢的、粗野的、低于標(biāo)準(zhǔn)的”狀態(tài)。正是基于對(duì)這種無政府狀態(tài)叢林的恐懼,人類為了生存與發(fā)展,必須建立被稱為國(guó)家的共同體,并賦予其一定的公共權(quán)力。或者說,所有人都會(huì)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將自己的權(quán)利讓渡給處于上升時(shí)期的、承諾提供后續(xù)保護(hù)的統(tǒng)治者[11]。但是,國(guó)家被賦予的公共權(quán)力既可能保護(hù)人權(quán),也可能踐踏人權(quán)。因此,人類又必須對(duì)自己所授出的公權(quán)力予以提防、加以規(guī)范和控制。因此,國(guó)家被稱作一種“必要的惡”。正是這種“惡”存在的必要性,決定了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的必要性。
根據(jù)社會(huì)契約理論,個(gè)人為了保障和維護(hù)那些在契約中得到公認(rèn)的權(quán)利而建立了政府。但是,“一旦建立起掌握著統(tǒng)治權(quán)的政府,它有可能不愿意把自己的權(quán)力局限在當(dāng)初授權(quán)的范圍內(nèi)。政府可能主動(dòng)承擔(dān)起重新規(guī)定個(gè)人權(quán)力的角色”[12]。“政府”或政府的代理人,極有可能采取獨(dú)立行動(dòng)修改或改變其擁有的權(quán)利,從而違反先前的約定。可以說,國(guó)家這個(gè)“利維坦”在給予人類幸福的同時(shí),也存在戧害特定公民的危險(xiǎn)。國(guó)家的最大任務(wù)是防止惡,但也惟有國(guó)家才能做出大惡來[13]。因此,在公權(quán)力與私權(quán)利關(guān)系定位中,人們必須尋找能夠遏制國(guó)家公權(quán)力異化的途徑。這一途徑就是權(quán)力制約。消除副作用的方法就是用能夠取得社會(huì)同意的規(guī)則處理各種公共事務(wù)。所謂社會(huì)同意的規(guī)則,在法治國(guó)家,就表現(xiàn)為由代議機(jī)關(guān)制定的法律。
如前所述,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hù)是有成本的。“斷定權(quán)利有成本也就要承認(rèn)為了獲得或保護(hù)權(quán)利我們必須放棄一些東西。”“公共政策的決定不應(yīng)該以假想自由與征稅者敵對(duì)為基礎(chǔ),因?yàn)槿绻@兩者真的是對(duì)立的,那么我們所有的基本自由都將等候被廢除”[14]。也就是說,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保障與其讓渡并不是對(duì)立的。因?yàn)椋褙?cái)產(chǎn)權(quán)需要國(guó)家(通過其政府)來做保護(hù)人,而國(guó)家需要公民讓渡的財(cái)產(chǎn)來維持,因此,為了維護(hù)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不得不向國(guó)家進(jìn)行讓渡。具體而言:
(一)權(quán)利之間的沖突需要國(guó)家協(xié)調(diào)和解決
由于資源相對(duì)于人的需求的有限性,權(quán)利人在行使自己的權(quán)利過程中,出于對(duì)自身利益的強(qiáng)烈追求,可能會(huì)為達(dá)到目的而侵犯他人利益,加上在很多情況下,權(quán)利的邊界本身并不清晰,權(quán)利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解決利益沖突的問題是由不同層級(jí)、不同部門的法律來完成的。對(duì)于私益之間的沖突,主要由私法來完成;公益與私益之間的沖突,則主要由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法加以解決。正如耶林所指出的:法律的目的是平衡個(gè)人利益和社會(huì)利益,實(shí)現(xiàn)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結(jié)合,從而建立起個(gè)人與社會(huì)的伙伴關(guān)系[15]。
在現(xiàn)代化國(guó)家中,國(guó)家是維持社會(huì)秩序的唯一正式的制度安排。國(guó)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自古至今,因生存資源引起的社會(huì)沖突可謂層出不窮。不管是為了最有效地避免沖突發(fā)生還是最有效地解決業(yè)已發(fā)生的沖突,客觀上都需要建立一個(gè)對(duì)強(qiáng)制性手段具有壟斷權(quán)力的國(guó)家。因?yàn)椋霸谝粋€(gè)可以控制的疆域內(nèi)建立一套暴力組織,其效率是最高的”[16]。 “在任何時(shí)候,能否建立一個(gè)對(duì)內(nèi)能夠絕對(duì)地維持社會(huì)秩序,對(duì)外能夠抵抗財(cái)產(chǎn)掠奪者的強(qiáng)大國(guó)家,都是個(gè)體生命獲得保障的基礎(chǔ)”[17]。
沒有救濟(jì)便沒有權(quán)利。權(quán)利受到損害需要救濟(jì),權(quán)利之間的沖突也需要國(guó)家協(xié)調(diào)和解決。如果沒有一種來自于私權(quán)利又凌駕于私權(quán)利之上的公共權(quán)力在法律上保證個(gè)人權(quán)利不受他人侵犯,個(gè)人權(quán)利就很難得到實(shí)現(xiàn)或者完全實(shí)現(xiàn)。“對(duì)權(quán)利的渴望和對(duì)權(quán)利保護(hù)的渴求,是人的最基本的倫理要求,也因?yàn)槿绱耍藗儾艜?huì)自動(dòng)地讓渡一部分權(quán)利給國(guó)家并形成國(guó)家權(quán)力”[18]。盡管私力也有解決糾紛的功能,但在任何有國(guó)家的社會(huì)里,基于有效性和成本的考量,私力救濟(jì)都難以完全取代公力救濟(jì)而獨(dú)自擔(dān)當(dāng)權(quán)利的保護(hù)神,而只能作為國(guó)家公力救濟(jì)的補(bǔ)充手段。
(二)社會(huì)公共利益需要國(guó)家代表和維護(hù)
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運(yùn)行使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下接近同質(zhì)化的利益格局迅速演變?yōu)槎嘣睦娓窬郑豢杀苊獾貢?huì)產(chǎn)生相互競(jìng)爭(zhēng)的利益關(guān)系。不僅私益之間可能發(fā)生沖突,個(gè)人在行使權(quán)利、追求個(gè)體利益時(shí)也可能對(duì)社會(huì)公共利益完全漠然。而社會(huì)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表者非國(guó)家莫屬。現(xiàn)代社會(huì),直接民主的巨大成本讓人們望而興嘆。民主普選組成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的制度事實(shí)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人民不可能統(tǒng)統(tǒng)變成國(guó)家權(quán)力的直接操作者。“即使從高度抽象的哲學(xué)層次上承認(rèn)建立社會(huì)秩序制度之合法性的一致同意的基礎(chǔ),但是在實(shí)踐層次上,一致同意的要求可能看起來不過是一種羅曼蒂克式的烏托邦”[12]。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代議制是人類政治生活中的一種無奈的選擇。只有在代議制下,公民才能從無盡的政治生活中解脫出來以自由地從事“第二職業(yè)”,譬如去經(jīng)商、進(jìn)行科學(xué)研究、在家欣賞音樂,等等。
(三)人民福利的增長(zhǎng)離不開國(guó)家的積極推進(jìn)
在自由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西方資本主義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整體規(guī)模和形態(tài)上,仍屬于“守夜人”式國(guó)家。國(guó)家與社會(huì)嚴(yán)格區(qū)分;國(guó)家權(quán)力長(zhǎng)期消極。這種國(guó)家模式的假定條件是,在自由競(jìng)爭(zhēng)和獨(dú)立價(jià)格的制約之下的,市場(chǎng)作為一個(gè)自足自律的領(lǐng)域無需政府干預(yù)也能保證公正與自由。具有代表性的觀點(diǎn)是,“個(gè)人自由只能通過限制政府干涉?zhèn)€人行動(dòng)或結(jié)社得到保證。個(gè)人自由不需要政府去實(shí)施,而只需要政府克制”[14]。
但是,資本主義在19世紀(jì)末的發(fā)展超越了這一模式。壟斷組織的出現(xiàn)使競(jìng)爭(zhēng)并不完全、價(jià)格也不獨(dú)立,隨著社會(huì)財(cái)富的分化和急劇集中,至少是一部分人發(fā)現(xiàn)所謂的“自由”僅僅是“貧困的自由”。于是,“自由放任”的市場(chǎng)轉(zhuǎn)向“規(guī)制市場(chǎng)”,“自由國(guó)家”過渡到了“社會(huì)國(guó)家”[19]。于是,政府干預(yù)主義興起并一發(fā)不可收拾。特別是自二戰(zhàn)以后,許多歐洲國(guó)家開始把福利權(quán)利當(dāng)成一項(xiàng)憲法權(quán)利來看待,因此,政府的積極職能和履行這種職能的權(quán)力獲得認(rèn)可。人民要求國(guó)家必須積極介入其生活,因而人民對(duì)國(guó)家的需求與依賴日益加深。國(guó)家在當(dāng)代的任務(wù),除必須保護(hù)個(gè)人之社會(huì)安全外,還需對(duì)公民提供“從搖籃到墳?zāi)埂钡纳嬲疹櫋?/p>
在社會(huì)國(guó)家下,人權(quán)觀念也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即從“消極主義”的人權(quán)觀轉(zhuǎn)到“積極主義”的人權(quán)觀。消極人權(quán)觀強(qiáng)調(diào)自由即強(qiáng)制的禁止,屬于“機(jī)械法治主義”;積極的人權(quán)觀則主張“財(cái)產(chǎn)權(quán)附有社會(huì)義務(wù)”,權(quán)利仰賴國(guó)家給付,是一種“能動(dòng)法治主義”。
面對(duì)新的歷史時(shí)期福利國(guó)家等思想的挑戰(zhàn),新憲政論者敏銳地提出重新評(píng)價(jià)國(guó)家作用的必要性。正如霍姆斯所言:“憲政政體必須不只是限制權(quán)力的政體,它還必須能有效地利用這些權(quán)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福利”[20]。這就突破了古典憲法理論片面強(qiáng)調(diào)控制國(guó)家的時(shí)代局限性。人民組建政府的目的并非只是在于保衛(wèi)安全,提供制度、分配供給、創(chuàng)造環(huán)境也是人民組建政府的目的,也是政府的義務(wù)之一。
四、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的形式與原則
(一)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的形式
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的形式凡有多種:稅收、征收、市場(chǎng)交易、行政強(qiáng)制、沒收、罰款、收費(fèi)、罰金等等。其中稅收、征收、市場(chǎng)交易是最主要的三種。政府采購(gòu)就是市場(chǎng)交易的形式。由于公民財(cái)產(chǎn)通過政府采購(gòu)合同向國(guó)家的讓渡,與民法上一般的契約交易相似,沒有多少?gòu)?qiáng)制性。因此,本文不予討論。而稅的征收和財(cái)產(chǎn)征收則帶有色彩濃重的強(qiáng)制性。也就是說,公民為了享受公民權(quán)利必須讓渡一部分自己的財(cái)產(chǎn),并將其轉(zhuǎn)化為支撐國(guó)家機(jī)器正常運(yùn)轉(zhuǎn)的國(guó)家征稅權(quán)或?qū)褙?cái)產(chǎn)的征收權(quán)。
(二)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的原則
筆者認(rèn)為,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的原則至少應(yīng)該包括:(1)公益讓渡原則;(2)依法讓渡原則;(3)有限讓渡原則。公益讓渡原則,是指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讓渡必須僅能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方得為之。這一原則在國(guó)家行使稅收征收權(quán)和財(cái)產(chǎn)征收權(quán)時(shí)均應(yīng)一體遵循。依法讓渡原則,在稅收征收中主要體現(xiàn)為稅收法定原則;在財(cái)產(chǎn)征收中主要體現(xiàn)為法律保留原則。有限讓渡原則,在稅收征收中體現(xiàn)為稅收的限度問題;在財(cái)產(chǎn)征收中則體現(xiàn)為公法上的比例原則[21]。
總之,肯定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可讓渡性并非從根本上否定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價(jià)值。恰恰相反,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讓渡理論的提出是為了光大和彰顯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價(jià)值。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強(qiáng)調(diào)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在國(guó)家征收權(quán)之先,是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成就了國(guó)家征收權(quán),而不是相反。因此,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對(duì)國(guó)家只能有限讓渡,也就是不能由國(guó)家公權(quán)完全剝奪,只能根據(jù)公益需要實(shí)施必要的限制。
參考文獻(xiàn):
[1] [英]鮑桑葵. 關(guān)于國(guó)家的哲學(xué)理論[M].汪淑鈞,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5:46.
[2] [美]道格拉斯·C.諾思. 經(jīng)濟(jì)史上的結(jié)構(gòu)和變革[M].厲以平,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2:108.
[3] [英]梅因. 古代法[M].沈景一,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59:66,174.
[4]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xué)——法律哲學(xué)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 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46.
[5] [英]霍布斯. 利維坦[M].黎思復(fù),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5:126-132.
[6] [英]洛克. 政府論(下篇)[M].葉啟芳,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4:59-60,77.
[7] [法]盧梭. 社會(huì)契約論[M].何兆武,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3:19.
[8] 蘇力. 從契約理論到社會(huì)契約理論[J].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1996(3).
[9] 劉劍文. 財(cái)稅法專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7:148.
[10] [美]科恩. 論民主[M].聶崇信,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8:47.
[11] 詹姆斯·M.布坎南. 財(cái)產(chǎn)是自由的保證[A].[美]查爾斯·K.羅利. 財(cái)產(chǎn)權(quán)與民主的限度[C]劉曉峰,譯. 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7:30.
[12] [澳]杰佛瑞·布倫南,[美]詹姆斯·M.布坎南. 憲政經(jīng)濟(jì)學(xué)·規(guī)則的理由[M].馮克利,譯.北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4:30-31.
[13] 胡肖華,倪洪濤. 論行政權(quán)的憲法規(guī)制[J].行政法學(xué)研究,2004(1).
[14] [美]史蒂芬·霍爾姆斯,凱斯·R·桑斯坦. 權(quán)利的成本——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M].畢競(jìng)悅,譯.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10-16,20.
[15] 張文顯. 二十世紀(jì)西方法哲學(xué)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08.
[16] 朱琴芬. 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國(guó)家理論及其對(duì)中國(guó)改革發(fā)展的啟示[J].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xué)報(bào),2005(1).
[17] 葉海波. 略論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當(dāng)代中國(guó)憲政建設(shè)[J].太平洋學(xué)報(bào),2008(3).
[18] 趙萬一,葉艷. 從公權(quán)與私權(quán)關(guān)系的角度解讀國(guó)家征收制度[J].華東政法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7(2).
[19] [日]蘆部信喜. 憲法(第三版)[M].林來梵,譯. 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13-14.
[20] [美]斯蒂芬·L·埃爾金,卡羅爾·愛德華·索烏坦. 新憲政論——為美好的社會(huì)設(shè)計(jì)政治制度[M].周葉謙,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156.
[21] 高景芳,王永強(qiáng).論征收中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法律保障[J].商業(yè)研究,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