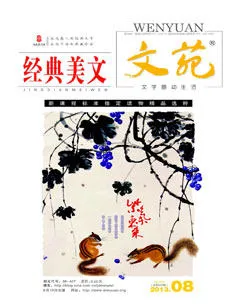一覺
在寫作本文之前的二十二天,段祺瑞執政府悍然開槍射殺徒手請愿的愛國青年,制造了震驚海內的“三一八”慘案。魯迅先生目睹了許多愛國青年慘遭殺害,悲憤之情噴薄而出,《一覺》可看作一篇檄文。文中有對生死的追問,有對戰斗精神的解讀,有對青年覺醒意識的謳歌和頌揚,有對黑暗社會的討伐和抨擊。先生認為,直面慘淡人生的靈魂才是人的靈魂,覺醒的斗士肩負著民族的希望。文中青年猛士的叛逆、犧牲、戰斗、覺醒引起魯迅先生內心欣然的“驚覺”,是這篇文字的精神所在。先生對青年崛起的“粗暴的流血和隱痛的靈魂”的體認,是他對“生”與“死”價值意義的最好詮釋。同時,青年的精神光輝,給了先生以希望和力量,促使他更加執著地在充滿黑暗的人間生活和戰斗。
心存悲憫,正視存在,傾吐真言,敢于擔當,是任何時代和社會都需要召喚的公民內在精神本質,尤其對肩負民族復興大任的青年一代,更是如此。
飛機負了擲下炸彈的使命,像學校的上課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空飛行。每聽得機件搏擊空氣的聲音,我常覺到一種輕微的緊張,宛然目睹了“死”的襲來,但同時也深切地感著“生”的存在。
隱約聽到一二爆炸聲以后,飛機嗡嗡地叫著,冉冉地飛去了。也許有人死傷了罷,然而天下卻似乎更顯得太平。窗外白楊的嫩葉,在日光下發烏金光;榆葉梅也比昨日開得更爛漫。收拾了散亂滿床的日報,拂去昨夜聚在書桌上的蒼白的微塵,我的四方的小書齋,今日也依然是所謂“窗明幾凈”。
因為這一種原因,我開手編校那歷來積壓在我這里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我要全都給一個個清理。我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這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們的魂靈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們是綽約的,是純真的——啊,然而他們苦惱了,呻吟了,憤怒了,而且終于粗暴了,我的可愛的青年們。
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因為這是人的魂靈,我愛這樣的魂靈;我愿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縹緲的名園中,奇花盛開著,紅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鶴唳一聲,白云郁然而起……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
我忽然記起一件事:兩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學的教員預備室里,看見進來一個并不熟悉的青年,默默地給我一包書,便出去了,打開看時,是一本《淺草》。就在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許多話。啊,這贈品是多么豐饒呵!可惜那《淺草》不再出版了,似乎只成了《沉鐘》的前身。那《沉鐘》就在這風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里寂寞地鳴動。
野薊經了幾乎致命的摧折,還要開一朵小花,我記得托爾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動,因此寫出一篇小說來。但是,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間,拼命伸長它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來造成碧綠的林莽,自然是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勞焦渴的旅人,一見就怡然覺得遇到了暫時息肩之所,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沉鐘》的《無題》——代啟事——說:“有人說:我們的社會是一片沙漠——如果當真是一片沙漠,這雖然荒漠一點也還靜肅;雖然寂寞一點也還會使你感覺蒼茫。何至于像這樣的混沌,這樣的陰沉,而且這樣的離奇變幻!”
是的,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眼前,他們已經粗暴了,或者將要粗暴了,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因為這些魂靈使我覺得是在人間,是在人間活著。
在編校中夕陽居然西下,燈火給我接續的光。各樣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馳去了,身外但有昏黃環繞。我疲勞著,捏著紙煙,在無名的思想中靜靜地合了眼睛,看見很長的夢。忽而驚覺,身外也還是環繞著昏黃;煙篆在不動的空氣中飛升,如幾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難以指名的形象。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