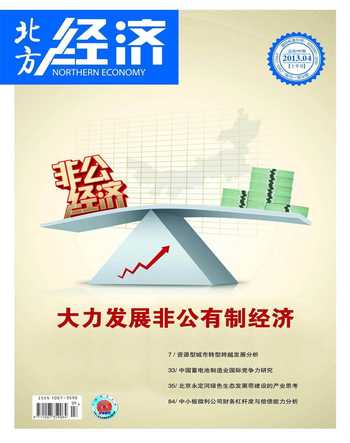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選擇
高雅
一、問題的提出:中國面臨來自“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一) 拉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回顧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當其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世界上許多國家人均GDP長期在900—11000美元甚至在3000—5000美元左右徘徊,并指出,東亞經濟要防止陷入這一陷阱,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解決普遍存在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
(二) 中國面臨來自“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城鄉收入差距拉大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在2001年人均GDP 首次超過1000美元,201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4428.5美元,已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不容忽視的是,中國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從我國1978-2010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對比來看,兩者逐年擴大,且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以2010年為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者之間的對比,城鎮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8.65倍,農村高收入是低收入的7.51倍。而《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中也提到,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僅為1.4%,財富差距達32倍。
(三)城鄉收入差距的關鍵:農民財產性收入的缺失
農村居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基本占據90%稍弱,近年來隨著各項惠農措施的實施,轉移性收入也逐年增加,而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從2006年起就一直徘徊在3%左右,農民擁有最重要的財產——土地,但卻是中國收入最低的群體,是最沒有話語權的群體。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推進城鄉土地要素分配均等化使農村土地參與到農民收益分配中,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二、實踐探索:河南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土地收益分配模式
筆者對河南部分地區做了深入調研,發現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至少可整理出40%的宅基地以及公共基礎設施用地,這些新增建設用地的所有者——農民集體積極進行探索,實現土地增值收益的變現,達到既增加農民土地要素收益,又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雙贏目的。
(一)土地所有權轉換:貨幣補償或產權調換
土地所有權轉換涉及兩種情況:公益項目國家征地和城中村改造項目,前者需要政府進行安置,以房換房,同時給予一定的補償,后者各地做法稍有不同,但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貨幣補償或產權調換的形式。從鄭州的情況來看,按照2007年公布的《鄭州市城中村改造工作流程(試行) 》,規定原村民合法住宅的補償安置以建筑面積為依據,3層以下的合法建筑面積,選擇貨幣補償的按市場評估價補償,選擇產權調換的按“拆一還一”標準安置,對三層以上建房問題則不做明確規定,由各區政府根據實際情況酌定,目前基本做法有“拆三補一”和“拆五補一”。
(二)土地流轉:安置房+土地長期受益(租金、分紅)
1.土地整體流轉
土地整體流轉,既包括農地,也包括置換的宅基地,適用于整體搬遷以及產業帶動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但兩者主導因素不同:前者為政府,目的在于扶貧或者公益項目建設,原有土地增值空間較小;后者為優勢產業,目的在于扶持優勢產業發展,原有土地增值空間大,農民收入增加大于前者。
鄭州上街區的南部山區共有西林子、東林子、營坡頂、楊家溝、老寨河5個行政村,人口1200多戶,4000余人,約占全區農業總人口的額10%,面積共1133hm,其中建設用地245hm,五村均為省(市)級重點貧困村,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等問題極大制約了山區發展。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實施了整體搬遷,村民年均收入凈增2500元,具體做法:①完善公共服務設施:財政出資5600萬元,在安置小區周邊配套建設公共服務設施,解決搬遷村民就學、醫療、養老問題。②確保農民長期獲得土地收益:出臺《搬遷村土地流轉收益分配及扶貧資金分配辦法》,統一分配山區土地流轉經營收益,保障搬遷村民享有土地的長期受益權。③補貼居民置換安置房:丈量測算村民自有房屋,市場化合理定價,每戶給予一定的補貼,統一置換為新建安置房。④完善社會保障:五保老人除自愿分散供養,在家中享受每人每年3120元的補助外,全部納入敬老院集中供養。
2.新增建設用地流轉
新增建設用地流轉涉及置換的宅基地,目前多數地區的采取的是租金加分紅的形式來實現土地收益分配。
郟縣冢頭鎮陳寨中心村位于冢頭鎮北3公里,輻射段村、仝村、秦樓3個行政村,1247戶,5446人,耕地4728畝,被確定為中心村后,開展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已建成新民居100余套,綠化面積3000m2,各項公共設施基本齊備,積極引導段村、仝村、秦樓向陳寨靠攏。具體做法:依托龍頭企業龍湖灣生態園,流轉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整理出來的宅基地,將其復墾為農地,發展苗圃種植業,建成占地80hm2的龍湖灣苗木生態基地。此基地采取的是合作社形式,農民以土地入股,每畝地折合資金4000元,年最低收入1200元/畝,其中包括固定租金600元/畝和年最低分紅600元/畝,生態基地效益好,分紅隨之增加,此外,農民還可在基地工作,獲得工資性收入。
3.土地產權不變,用途改變:土地補償費
土地產權不變,用途改變,即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土地利用與項目區內土地整理項目同步實施,同時也最大化釋放土地整理項目的作用。從調研情況來看,采取的均是土地補償的方式,收入多數用于新型農村社區建設。
新鄭市薛店鎮把常劉中心村(常劉村、薛集村)和解放北路社區(崗周村、草店村、花莊村)兩個項目合二為一,形成城鄉增加掛鉤項目,計劃爭取掛鉤轉指標42.7hm2,其中22.7hm2用于安置區建設(常劉中心村10hm2,解放北路社區12.7hm2),20hm2平移到鎮區招商進行商務開發,獲得土地補償費,用于平衡建設資金。衛輝的唐莊鎮利用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整理出的200畝土地進行指標替換,獲得600-700萬貨幣收入,用于新型社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三、反思:成績與問題并存
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在河南已經開展了一段時間,從現有狀況來看,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方面既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也存在一定的問題。
(一)成績:增加了農民財產性收入
與全國相比,河南農村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占純收入比重從2006年起持續增加,且均高于同期全國水平,2010年增加為5.07%,高于全國1.65個百分點,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有助于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事實上,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在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同時,通過土地流轉,引進各類項目,實現“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增加了農民的工資性收入。
(二)問題:農民的弱勢地位
1.制度約束。現行農村集體土地產權制度的基本框架是所有權和使用權相分離:所有權主體是村農民集體、村內若干個農民集體、鄉鎮農民集體,使用權主體則按不同的土地類型有不同的主體,宅基地使用權主體是農戶,村莊內公共用地是集體全體成員。而對所有權而言,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是虛置的,直接導致了農村土地實際為少數人所控制,以權謀私,侵害了農民的土地權益。
2.村集體、地方政府對農民利益的侵占。村集體、地方政府對農民利益的侵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業主和地方政府為了各自利益壓低租金,而農民由于缺乏組織,往往處于弱地位,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模式;其二,村集體和地方政府對農村集體土地實行強制性流轉,并且往往截留、挪用土地增值收益。
3.土地收益變現困難。受農村宅基地使用政策和房屋產權證發放政策的限制,鎮村一體化后,農民到城鎮集中居住點或中心村新建的房屋不能發放房產證和建設用地分割使用證,部分農民城市安家后,無法將原有房屋進行變現,實現財產性收入增加。
四、結論與啟示:推進城鄉土地收益分配均等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在于縮小貧富差距,將貨幣從邊際效用較低的高收入群體轉移到邊際效用較高的低收入群體,增加社會總效用:一方面可以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對弱勢群體的扶持,增加話語權,減少社會動蕩。
從中國目前情況來看,縮小貧富差距的關鍵在于拉近城鄉收入差距,在于大幅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中國人口眾多、農地有限,人均耕地面積0.152hm2,經營性收入增加有限,轉移性收入主要是靠政府的財政支持,在目前的情況下,想要大幅增加也存在一定的困難,對工資性收入而言,隨著農民工工資的提高,這一塊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成為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源泉,然而,我們卻忽視了農民最重要的一塊收入:土地財產收入。
應該推進城鄉土地收益分配均等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體而言,就是開放農村集體土地市場,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合法入市,使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中新增建設用地收益留到農村,留給農民,真正還利于農民,實現農民收入增加。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旅游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張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