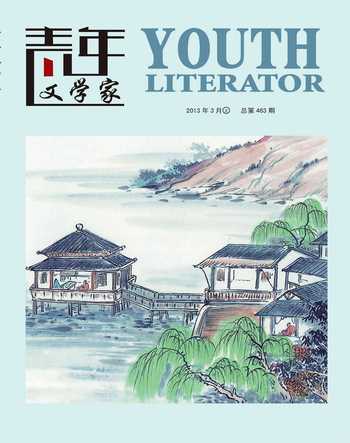淺談神魔小說《西游記》人物形象的道德內涵
摘要:神魔小說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一種,又稱神怪小說。它在明清兩代的小說史上有著獨特的歷史地位。神魔小說中的神、魔二元對立形象,不僅是小說情節發展的主要線索和推動力量,而且是作家反映現實,表達其社會理想、道德理想的主要手法。在“神魔小說”中,神、魔形象是具有一定的道德內涵的。主要表現在:神仙是封建正義的維護者,妖魔則是封建正統秩序的破壞者,是“邪惡”的象征。“神魔小說”中的神、魔對立也是人心性結構中“善”與“惡”的對立;神、魔斗爭乃是人心“去欲就善”艱難過程的象征性寫照。而這些在神魔小說《西游記》中是有體現得淋漓盡致。
關鍵詞:神魔小說;《西游記》;道德內涵
作者簡介:張先云,男(1987-),青海西寧人,青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古代文學明清小說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7-0-02
在“神魔小說”中,雖然“神仙”與“妖魔”的本領是很相似的,但是在道德上他們卻是完全對立的。“神仙”具有世俗社會道德標準中的各種美德,是“正義”的象征、世俗道德的完美體現者;而“妖魔”代表了世俗道德中種種“邪惡”的因素,并最終因此受到懲罰。小說的“神勝魔敗”結局也因此有了一種道德寓意。神魔的道德對立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神仙是封建正義的維護者,妖魔則是封建正統秩序的破壞者,是“邪惡”的象征
“神魔小說”中,神仙常被描寫成忠君撫國、維護封建秩序的“英雄”。《西游記》中的孫悟空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尤其他的無拘無束、藐視權威的反叛性格,讓我們記憶猶新。從文學形象看,小說前七回作為“反叛者”的孫悟空顯然個性更鮮明,形象更為生動。但小說作者心目中的孫悟空,并非是“反叛者”形象,而是一個棄“惡”從“善”,皈依正道,并在實際行動中竭力維護封建正統的一個形象。因此,《西游記》第七回以后,孫悟空的性格有了一個巨大的變化。他對天上的等級森嚴的神佛世界開始接受和服從。雖然西去的路上充滿挫折,他自己也屢受師父不公正待遇,他卻義無反顧地去完成神佛們交給他的任務。其實,“取經”的發起人和組織者雖為天上神佛,但其目的卻是要為塵世封建王朝整肅道德,建立統治秩序。其現實意義,就如如來講述“取經”理由時所言,乃是要助孔氏之“仁義禮智之教”,改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局面。也正因如此,“取經”既符合神佛“救濟眾生”意愿,又能“普諭世人為善”,從而具有保人間帝王“江山永固”之意。于是,“人道”與“神道”取得了一致,而孫悟空等人也自然成為忠君扶國的英雄了。也正因為有了這層涵義,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西天”路上的孫悟空一反其藐視權威的性格,大行佐國扶命之舉,竭力維護現存統治秩序。他擊殺的妖魔中,許多就是亂政欺君的“反叛者”。他在烏雞國,為國王鏟除妖魔,為國王恢復權力,重建封建統治秩序,并以此為功。即使對那些胡作非為的君王,他也采取“除了邪,治了國,勸正君王”的態度。例如對滅法國、車遲國昏庸無能的國君,也是好言相勸,尊崇有加,自覺維護君臣之道。顯然,這時候的孫悟空形象與前面以“齊天大圣”自居,藐視權威的“反叛者”形象已相去甚遠。從文學的角度看,這時的孫悟空已喪失舊日風采和吸引力,個性逐漸消退了。但從另一方面看,這個改過自新,以忠誠撫國為己任,自覺維護封建秩序的孫悟空,才是作者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只有這樣的“英雄”才符合封建世俗社會的道德標準。
“神魔小說”還塑造了一大批作為神仙對立面,代表社會邪惡勢力的妖魔。“神魔小說”中的“魔”,實為“妖魔”合成。他們在小說中也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本領。他們也可以上天入地,日行千里,呼風喚雨,隱身變形,因而能夠與神仙長期抗衡,演出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神魔斗法故事。“妖魔”不僅在能力上與“神仙”相似,而且常常與“神仙”存在一定的關系。《西游記》遍布“西天”路上的妖魔中,有許多就直接來自天庭神佛門下,或由神佛變化易形面來,以考驗“取經人”的意志。因此,“神魔小說”中的神與佛間存在著一種復雜關系,既對立,又相通,還常常互相轉化角色。這種設計使小說人物關系更為復雜和微妙,使情節增添了曲折性和趣味性。同時,也是對中國古代神、妖辯證關系認識的一種繼承。“神魔小說”中的妖魔們還常常違反君臣之道,犯上作亂,破壞綱常,在封建倫理觀念中,此乃大逆不道。《西游記》中,由于“取經”直接關系著世俗教化,關系著封建政權的穩定,所以它受到天上神佛和地上明君圣主的一致支持和關懷。因此,破壞“取經”,就是以下犯上,藐視君威。正是這樣,對“取經”的態度,就成為小說“神”與“魔”的分野、“正”與“邪”的標準。同時,小說中許多妖魔還自恃神功,欺君犯上,權傾朝野,甚至篡權自立。比如車遲國的虎力大仙,比丘國的國丈,烏雞國的青獅等,皆不守君臣之道,侵犯君威,以下犯上。他們的行為和下場,表現出作者對君臣之道等世俗道德觀念的強調和認同。“神魔小說”所描寫的“妖魔”除了違反封建綱常,觸犯正統外,另外一個重大的特征就是“害民自利”,濫施暴力,與神仙的仁慈、利民助民行為形成鮮明對比。這點也常常成為神、魔斗爭的重要的原因。具體地說,“神魔小說”中的妖魔大多天性殘忍,以殺人傷生來滿足自己的私欲。《西游記》中的眾多妖魔大多是為害一方,擾亂當地百姓的惡人,并且他們大都以食人為樂。如第二十八回中的黃袍怪就在天宮中吞噬宮女;第四十七回中的金魚精每年要陳家村村民以童男童女為祭品;比丘國妖魔所化的國丈為獲取藥引,要取一千一百一十一個小兒心肝。這些都是“妖魔”殘暴天性及害命行徑的描寫。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神魔小說”中的“妖魔”大都以違反封建綱常倫理和害民自利為基本特征,從而與“神仙”形象形成鮮明對照。這種叛明“神”與“魔”的方法,顯然是以世俗封建道德為基本標準的。因此,小說中的“神”與“魔”,常常是同出一源,能力本領相似,但卻處于封建正統道德觀念中的兩極,從而使神仙們成為“正義”的代表,妖魔們成為“邪惡”的象征。其實,“正”與“邪”,“善”與“惡”從來不是抽象的,而是以一定時代、一定階級屬性的標準為依據的。“神魔小說”中的這種標準只有一條,就是中國封建社會以統治階級思想為主體的世俗正統道德觀念。
二、“神魔小說”中的神、魔對立也是人心性結構中“善”與“惡”的對立;神、魔斗爭乃是人心“去欲就善”艱難過程的象征性寫照
“正義”與“邪惡”的對立,還不是神、魔形象的全部內涵。中國文化在研究和評判“善”與“惡”時,不僅注重其外在行為,更關注其內部的“善”、“惡”之因,即導致其行為差異的根源。所以,中國傳統道德不僅包括對人言行的規范,還包括對人“心性”的特殊要求,即要求人達到內外皆善的道德標準。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代表的儒道兩家,皆十分重視“心”的作用,強調人的“內”善,認為只有內心至“善”才能最終達到行為之“善”。孟子把人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為儒家道德準則“任義禮智”之“四端”。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化是十分看重人的道德動機的,常常以人“心性”的善惡來評判人行為的善惡,認為“善行”由“善因”而生。這種道德觀對“神魔小說”作家的創作意識也有影響。這種影響就是:“神仙”與“妖魔”所代表的“正義”與“邪惡”,不僅指人行為中的“善”與“惡”,而且指人內心中的“善因”與“惡因”。換句話說,“神”與“魔”也是人類心性結構中對立的善、惡兩極的象征和文學形象。正是由于心性上善、惡對立,才導致了神、魔行為的差異和對立,才使雙方成為封建世俗道德的維護者和破壞者。因此,神與魔的對立和斗爭又象征了人性中“善”戰勝“惡”,即“去欲就真”的道德傾向和艱難過程。在小說《西游記》當中,由于孫悟空實為“人心”之象征,因此小說中有關他的故事自然寓含著修心去欲之意。
小說在講述孫悟空不復管轄、藐視權威的任性妄作行為后,開始描寫這個人物性格的變化,寓含著去欲歸真之意。小說將抑制孫悟空行為的“緊箍咒”定名為“定心真言”;將孫悟空受神佛降服,加入取經行列稱為“心猿歸正”,或直稱之為“修心”。為了強化孫悟空作為去“欲”就“善”象征的意義,作者還一再讓他本人來宣傳去欲修心,“明心見性”之理。如小說第八十五回,孫悟空又告訴師父:“心凈孤明獨照,心存萬境皆清,差錯些兒成惰懈,千年萬載不成功”,直接指明取經的成敗在于內心的修煉,在于是否能去欲還清虛之本。
這些都表明,孫悟空乃是作者用來說明去欲歸真,明心見性之理的文學形象,是棄“惡”就“善”的象征。除了主人公孫悟空外,《西游記》另外幾個主要人物也是謫降天仙,也是受欲望之害而失去仙職。如豬八戒,原為天宮天蓬元帥,因心發淫意,調戲仙女而受罰,投胎豬腹;白龍馬因不孝而謫;沙僧在天庭打碎圣盞,唐僧輕慢輕教,不聽說法,這些皆是心性不凈,欲望藏身的表現。從這兒看,《西游記》作者在解釋人的行為過失時,皆追溯至心性之“欲”。因此,只有去除欲念,才能獲得內善,重歸天界。“西天取經”象征的正是一個修心去欲的過程。
參考文獻:
1、吳承恩 著;黃肅秋注釋;李洪甫校訂《西游記》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3版
2、朱一玄 編;《西游記》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2年 02 月
3、席光偉 《西游記里的妖精們》,知音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
4、石昌渝 著 《中國小說源流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3年
5、《西游記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