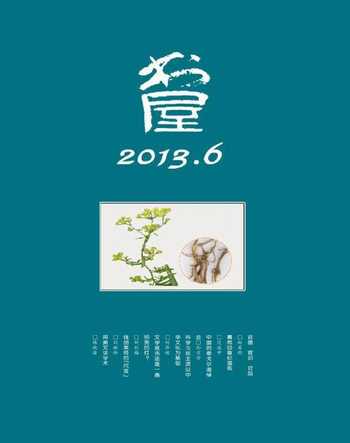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另議
張曉唯
1925年至1929年間存續(xù)的清華研究院國學(xué)科(亦稱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因為邀聘到梁啟超、王國維兩位冠絕一時的學(xué)問大家,且輔之以留洋歸來前程似錦的青年才俊趙元任、陳寅恪、李濟(jì)諸人,極大吸引了中國社會自科舉廢后難覓出路的國學(xué)后生。在清華園內(nèi)西方大學(xué)體制與傳統(tǒng)書院精神的混合氛圍中,教學(xué)契合,師生兩得,呈現(xiàn)“五四”之后雖然短暫卻光耀一時的國學(xué)教育勝景,以致令后人艷羨不已,交口稱頌。可是,這個“畸形機構(gòu)”真正的好時光不過一、二年,其運行軌跡呈逐年下降趨勢,最終難以為繼表面看來是王、梁兩位大師先后駕鶴西去、清華校內(nèi)大學(xué)部與研究院之間因經(jīng)費之類的利益博弈所致。實則,國學(xué)研究院的“書院取徑”與清華的現(xiàn)代大學(xué)體制之間難以兼容,致使國學(xué)研究院的生長空間日漸逼仄,以致不得不停辦。
一
上世紀(jì)二十年代教育界的“改大”(升格為大學(xué))之風(fēng)、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整理國故”的強力吁求以及美國決定退還第二批庚款的利益驅(qū)動,促使清華同期成立大學(xué)部和研究院兩個新設(shè)機構(gòu),欲求走出昔日留美預(yù)備學(xué)校的有限格局,開拓更廣闊發(fā)展空間。清華學(xué)校的獨特性,使其具備如此的財力和預(yù)期實力。創(chuàng)辦研究院的初衷是多科并舉,整體推進(jìn),可是國學(xué)優(yōu)勢一枝獨秀,竟演變成大冠之下獨木支撐,且有喧賓奪主之勢。當(dāng)年的清華校長曹云祥可謂頗有作為,正是在他任內(nèi),學(xué)校的“改大”進(jìn)程邁出實質(zhì)步伐,又順從“輿情”,開啟清華“教授治校”機制。他啟用《學(xué)衡》主編吳宓籌辦研究院事宜,使得這位自“東南大學(xué)校長風(fēng)潮”之后流落東北的“潦倒學(xué)人”有了用武之地,驟然煥發(fā)出活力。
吳宓乃哈佛碩士,而國學(xué)根基深厚,尤為突出的是他的學(xué)術(shù)識力和眼光,他對早年陳寅恪的賞識和推重,帶有幾分預(yù)見性。在籌組清華研究院過程中,他充當(dāng)執(zhí)行人角色,作用非比尋常。王國維和梁啟超二位接受清華禮聘,均為吳宓躬身親為,特別是王國維先生深感這位籌備主任雖具西洋教育背景,卻肯深施大禮誠待學(xué)人,顯現(xiàn)古人禮儀風(fēng)范,遂放下往昔“矜持”身段,慨然應(yīng)允舉家遷入清華園。其后吳宓又與觀堂先生熟商,訂立研究院章程,奠定了該機構(gòu)的基本“法度”。此外,推薦和聘任陳寅恪來清華執(zhí)教,吳宓應(yīng)居首功。隨著諸位大師相繼到來,研究院國學(xué)科的籌建順風(fēng)順?biāo)瑓清蛋l(fā)展國學(xué)研究院的雄心也變得愈發(fā)膨脹。
言及國學(xué)研究院的創(chuàng)建,胡適和梁啟超二人的作用不可輕忽。胡適作為“史前”的清華人,又是“整理國故”倡導(dǎo)者,他對國學(xué)研究院的構(gòu)想和建言,幾乎全盤為曹校長所接受,清華方面亦曾請他出任“山長”角色,胡適自然敬謝不敏。梁啟超從民國政壇敗退下來,雖思伺機再起,然“講學(xué)”風(fēng)氣已自北大彌散開來,任公反而要跟著走了(梁漱溟語)。他不甘在思想學(xué)術(shù)上落于人后,力求找回屬于他“自己的時代”,二十年代他設(shè)帳南開,又講學(xué)東南、清華等學(xué)府,儼然回歸學(xué)界。然外界仍以研究系魁首目之,講學(xué)舉動似屬韜晦之略。可是任公的“趣味主義”確乎真實存在,他與清華校方的淵源非同一般,國學(xué)研究院的醞釀顯然也有他的推力因素。他在清華時的助教蔣善國憶述:“其實國學(xué)院機構(gòu)之成立,完全由于任公一人之提倡。”雖稍嫌夸張,卻也道出了梁的特殊影響力。任公日后在清華得享“特殊禮遇”,多少佐證了此類說法。
許多研究者交口稱道“研究院章程”,贊其具有典范意味。該機構(gòu)的宗旨為“研究高深學(xué)術(shù),造成專門人才”,在先設(shè)國學(xué)一科的情況,研究內(nèi)容主要為中國文史哲及語言,培養(yǎng)目的為“以著述為畢生職業(yè)者和各級學(xué)校之國學(xué)教師”。關(guān)于研究院教員,分為教授和講師,教授須“宏博精深、學(xué)有專長之學(xué)者”,講師須“對于某種學(xué)科素有研究之學(xué)者”。專任教授與特別講師的區(qū)別,主要是專職與兼任之不同。關(guān)于學(xué)生,錄取資格相對寬泛:大學(xué)畢業(yè)生或具有相當(dāng)程度者;學(xué)校教師或?qū)W術(shù)機關(guān)人員,“具有學(xué)識和經(jīng)驗者”;具有經(jīng)史小學(xué)等根柢的自修之士。入學(xué)考題分為三部分:一、“經(jīng)史小學(xué)”基礎(chǔ)問答題;二、作文;三、在中國文、史、哲、經(jīng)學(xué)、小學(xué)、外文(英或法或德文)、自然科學(xué)(物理或化學(xué)或生物)及語言學(xué)八門中任選三門作答即可。顯然,具有文史根柢者可以從容選答,發(fā)揮特長,順利過關(guān)。無論師、生,均須“常川住宿,屏絕外務(wù),潛心研究”。學(xué)生免交學(xué)費及住宿費,每學(xué)期交膳食費約三十五元,預(yù)存賠償費五元,零用支出自備。學(xué)生在校研究以一年為期,完成論文且合格者,準(zhǔn)予畢業(yè),遇選題較難而成績較優(yōu)者,經(jīng)教授同意,可續(xù)行研究一至二年。
該章程的特色部分在“研究方法”一項,開列九條之多。開宗明義即“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xué)(導(dǎo)師)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dǎo),其分組不以學(xué)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xué)員與教授關(guān)系異常密切,而學(xué)員在此短時期中,于國學(xué)根柢及治學(xué)方法,均能確有所獲”。這里的不以學(xué)科分組,而以教授個人為主,凸顯了教授自主作用,隨后成立的五個研究室,即分別由梁、王、趙、陳及李濟(jì)主導(dǎo)。開學(xué)之初,教授公布指導(dǎo)范圍,學(xué)員自由選擇導(dǎo)師,師生間確定指導(dǎo)關(guān)系后,“教授于專從本人請業(yè)之學(xué)員,應(yīng)訂定時間,常與接談,考詢成績,指示方法及應(yīng)讀書籍”。此外,教授還須承擔(dān)“普通演講”,每星期至少一小時,“本院學(xué)員均須到場聽受”。“章程”要求“教授學(xué)員當(dāng)隨時切磋問題,砥礪觀摩,俾養(yǎng)成敦厚善良之學(xué)風(fēng),而收浸潤熏陶之效”。師生兩方面教與學(xué)均具主動性,在密切接觸請業(yè)之中增進(jìn)情感,傳承學(xué)術(shù),培育學(xué)風(fēng)。
近代學(xué)校體制引入中國后,教育界有識之士漸漸感到學(xué)校教學(xué)過程生硬機械,昔日書院那種師生間情誼融融的氣氛難以再現(xiàn),像梁漱溟、錢穆之類自學(xué)成才者對于大學(xué)環(huán)境均感不適。作為補救之道,希冀將傳統(tǒng)書院精神融入近代學(xué)校體制,以收兩全其美之效,清華研究院章程實則此類努力的有益嘗試。應(yīng)當(dāng)說,在國學(xué)研究這一特定領(lǐng)域,大師級學(xué)者形成“學(xué)術(shù)磁場”,眾弟子環(huán)繞周邊觀摩請業(yè),不難形成人們想望中舊時書院的那種預(yù)期效果。該章程從制度層面構(gòu)設(shè)復(fù)制了古代書院再生于近代學(xué)校體制之內(nèi)的綺麗場景。從當(dāng)年學(xué)生的憶述文字中,后人分明感觸到那種理想的教育境界,這應(yīng)是該章程獲享贊譽的主因所在。
二
就實施層面而言,清華以其特殊財力和地位,確乎出手不凡,禮聘到梁啟超、王國維兩位大師級學(xué)者及潛力無限的青年才俊。相比較北京大學(xué)研究所國學(xué)門此前僅聘請羅振玉、王國維為通信導(dǎo)師,且為時短暫的情形,清華方面明顯勝出一籌,這也與清華的政治色彩較北大淡漠有關(guān)。在羅、王之學(xué)已成“顯學(xué)”的背景之下,潛心考訂古學(xué)、成果豐碩的王國維受到各方服膺,其保皇之政治立場反而為人們所忽略不計。觀堂先生常年追隨羅振玉,受益多多,其轉(zhuǎn)向古學(xué)即受雪堂影響,而偏于守舊,亦與羅相關(guān)。他基本上屬于自修成名,無疑天分極高,然若無羅氏及東洋學(xué)圈的陶染,能否達(dá)此高峰,恐亦難說。他自日本返滬后,在哈同花園內(nèi)的倉圣明智大學(xué)任教,游離于國內(nèi)正規(guī)高等教育界之外。當(dāng)其學(xué)術(shù)地位已成,北大以蔡元培校長之尊,佐以沈兼士、馬衡等碩學(xué)人士請其“出山”,由此才開啟了其真正意義上的大學(xué)執(zhí)教生涯。惜之因為北大一篇指斥皇室之文惹惱觀堂先生,竟憤然斬斷與最高學(xué)府的這段因緣。隨著溥儀出宮,王氏失去“南書房行走”一職,就在他生計無著落之時,清華研究院為他提供了理想去處。在清華園的兩年,是王國維一生中的最后時光,他的生活得以安頓,內(nèi)心怡然,其學(xué)術(shù)成就更得到一個被廣泛認(rèn)可和傳承的天賜良機。從最終結(jié)果看,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可謂他一生歷經(jīng)“漂泊”之后的最好歸宿。
比王國維年長四歲的梁啟超,一生跌宕起伏,大部分時間處于時代的風(fēng)口浪尖,而最后十余年則相對穩(wěn)健沉寂。他的公共形象主色調(diào)無疑屬政治中人,可是“輿論驕子”和文章高手,又使他在清末思想文化界獨步一時。與默默治學(xué)功底深厚的王國維不同,他應(yīng)是那種“感應(yīng)敏速而能發(fā)皇于外”的文墨快手。他的時代感和趣味導(dǎo)向,從外部看來顯得“流質(zhì)易變”,似乎有歉深沉,可是異乎尋常的才氣和原本并不缺乏的定力,在年逾不惑之后,竟在國學(xué)領(lǐng)域大放異彩,且一發(fā)而不可收。在他內(nèi)心一定有著與“五四”新文化派(如胡適)一較高下的強烈沖動,當(dāng)政治上東山再起的可能越來越渺茫之時,便愈加傾力于學(xué)術(shù)和教育。他籌謀在天津設(shè)立半學(xué)校半書院性質(zhì)的“文化學(xué)院”,顯然他同樣深信:“沒有不在政治上發(fā)揮作用的思想和文化。”在諸事不成之后,清華研究院的籌辦為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現(xiàn)成平臺。后來任公自述:身體久病,獨拳拳于清華,難于割舍。可見他對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的依戀,有些出人意表之外。在清華,雖有人以“政客”目之,亦有學(xué)生微責(zé)其學(xué)問半為“入門之學(xué)”,但畢竟“跟隨從學(xué)者”(請其指導(dǎo)論文之學(xué)生)為數(shù)最眾,大體超過觀堂先生一倍之多。即使在舊學(xué)尚有吸引力的時代里,青年學(xué)子也更傾心于像梁啟超這樣才華橫溢、知名度高、社會資源充盈的特殊學(xué)者。梁任公在清華縱然難以忘情于政治,然其導(dǎo)師本職(至少在前期)做得中規(guī)中矩,游刃有余,其精神追求在此覓得最佳棲息之所。國學(xué)研究院第一屆學(xué)生周傳儒即指出:任公在清華“實為一生用力最專、治學(xué)最勤、寫作最富之時期。……其實欲包舉二千年來中國學(xué)術(shù)文化合于一爐而冶之”。就此而言,執(zhí)教清華成為他終結(jié)多姿多彩人生的命中歸宿。
學(xué)界常以所謂“四大導(dǎo)師”顯示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的師資實力,據(jù)說這源自時任清華教務(wù)長的張彭春之口。實則,趙元任、陳寅恪初入清華時的聲望遠(yuǎn)不能與王、梁二位比肩而論,他們畢竟剛剛留學(xué)歸來,趙雖有博士學(xué)銜,且在美國大學(xué)一度任教,仍屬初出茅廬;而陳雖博學(xué),然知識構(gòu)成帶有明顯個性特征,不易融入學(xué)校課程體系之中,難免所謂“曲高和寡”窘境。事實上,趙元任擅長的“語音學(xué)”,陳寅恪掌握的多種“已然死亡的語言”和西方漢學(xué)中的東方文獻(xiàn)之類,在具有不同程度國學(xué)根柢的學(xué)生們看來,西洋背景過于濃重,與他們所理解和認(rèn)同的國學(xué)內(nèi)容頗有距離,以致難以接受。研究院第一屆學(xué)生曾經(jīng)集體抵制趙元任的“語音學(xué)”考試,也甚少有學(xué)生請趙作論文導(dǎo)師,加之元任先生經(jīng)常外出進(jìn)行語言調(diào)查,在校時日有限。
陳寅恪上課,多數(shù)學(xué)生感覺“程度不夠”,沒有興趣,幾乎沒有人請陳先生指導(dǎo)論文,盡管課下交流學(xué)生們也承認(rèn)陳師學(xué)問淵博。“生源興旺”的前兩屆學(xué)生中,絕大多數(shù)請梁啟超、王國維作論文導(dǎo)師,只個別學(xué)生跟從趙元任、李濟(jì)(特別講師)研究語言或人類學(xué)。處境尷尬的陳先生曾作詩調(diào)侃眾學(xué)生師從梁、王二師乃“南海圣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xué)少年”,既是揶揄,也似自嘲。有學(xué)者指出,在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的不妙處境,促使陳寅恪學(xué)術(shù)轉(zhuǎn)向中古史,在魏晉隋唐史領(lǐng)域成就斐然。然而那已是“后清華”時期獲得的榮耀,將之前移至國學(xué)研究院時期加以稱頌,不僅時間錯位,也勢必遮蔽前期的真實情景。趙元任的情況也大體如此。趙、陳在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尚是學(xué)界新人,以其潛在學(xué)養(yǎng)而論,他們的學(xué)術(shù)前程實際是以“清華前期”為起點蹣跚顛簸著揚帆起航的,而并非“天才嬰兒”的第一聲啼哭就是一首小詩。
三
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先后招收四屆學(xué)生,第一屆新生二十九人,第二屆新生二十九人,第三屆新生十三人,第四屆新生三人,四年畢業(yè)生總數(shù)七十人。首屆學(xué)生入學(xué)考試,科目雖多,然幾乎不出經(jīng)史小學(xué)范圍,招致校內(nèi)一些人詬病。第二年入學(xué)考試明顯增加了題量和難度,并與所選學(xué)科掛鉤。前兩屆考生中,出身中小學(xué)教員者占將近百分之四十七,具有大學(xué)學(xué)歷者占近百分之三十二,平均年齡為二十四歲,高低年齡差達(dá)十四歲之多。學(xué)生年齡偏大,卻有社會閱歷,且文史根柢相對厚實,一些人此前已有著述。有研究者認(rèn)為,總體上他們的實際學(xué)力高于現(xiàn)今文史專業(yè)研究生,但也有學(xué)者指出,由于考生的整體學(xué)歷偏低,尚不能稱作與本科相銜接的研究生教育。第一屆畢業(yè)生公布成績,排列等級,頒授獎學(xué)金,比較正規(guī)。第二屆畢業(yè)生既未排列成績,亦未發(fā)獎學(xué)金,僅舉辦成果展覽。第三屆畢業(yè)生因評閱成績的梁啟超正在病中,尚未給出成績,因而未公布成績,連畢業(yè)證書亦遲發(fā),屬后補。可見研究院辦學(xué)的大致走勢。全部畢業(yè)生中,研究中國文學(xué)者居多,其次為中國歷史、哲學(xué)及其他,他們離校之后,從事本業(yè)者比重相當(dāng)高,其中三分之一在文史類領(lǐng)域頗有成就。這一結(jié)果應(yīng)當(dāng)說頗為豐碩,與當(dāng)年梁任公對眾弟子的預(yù)估大致吻合。不過倘略微苛刻評說,則不免聯(lián)想起章太炎曾發(fā)過的高論,大意是說: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因大國手的門生,往往恪遵師意,不敢獨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顧炎武門下,高者不過潘耒之輩;而二國手的門生,在老師的基礎(chǔ)上,不斷前進(jìn),往往能青出于藍(lán),如江永的門下,就有戴震這樣的高足。人們留意到,國學(xué)研究院學(xué)生們的專業(yè)范圍比較狹窄,遠(yuǎn)遜于他們導(dǎo)師的博學(xué)程度,這在近代中國大概也屬無可奈何之事。
當(dāng)然,大師與弟子們的教學(xué)細(xì)節(jié)不乏生動之處。梁啟超顯然著力營造書院式氛圍。在第一屆學(xué)生開學(xué)典禮后的茶話會上,他特別講述了“舊日書院之情形”,有些懸為高鏡意味。他倡導(dǎo)“養(yǎng)成做學(xué)問的能力,養(yǎng)成做學(xué)問的習(xí)慣”,大談治學(xué)方法和“論文式研究”,進(jìn)而主張“治學(xué)與做人并重”,形成一種“尊師重道”風(fēng)氣。任公具有“通儒”資質(zhì),他的底蘊是希求“經(jīng)師人師合一,道德學(xué)問打通”,將個人與社會、學(xué)術(shù)與政治連成一片。學(xué)界評價他“所長在通識,考據(jù)無甚稀奇”,學(xué)生們回憶他授課時才氣縱橫,對史料如數(shù)家珍,誠可謂“巴州詩句澶州策,信手拈來盡可驚”。可是梁啟超在學(xué)生們面前對同事王國維表現(xiàn)出充分尊重,他在校內(nèi)演講時說:“教授方面以王先生最為難得,高我十倍。”王國維的為師風(fēng)范則是另一景致,據(jù)弟子徐中舒追憶:“余以研究考古故,與先生接談問難之時尤多,先生談話雅尚質(zhì)樸,毫無華飾。非有所問,不輕發(fā)言;有時或至默坐相對,爇卷煙自遣,片刻可盡數(shù)支;有時或欲發(fā)揮,亦僅略舉大意,數(shù)言而止;遇有疑難問題不能解者,先生即稱不知,故先生談話,除與學(xué)術(shù)有關(guān)者外,可記者絕少也。”雖則寡言,卻難掩學(xué)問的深厚,以至連清華校仆亦聞知:拖發(fā)辮者乃本校最有學(xué)問之人。
王國維在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所作“普通演講”的題目先后有:古史新證、說文練習(xí)、古金文學(xué)、禮記、尚書等,基本為其研究心得。他在前兩個學(xué)年公布的指導(dǎo)學(xué)科范圍是:經(jīng)學(xué)(書、詩、禮)、小學(xué)(訓(xùn)詁、古文字學(xué)、古韻)、上古史、金石學(xué)、中國文學(xué),顯示出專精的特點。梁啟超“普通演講”的題目則有:中國通史、歷史研究法、儒家哲學(xué)、讀書示例—荀子等,其前兩年指導(dǎo)學(xué)科范圍是:諸子、中國佛教史、宋元明學(xué)術(shù)史、清代學(xué)術(shù)史、中國文學(xué)史、中國哲學(xué)史、中國文化史、東西交通史、中國史、史學(xué)研究法、儒家哲學(xué)、中國文學(xué)。其治學(xué)領(lǐng)域?qū)挿海髦荚谕ǎ容^接近現(xiàn)代學(xué)科分野。第一屆學(xué)生中(含舊制大學(xué)部學(xué)生三人)請梁指導(dǎo)論文者二十三人,請王指導(dǎo)論文者十二人。第二屆學(xué)生中(含上屆留院繼續(xù)研究者七人)請梁指導(dǎo)者二十二人,請王指導(dǎo)者十二人,請趙元任、梁啟超共同指導(dǎo)者一人,請李濟(jì)指導(dǎo)者一人。可見梁、王二師“人氣”之高。
國學(xué)教育向來尊崇“熟讀精審,循序漸進(jìn),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的學(xué)習(xí)領(lǐng)悟路徑,強調(diào)自主性。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自不例外,其自由論學(xué)之風(fēng)尤為可貴。第一屆學(xué)生姚名達(dá)在院學(xué)習(xí)三年之久,其間他修訂了王國維《觀堂集林》中的一處舛誤。他刊載于《國學(xué)月報》上的《友座私語》云:“靜安先生,稟二百載樸學(xué)昌盛之業(yè),值三十年史料出現(xiàn)之富,其所著作,皆有發(fā)明,考證至此,極矣。然對于新出史料,或昧其出土確地。如商三句兵,初以為出于保定清苑之南鄉(xiāng),有跋著在《觀堂集林》,嗣又手批云:‘后知三器本出易州。不知其所據(jù)者何人之言。而竟因此而斷為‘殷時北方侯國之器,‘商之文化,時已沾溉北上。又謂‘蓋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遠(yuǎn)至易水左右,‘則今保定(后改易州)有殷人遺器,固不足怪。先生蓋已深信其說不謬矣。然以吾聞之陸沂教授,則此三器實出陜西,陜西商人攜至保定,北京延古齋肆主陳養(yǎng)余君得之,以轉(zhuǎn)售于羅叔言參事,先生則又見于參事許,蓋以見聞授受,至五六次,真相漸昧矣。陳君昨年親語教授,此器斷非保定易州出。……讀先生之文者,幸留意焉。”可見即使大師亦不免疏漏,質(zhì)疑而非盲從,方可做真學(xué)問。
梁啟超在一次對學(xué)生的演講中,提及中國的蓄妾問題,語意略顯曖昧,大概緣于社會積習(xí)較深,未提出果決主張。留美預(yù)備部學(xué)生王政聽后不以為然,他寫《為蓄妾問題質(zhì)疑梁任公先生》一函遞交梁師。信中寫道:“由各方面觀察,蓄妾制均無存在之理由。吾國法律許置妾,是吾國法律的缺點,吾輩負(fù)有改造社會之責(zé)任,當(dāng)思所以補救之方。即事實一時不能做到,言論間亦不妨盡量發(fā)表。……政自幼讀先生偉著,以其思想新穎,立論精確也。今于蓄妾制一段雖不敢茍同,猶疑先生有未盡之論,故不揣冒昧,敢以上聞。”梁啟超閱罷此信,交給《清華周刊》公開發(fā)表,并在信后附上跋語,略作申論。自由論學(xué)之風(fēng),彰顯了“獨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學(xué)府內(nèi)涵。清華研究院第三屆學(xué)生藍(lán)文徵憶述當(dāng)年師生均“以學(xué)問道義相期”情形,稱該院“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fēng)”。第一屆學(xué)生吳其昌亦有此喻。南宋贛地的鵝湖、白鹿洞兩書院,承載當(dāng)年朱熹、陸九淵講學(xué)論道古風(fēng),以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比附之,應(yīng)是至高的贊許。
四
王國維早先論及學(xué)校教育曾說過:“一校之中實行教授之人多,而名為管理之人少,則一校之成績必可觀矣。”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機構(gòu)基本由教授、講師、助教組成,行政人員極少,且不乏兼職者。前兩年的辦學(xué)成績有目共睹,梁啟超不禁欣欣然:“吾院茍繼續(xù)努力,必成國學(xué)重鎮(zhèn)無疑。”同在北京城內(nèi)的北大研究所國學(xué)門雖成立在先,然清華的經(jīng)費、師資和環(huán)境均較之優(yōu)越,加之,清華的“密集謹(jǐn)嚴(yán)”勝過北大的“自由松散”,超越勢頭已然明顯。不過,初期主持院務(wù)的吳宓因為諸事順?biāo)欤叭惶岢鰯U(kuò)充研究院議案:增聘教授,擴(kuò)大招生名額,增加經(jīng)費預(yù)算,甚而主張專辦國學(xué)研究院,這實質(zhì)上更改了最初的“研究院章程”。在校務(wù)會議上,吳案遭否決,教務(wù)長張彭春針對性提議:“此后研究院應(yīng)改變性質(zhì),明定宗旨,縮小范圍,只作高深之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國學(xué)。教授概不添聘,學(xué)生甄取從嚴(yán),或用津貼之法,冀得合格之專門研究生。”該提議獲得通過。吳宓反對,要求復(fù)議,復(fù)議結(jié)果幾乎維持原議,只稍作緩沖。吳宓隨后辭去研究院主任一職,轉(zhuǎn)任外文系教授。其間,研究院教授們的態(tài)度耐人尋味:梁啟超堅定支持吳宓,而趙元任、李濟(jì)則贊同校務(wù)會議決定,王國維不置可否,態(tài)度模糊(陳寅恪尚未到校)。應(yīng)當(dāng)說,校務(wù)會議的決定帶有清華校內(nèi)的主流背景,擴(kuò)充計劃擱淺,國學(xué)研究院擴(kuò)張路徑被阻塞。
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由盛而衰的轉(zhuǎn)折,應(yīng)是王國維的自沉。原本被人們忽略不計的保皇因素,在南方北伐硝煙日近之際,忽然間“靈光一現(xiàn)”,令國人震驚,也使研究院師生哀鴻一片,這位大師的驟然離去,就國學(xué)研究院而言其影響可謂至深至巨。其后另一主干教授梁啟超由于身體欠佳等因,時常離校,致使“常川住院”規(guī)定形同虛設(shè),更帶來雪上加霜效應(yīng)。研究院第三屆新生王省對梁氏長時間缺課頗感義憤,向校方遞交意見書,要求有所匡正。校評議會僅含糊回應(yīng),引發(fā)王省不滿,遂投書《世界日報》,敦促清華評議會作出果斷決定。梁啟超提出辭職,引發(fā)清華校內(nèi)“挽梁”行動,評議會最終將王省開除,而暗中與此關(guān)聯(lián)的曹云祥校長和朱君毅教授亦相繼去職。不妨說,“王省事件”可能牽涉清華權(quán)力機構(gòu)(如董事會)的“內(nèi)爭”,似乎也隱含某些南方革命氣息因素。梁啟超就曾指斥國學(xué)研究院內(nèi)有國、共兩黨人員若干云云,其政治立場明顯對立,這未嘗不是激進(jìn)青年借故發(fā)難的緣由。經(jīng)此事件,研究院之衰相愈加顯現(xiàn)。梁啟超雖被慰留,但活力大減,終流于“通信導(dǎo)師”,與前期已不可同日而語。研究院后期,陳寅恪幾乎獨力支撐,增聘了馬衡、林宰平二位兼職講師,亦曾邀聘章太炎、羅振玉和陳垣諸位,希圖重振雄風(fēng),卻均未如愿。
原本西學(xué)氛圍濃重的清華園,竟然出現(xiàn)一個大師云集的國學(xué)院,耗費甚巨不說,其勢頭亦蓋過科學(xué)諸科,校園中的困惑和質(zhì)疑始終不斷。有統(tǒng)計顯示,1911年至1929年間清華留美學(xué)生總計一千一百余人,其中學(xué)工科者為百分之三十一,學(xué)理科者為百分之十,學(xué)商科者為百分之十一,學(xué)政法經(jīng)濟(jì)等科者為百分之二十五,學(xué)農(nóng)醫(yī)者近百分之十一,學(xué)文史哲者為百分之七,學(xué)軍事者為百分之二,其他百分之三。可知,選擇理工農(nóng)醫(yī)等實科者過半,選擇社會科學(xué)及商科者達(dá)三分之一強,而文史哲學(xué)生不足十分之一,如此的校園學(xué)科傾向,形成國學(xué)研究院揮之不去的外部壓力就不足為怪了。究竟科學(xué)與國學(xué)孰先的問題,實則已有答案,此乃近代社會發(fā)展大勢使然。“整理國故”之風(fēng)確曾吹進(jìn)清華,據(jù)賀麟回憶:清華學(xué)生中曾流行攜帶《資治通鑒》、《文選》、《十三經(jīng)注疏》及諸子等線裝書出洋。然而從學(xué)科分布來看,畢竟為少數(shù)。即使贊譽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的學(xué)者亦承認(rèn):該院主要導(dǎo)師“不恰當(dāng)?shù)剡^分迷戀舊文化”。在清華決意“改大”,努力靠攏現(xiàn)代大學(xué)體制進(jìn)程中,越發(fā)感到國學(xué)研究院自成系統(tǒng),同其他教學(xué)機構(gòu)不相銜接,與大學(xué)體制難以融合,呈現(xiàn)結(jié)構(gòu)性矛盾,因而對其批評之聲也就不絕于耳。
身為大學(xué)部文科教師的哈佛博士錢端升,從一開始就反對設(shè)立研究院,主張辦大學(xué)須優(yōu)先筑牢文理科基礎(chǔ),然后發(fā)展應(yīng)用學(xué)科,國學(xué)固然重要,但無需設(shè)專門機構(gòu),那樣既靡費資金,又導(dǎo)致管理混亂,像梁啟超、王國維如此令人尊仰的學(xué)者應(yīng)納入大學(xué)文科之中發(fā)揮作用。理科教授陳楨則從學(xué)科均衡角度批評“考古優(yōu)先”做法,提出應(yīng)重點培育社會急需的自然科學(xué)。教育學(xué)教授邱椿指責(zé)研究院只設(shè)國學(xué)科乃是畸形發(fā)育,國學(xué)“高高在上”壓低其他學(xué)科,實屬復(fù)舊。清華“改大”前后,一批本校畢業(yè)留美學(xué)成歸來回校任教的少壯派教師漸成主導(dǎo)力量,他們引領(lǐng)學(xué)術(shù),積極參與校政,力主教授治校,錢端升等便是其代表。
因而,與吳宓擴(kuò)充國學(xué)研究院計劃遭遇頓挫幾乎同時,教職員大會于1926年4月中旬通過《清華學(xué)校組織大綱》,其中規(guī)劃籌組與大學(xué)本科相銜接的大學(xué)院,“至民國十九年(1930)大學(xué)院成立后,研究院即行停辦”,這既留出了過渡性階段,也規(guī)定了研究院的“大限”,內(nèi)中清華各種力量間的博弈已清晰可見。即使王國維、梁啟超二位大師健在如初,國學(xué)研究院的命運恐怕也難以逆轉(zhuǎn)。可是,由于清華學(xué)生會的介入和強烈要求,大學(xué)院“早產(chǎn)”,研究院隨即終結(jié)。大學(xué)部學(xué)生們的訴求更多出自利益考量,他們指責(zé):“國學(xué)研究院人數(shù)極少,而所耗甚巨,影響于清華之發(fā)展實大。”此處的“所耗甚巨”,應(yīng)指國學(xué)研究院教授高薪、學(xué)生免繳學(xué)費、圖書購置費數(shù)額過大等項。王國維的聘書明文規(guī)定:“每月薪金銀幣四百元,按月照送”;梁啟超的薪酬尚難查考,但從清華校方為他提供號稱“外國地”的北院2號住宅遠(yuǎn)勝過其他三位導(dǎo)師的南院房舍推測,其收入應(yīng)高于王、趙、陳諸位。清華一般教授月薪到了羅家倫時代經(jīng)大事興革方達(dá)到三百六十元以上,大學(xué)部學(xué)生每年須繳納學(xué)費四十元,羅校長減免為二十元,學(xué)生尚不滿足,要求全免。待遇相對特殊,應(yīng)是國學(xué)研究院頻遭責(zé)難的另一因由。
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停辦是在1929年6月,擬議中的取代機構(gòu)大學(xué)院提前試辦,國學(xué)院送走最后一批畢業(yè)生即告壽終正寢。校長已是國民政府派來的羅家倫,在他任內(nèi)國立清華大學(xué)正式成立。國學(xué)研究院“孑遺”陳寅恪先生轉(zhuǎn)入文科,獲中文系、歷史系雙聘待遇,實乃研究教授。不過,他的重心似乎在新創(chuàng)設(shè)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他與舊清華同事趙元任、李濟(jì)分掌該所歷史、語言和考古三組。海內(nèi)堅守國學(xué)教育的專門機構(gòu),惟有私立無錫國學(xué)專科學(xué)校“綠樹常青”,那無疑屬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的一個“異數(shù)”。
(蘇云峰:《從清華學(xué)堂到清華大學(xué)(1911—1929)》,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孫敦恒:《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史話》,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朱洪斌:《清華國學(xué)研究院與新史學(xué)》,南開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未刊稿),2007年10月;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卞僧慧:《陳寅恪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