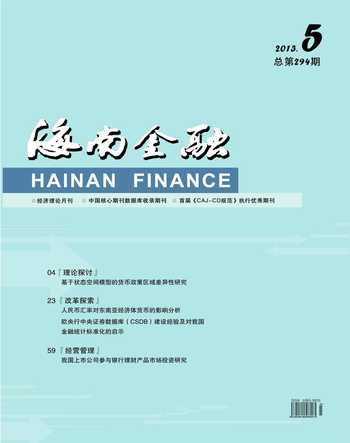人民幣匯率對東南亞經濟體貨幣的影響分析
盧孔標
摘 要: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波動與東南亞經濟體貨幣兌美元匯率波動相關性明顯提高,區域內匯率聯動性加強。通過對東南亞經濟體匯率參照貨幣實際構成與權重的計量分析,人民幣已經成為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經濟體匯率的參照貨幣。進一步鞏固和提升人民幣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需要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并加強區域匯率機制的協調。
關鍵詞:匯率;人民幣;人民幣區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3)05-0023-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5.05
一、引言
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下簡稱人民幣匯改)后,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便利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措施。人民幣貿易結算和資本項下人民幣業務快速增長。特別是與中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的國家持續增加,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快速發展。人民幣匯率對東南亞地區乃至全球其他經濟體貨幣的影響逐漸顯現,人民幣與東南亞經濟體貨幣匯率聯動趨勢明顯增強。
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2%以后,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斷推進。2007年5月21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日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三擴大至千分之五;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照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2012年4月16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千分之五擴大至百分之一。從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走勢來看,整體呈現單邊升值態勢(見圖1)。2005年7月匯改前后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2005年7月21日前,人民幣基本釘住美元;2005年7月21日-2008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保持升值態勢;2008年8月至2010年6月,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收窄,基本保持在6.83元/美元的水平;2010年6月至今,人民幣兌美元繼續升值,并呈現雙向波動幅度加大特征。截至2012年9月末,按照國際清算銀行口徑計算的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相對2005年7月末分別累計升值21.39%和28.76%。
東南亞經濟體貨幣隨著人民幣升值路徑的明確而普遍升值,并呈現匯率波動集群性變化的特征[1],這可以從兩方面得到驗證。第一,從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前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走勢與其他經濟體貨幣兌美元走勢的比較來看,馬來西亞林吉特、新加坡元、菲律賓比索兌美元匯率走勢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走勢較為一致(見圖1)。第二,人民幣與東南亞經濟體貨幣匯率波動的相關性不斷增強。2005年7月匯改前,人民幣與主要貨幣匯率波動之間的相關性均為負,且系數較低;2005年7月匯改后,人民幣與馬來西亞林吉特、菲律賓比索、新加坡元、泰銖匯率的相關系數大幅上升。主要東南亞經濟體貨幣匯率間的相關性也明顯加強,呈現區域貨幣聯動的趨勢。
人民幣匯率與東南亞經濟體匯率的聯動,可能是市場因素作用的結果(如面臨共同的外部沖擊),也可能是匯率機制安排和政策干預的結果(如一種貨幣釘住另一種貨幣導致匯率走勢一致),也可能是市場因素與政策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角度來看,本文更注重這種聯動背后隱含的匯率機制安排變化,即人民幣是否成為東南亞經濟體匯率的重要參照貨幣。為此,本文試圖回答三個問題:哪些東南亞經濟體關注人民幣匯率變化?人民幣在東南亞經濟體貨幣籃子(如果該經濟體實行實際的參照一籃子貨幣)中的權重多大?東南亞區域內是否真的已經形成“人民幣區”?
二、文獻綜述
判斷和衡量人民幣匯率對其他貨幣影響的一個重要角度是人民幣是否為貨幣的參照貨幣(reference currency),基本方法是估算各國匯率形成機制中貨幣籃子的構成和權重,這一框架最初由Haldane和Hall(1991)[2]、Frankel和wei(1994)[3]提出,被后續研究不斷借鑒和拓展。越來越多研究探討人民幣匯率對東南亞國家貨幣的影響,較一致的結論是,美元仍是本區域貨幣籃子的核心組成部分,而人民幣已經成為東南亞國家貨幣匯率的重要參照。Shu(2007)等[4]發現人民幣匯改后(2005年7月-2007年2月)人民幣對新加坡元和泰銖的影響系數超過日元和歐元,僅次于美元。Ito(2008)[5]指出如果剔除美元因素,僅考察人民幣和日元對亞洲區域經濟體貨幣的影響的話,人民幣的影響已經超過日元。Balasubramaniam (2011)等[6]發現,只有在人民幣不釘住美元的情況下,人民幣對其他經濟體匯率機制的影響才是顯著的,在其分析的132種貨幣中,32種貨幣受人民幣影響,但在2008年人民幣匯率釘住美元期間,人民幣影響力明顯下降。Henning(2012)[7]認為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和菲律賓等幾個東南亞國家已初步形成松散但有效的“人民幣區”,韓國正逐步加入,但美元仍然主導東亞地區的貿易、投資和儲備貨幣結構。Frankel和Wei(2007)[8]、Girardin(2011)[9]等研究關注人民幣匯率貨幣籃子的構成。國內關于人民幣匯率與東南亞經濟體貨幣關系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和估算其他貨幣在人民幣匯率所參考的一籃子貨幣中的權重[10-12],對人民幣匯率的溢出效應鮮有分析。
東南亞地區長期以來沒有匯率合作機制,匯率制度主動協調不明顯。對于東南亞貨幣匯率聯動以及人民幣區域影響力提升的原因,主流的觀點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深和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蘇應蓉和徐長生(2009)認為1997/98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匯率波動呈現出來的聯動趨勢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加深的結果,經濟結構相似、經濟周期趨同的東亞經濟體需要一致的匯率制度。Shu等(2007)沒有分析具體原因,但認為人民幣對亞洲貨幣的影響可能是亞洲經濟體政府政策選擇的結果,也可能是外匯市場壓力所致。Balasubramaniam 等(2011)認為人民幣匯率政策對其他經濟體匯率政策的溢出影響主要由兩個機制,一是和中國在全球出口市場上競爭的國家,會避免對人民幣升值以維持出口競爭力;二是作為亞洲生產網絡的組成部門,東南亞經濟體有必要降低和人民幣雙邊匯率的波動。Ito(2008)也認為維持出口競爭力是各國追隨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重要原因。Henning(2012)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中國在東南亞貿易和生產網絡中的重要性上升是人民幣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重要原因,中國的“結構性權力”并不能解釋人民幣的影響力,且“人民幣區”的協調與穩定有賴于美元的中間角色。Subamanian和Kessler(2012)[13]認為不能排除貿易競爭壓力導致東南亞經濟體參照人民幣匯率的可能性,不過人民幣的影響力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區域貿易一體化。
人民幣匯改采取的是漸進推進戰略,人民幣匯率變化因而具有非常顯著的階段特征,人民幣匯率對東南亞經濟體貨幣的影響在不同時間段亦呈現不同特點。現有研究一般以2005年7月為分界點劃分兩個考察區間,Henning(2012)和Subamanian和Kessler(2012)則將匯改后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劃分為三個時期,但二者在時間節點確定上并不一致。本研究在上述研究框架基礎上,根據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波動特征,進一步細分考察區間,并將研究時間進一步延長到2012年10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