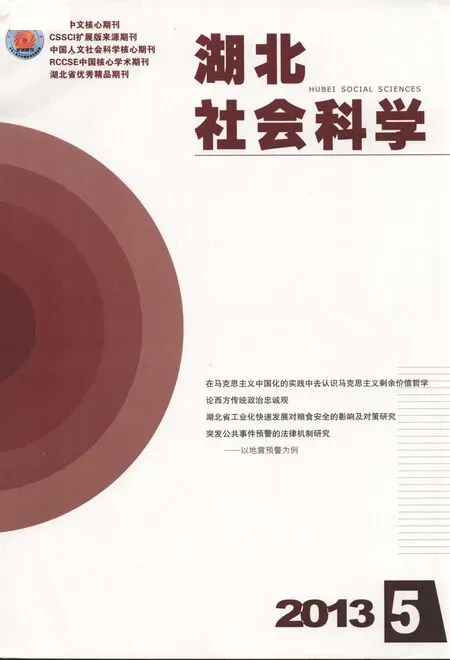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
——基于省級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
王瀅淇,闞大學
(1.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2.南昌工程學院經濟貿易學院,江西南昌 330099)
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
——基于省級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
王瀅淇1,闞大學2
(1.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2.南昌工程學院經濟貿易學院,江西南昌 330099)
根據2003-2011年度間的省級動態面板數據,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實證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得到以下兩點結論:一是全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回歸系數較小;二是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效果不明顯,均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為了更好地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應采取加大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以獲取技術溢出促進產業升級等措施。
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系統廣義矩估計
一、引言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很快,我國正從以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為主轉向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并重的階段,在“引進來”的同時,也在積極的“走出去”,但迄今為止,學術界的研究幾乎全部集中在“引進來”的經濟效應上,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至于“走出去”的經濟效應,雖然也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如學者們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的理論研究頗為深入,但實證研究不多。又由于外商直接投資所轉移的技術與我國產業現有技術的差距逐步縮小,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的邊際效應會出現遞減趨勢,以市場換技術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戰略是不能滿足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因此,筆者利用2003-2011年度間的省級動態面板數據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進行實證研究,一方面為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奠定堅實的實證基礎。另外一方面有利于我國更好地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二、國內文獻回顧
國內學者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的實證研究主要有范歡歡和王相寧(2007)利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實證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比例變化與第一、三產業結構比變動基本無關,僅與第二產業結構比有正的彈性系數比關系,從而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沒有明顯促進作用[1](p56-58);王英和劉思峰(2008)利用2003-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行業結構和國內產業結構的數據,通過計算灰色絕對關聯度、灰色相對關聯度和灰色綜合關聯度,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結果發現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與國內產業結構密切相關,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其中對于采礦業和制造業的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有著更為重要的促進作用[2](p61-66);馮春曉(2009)通過構建測度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的指標,利用15個制造業行業2003-2007年數據分析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對其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其產業結構優化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中與高度化相關性較強,而穩健性檢驗表明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其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且前者是后者的格蘭杰原因,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優化作用非常微弱[3](p97-104);潘穎和劉輝焊(2010)則根據我國1990-2007年數據,運用協整理論和Granger因果檢驗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對外直接投資短期不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長期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4](p102-104)。
由此可見,國內學者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的理論研究頗為深入,主要是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機理和路徑。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的實證研究不多。僅有的實證研究是基于時間序列數據或行業面板數據,時間序列數據是基于國家層面,實證結論缺乏針對性,而行業面板數據時間跨度較短,行業截面個數較少,實證結論缺乏可靠性,并且僅有的實證研究也沒有考慮到解釋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從而導致估計偏差,筆者利用2003-2011年度間的省級動態面板數據,運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克服內生性問題實證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
三、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根據以往的研究文獻,筆者設定了如下計量模型:

其中i表示第i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t表示第t年,Uit是隨機誤差項。
GF表示產業結構,大多學者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或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產值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本文采用后者,主要是因為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產業結構升級主要表現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值不斷增加,采用前者可能不能很好地衡量產業結構升級。對于第二、三產業產值和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用各地區國內生產總值指數(以2003年為100)進行了折算。至于加入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的GF,主要是為了涵蓋未考慮到的其他影響因素。
OFDI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通過獲取關鍵資源、轉移邊際產業、扶持新興產業、產業關聯、競爭示范效應、反向技術溢出等渠道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對于對外直接投資指標,筆者采用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來衡量,將各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按當年時間加權平均匯率調整。
Kd表示國內投資,國內投資是產業擴張的重要條件,國內投資的變化將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動,并且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經濟中將更多的投資于先進的技術設備,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筆者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減去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來衡量,首先用各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以2003年為100)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進行折算,然后將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按當年時間加權平均匯率調整,最后兩者相減得到國內投資。
TE表示技術進步,技術進步會導致原材料消耗水平降低,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引起產業中間需求結構和中間投入結構變化,改變投入產出關系,促進整個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產業升級;會提高勞動生產力,勞動力發生轉移,使產業結構升級;也會促進新興產業出現和成長,并使原有產業的產品不斷更新換代,從而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對于技術進步指標,大多學者用政府財政研發投入表示或者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通過索洛余值法測算的全要素生產率衡量,就前者而言,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度不高,技術進步大多并不依賴高風險和高資本的研發投入,而是依賴低風險甚至低資本投入的技術引進,因此,該指標很可能低估了我國的技術進步,對于后者,基于新古典生產理論建立的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方法有諸多前提和假定條件,如完全競爭市場、資本與勞動任意替代、要素充分利用、技術中性等,而我國幾乎不具備這些條件,所以通過索洛余值法測算的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技術進步指標難以說明我國的技術進步水平,又由于基于DEA方法測算的非參數Malmquist生產率指數不需要引入較強的假設,能更好地衡量技術進步,故筆者采用Malmquist生產率指數來衡量。為了計算Malmquist生產率指數,需要對資本存量計算,這里使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具體公式為Kit=Iit/Pit+(1-δ)Kit-1,其中Iit為第i個省份第t年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Pit為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以2003年為100),δ為資本折舊率,本文采用國際上慣常的做法,將其設定為5%,至于初始年份2003年各省份的資本存量,本文借鑒徐現祥(2007)的做法,通過下式求出Ki,2003=Ii,2003/(0.03+ Zi),其中,Zi為第i個省份2003-201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
IN表示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需求層次會隨之提高,消費結構也會不斷升級,由于第一產業產品收入彈性低于第二產業產品,第二產業產品收入彈性又低于第三產業產品,故收入水平提高會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對于居民收入水平指標,筆者采用各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
FD表示金融發展水平,金融發展通過資金形成、資金導向、信用催化和風險分散等機制作用于資金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使資金逐漸從回報率低的產業轉向回報率高的產業,加快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對于金融發展水平的衡量,主要有兩個指標:麥氏指標和戈氏指標,麥氏指標是廣義貨幣存量與GDP的比重,由于無法收集到各地區的廣義貨幣存量,這里采用戈氏指標即金融機構年底貸款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
TR表示對外貿易,通過對外貿易可以解決我國過剩的生產能力和產品結構性短缺,支撐產業結構調整;通過對外貿易可以彌補國內資源的不足,使相關產業的資源瓶頸消失,提高產業競爭力,并通過競爭效應、資源配置效應、關聯效應等途徑影響其他產業發展,從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通過對外貿易還可以發揮比較優勢,實現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對于對外貿易指標,筆者采用進出口總額來衡量,將各地區的進出口總額按當年時間加權平均匯率調整。
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彌補了國內產業資本的不足,其技術溢出機制優化了產業結構;外商直接投資也加劇了國內市場競爭,將低效率的企業從本行業中淘汰出去,從而優化了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對于外商直接投資指標,筆者采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來衡量,將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按當年時間加權平均匯率調整。
(二)數據說明。
文章選擇的樣本時間是2003年-2011年,25個省份,其中,東部地區有:北京、天津、上海、河北、遼寧、山東、廣東、江蘇、浙江和福建,中部地區有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區有內蒙古、廣西、四川、云南、陜西、甘肅和新疆(海南、重慶、貴州、青海、寧夏和西藏數據不全),其中2003-2008年各地區第二產業產值、第三產業產值、國內生產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勞動力、金融機構年底貸款余額、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總額的原始數據來源于《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2009-2011年的原始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2003-2011年各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來源于當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變量之間的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所以已經在設定模型時進行了自然對數變換。
四、實證分析
(一)內生性問題。
在這里由于可能會因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而導致估計偏差,內生性來源于以下幾種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作為動態項,該項易和隨機誤差項存在相關關系;二是產業結構升級往往伴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產業結構升級是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可能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的地區,原本產業結構水平就高;三是產業結構升級也是促進技術進步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原因之一,有可能技術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高的地區,原本產業結構水平就高;四是產業結構升級,不同產業的生產能力提高,使得出口產品質量提高以及對進口資源合理利用,從而促進對外貿易發展,即產業結構升級也是對外貿易增加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可能進出口總額高的地區,原本產業結構水平就高。可見,即使回歸結果表明產業結構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顯著,也不能斷言后者對前者有促進作用,這里最小二乘法已經不能一致和無偏地估計系數,文章使用廣義矩估計方法,由于差分廣義矩估計方法會損失一部分樣本信息,且工具變量存在弱有效性問題,在計量檢驗時,會出現檢驗無法通過的情況,并且,這里由于樣本數據年份較少,觀測值又較多的客觀限制,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文章更為適用,在進行系統廣義矩估計時,文章選取各解釋變量的部分已知值(原變量加滯后2期)作為估計的工具變量。
(二)實證結果。
筆者利用Stata軟件對全國、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進行估計,得到了全國、東部、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如表1所示,從回歸結果可知:
1.全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在10%顯著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但回歸系數較小,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規模還較小;二是我國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上具有盲目性,獲利不大,甚至虧損;三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重較小,這制約了我國通過轉移邊際產業和利用反向技術溢出效應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四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大部分分布在香港、新加坡、澳門、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等亞洲地區和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秘魯、巴西、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地區,而對技術先進的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較少,據筆者計算,對亞洲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約占總流量60.3%,對拉丁美洲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約占總流量26.9%,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僅占總流量5.8%,這制約了我國利用反向技術溢出效應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2.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在5%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效果不明顯,兩地區回歸系數的概率值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較大,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較小,就2003-2011年而言,東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占地方合計74.1%,而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分別占地方合計15.1%和10.8%;二是東部地區的境外企業數量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就2003-2011年而言,東部地區的境外企業數量占境外企業總數的六成以上;三是東部地區較中部與西部地區經濟發達,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轉移邊際產業和促進新興產業能更好地促進其產業結構升級;四是東部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金融發展水平和研發水平較高,能更好地吸收對外直接投資的反向技術溢出效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而中部與西部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金融發展水平和研發水平較低,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反向技術溢出效應吸收有限;五是東部地區的產業關聯度較高,其對外直接投資通過產業關聯渠道能更好地促進其他產業發展,使產業結構升級,而中部與西部地區的產業關聯度較低,制約了兩地區對外直接投資通過產業關聯渠道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并且,從表1中還可以看出,全國和三大地區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因素是國內投資和技術進步,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和FDI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而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和FDI并沒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原因可能在于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和FDI規模較大、質量較高、東部地區能更好地吸收對外貿易和FDI的技術溢出效應;而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和FDI規模較小、質量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產業結構同構化現象,兩地區可能因為對外貿易而專門從事傳統產品生產,外商也往往投資于兩地區的傳統產業,實行低層次產業外延擴張,并且兩地區對外貿易和FDI的技術溢出效應不明顯,吸收能力也較弱。此外,東部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發展水平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發展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效果不明顯,回歸系數的概率值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原因可能在于兩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低,制約了消費結構升級和金融發展水平低,金融機構的中介作用尚未充分發揮的緣故。

表1 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影響的實證結果
五、結論
為了更好地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第一,我國應鼓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要適當采取政策傾斜鼓勵中部與西部地區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此同時,加強政府宏觀指導,以減少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盲目性,獲取更多的海外收益,用于產業結構升級;第二,調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質量,增加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第三,加大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獲取他們的技術溢出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第四,東部地區尤其是中部與西部地區需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為私人人力資本投資提供補貼和融資以及通過增加勞動力市場的競爭性和流動性來刺激私人人力資本投資等辦法提高人力資本水平、要繼續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提高金融發展水平、要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研發水平,從而更好地吸收對外直接投資的反向技術溢出效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最后,東部地區尤其是中部與西部地區要提高產業關聯度,以便對外直接投資通過產業關聯渠道更好地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1]范歡歡,王相寧.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影響[J].科技管理研究,2006,(11).
[2]王英,劉思峰.OFDI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基于灰關聯的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8,(4).
[3]馮春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優化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9,(8).
[4]潘穎,劉輝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0,(2).
責任編輯 郁之行
F124.3
:A
:1003-8477(2013)05-0082-04
王瀅淇(1992—),女,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學生。闞大學(1982—),男,南昌工程學院經濟貿易學院講師,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