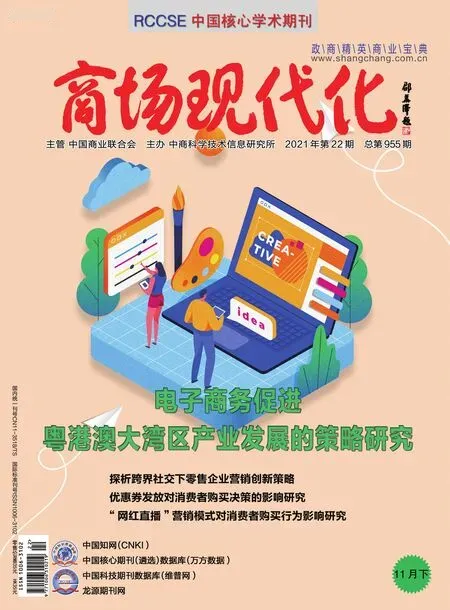個體創造力轉化為團體創造力的關鍵因素研究文獻綜述
■張發祥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一、團體創造力的重要性
美國心理學家R.J.Sternberg(1995)認為:在知識經濟時代,創造力已經成為一切有價值事物的DNA。在全球經濟快速發展,商業競爭愈演愈烈的21世紀,創新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而創新的根源在于創造力,Shally,ilson和 Blum(2000)指出創造力在任何職業中或任何員工身上都可能發生;在產業劇烈變革的背后,無論是企業還是科研院所,為了追求自身持續的競爭優勢,在創新過程中都需要處理大量的信息,同時做出復雜而正確的決策,這已遠遠超出個體科研人員的能力范圍,正如Bennis和Biederman(1997)指出:“個體問題解決這一孤獨的騎兵已經死去”;由于任何個體都不可能擁有創造和創新所需的全部資源、技術和知識,隨著開放式創新的提出,因此在創新的過程中團體創造力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研究個體創造力的基礎上,如何有效地將個體創造力轉化為團體創造力,達到“1+1+1>3”的協同效應,已成為團體創造力研究的重點。
二、創造力定義
自1950年美國心理學家Guilford發表《論創造力》的演講,到目前為止創造力的研究已超過半個世紀,但是研究人員還是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統一的創造力定義,主要由于研究人員對創造力的研究側重點和研究范式以及理論依據不同。對于創造力的定義,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理解:
第一,從過程角度來看,Wallas(1926)認為,創造性思維的經典模型將創造性思維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準備(研究要解決的問題和目標)、醞釀(不再刻意思考,但下意識的思索可能仍在發生)、啟發(方案自己浮出水面,即“靈光一現”)和確認(用邏輯和知識將創意變成適當的解決方案);Koestler(1964)認為,創造力類似一個雙邊的社會性過程,經過深思熟慮,將兩種本不相關的想法或事物聯系在一起,從而產生新的見解或發現。他主要強調了要以獨特的方式看待事物,要具有辨別新信息及用它來解決問題的能力;Stein(1967)將創造力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形成假設、假設檢驗和溝通;Parnes,Noller和Biondi(1977)提出了一個關于創造性思維過程的五階段模型:發現事實、發現問題和定義問題、產生創意、發現解決方案以及接受解決方案;Basadur(2004)、Basadur,Graen 和Green(1982)指出創造力包括持續地發現、解決問題并實施新的解決方案。
第二,從結果角度來看,一般來說將創造力定義為新穎的事物。Rogers(1954)將創造力定義為由于個人和情景(如環境、事件、人物)的獨特性而產生的新穎的相關產出;Amabile(1983)在Barron(1955)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創造力是個體或小型的工作團體所產生的新穎且適當的想法;在他們后續的研究中,將創造力定義為是新穎且實用的,包括了適當的創意、過程或程序。Amabile(1988);Mumford 和 Gustafson(1988);Shalley(1991);認為,創造力是一種知識的聯結與再排列在那些允許自己柔性思考的人們的頭腦中來產生新的、常常是令人驚奇但有用的新主意。
除此之外,基于創造力多層次的研究,如陳德輝,王續琨(2012)指出,個體創造力是個人創造動機、領域技能和創造技能的函數;團體創造力是個體創造行為、團隊創作和團隊執行的結果;組織創造力決定于團體創造力、組織特性和環境的擾動。
三、個體創造力的影響因素
在早期的創造力研究,特別是心理學的研究領域中,研究者主要關注了創造力個體的個人行為特征和創造結果。例如,Cox(1926)和 Galton(1870)研究了名人傳記和自傳,以確定是否存在對創造力有特別影響的人格特質或智力類型。Simonton自1975年開始通過研究檔案的方法,關注了歷史上的著名音樂家、藝術家、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創造性成果;Zukerman和Cole(1994)比較了著名科學家和普通人關于程序性知識的工作方法,發現著名科學家更注重戰略性方法和問題。以上這些個體層面創造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學方面,并且多以著名的科學家和藝術家為研究對象。
隨著對創造力研究的深入,研究人員將重點放在了員工的創造力上,并且逐漸認識到任何個體都具有創造力。Amabile構建的創造力成分模型是一種構成要素理論,它提出了一切領域產生創造性的必要和充分構成要素。她認為創造性產品的產生是三個基本成分相互作用的結果:領域相關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和工作動機。其中,領域相關技能包括在特定領域的事實性知識與專業技能;創造力相關技能,也叫創造力相關過程,包括與產生創造性思維的策略、適當的認知風格、產生創意的工作方式有關的顯性或隱性知識;工作動機包括內在的和外在的,主要是個體的工作態度和對于自己工作動機的感知。相對于Amabile的創造力成分模型而言,Woodman對創造力影響因素的考慮則更全面一些,他認為個體創造力是受人格因素、認知風格與能力、相關任務領域技能、動機和社會情景影響的一種功能。強調了個人的性格特征和工作環境中的情景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完全能夠預測創造性行為。就個人特征來說,包括了認知能力或風格、人格、內在動機和知識的重要性。Ford(1996)提出的個體創造力活動模型認為,個體的創造力活動室意義建構、動機、知識和能力的結合。Drazin,Glynn和Kazanjian(1999)針對長期的、大規模的組織項目研究發現,個體有自己的參考框架,創造力是個體對創造性活動的心理參與。Sternberg提出創造力的三側面模型,從智力、智力風格與人格三個側面解釋產生創造力的心理過程。
國內學者對個體創造力的影響因素的研究剛剛起步,陳德輝和王續琨(2012)從認知與非認知兩個維度出發分析了個體創造力的影響因素,指出認知(如知識、認知能力和偏好等)與非認知(如人格因素等)的影響:(1)創造者本性;(2)個人動機;(3)相關知識和技能;(4)創造技能(認知型態、認知能力和創造風格);(5)人格因素(自尊等);(6)先前環境背景(生活和工作經驗的強化等);(7)情境脈絡作用(如身體狀況、任務與時間的限制);(8)社會作用(如社會所提供的便利和回報)。其中(1)~(4)是正向作用,(6)和(7)主要是反向作用,(8)是可變的作用,既可以促進個體創造力也可能阻礙創造力的發揮和實現。
四、個體創造力轉化為團體創造力的關鍵因素
關于團隊創造力的定義的研究一直沒有得到共識,分歧在于團隊創造力主要是由個體創造力決定還是由團隊層面的獨特屬性或作用機制來決定的,本文將以上兩種觀點的相關文獻總結如表一,這些因素包括:團隊成員多樣性、認知風格、團隊創造氣氛、反饋和沖突。
第一,在團隊成員多樣性方面,Tjosvold,De Dreu,Porac&Howard認為:個體的不同帶來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點產生多重視角、分歧和沖突,如果這種信息型沖突的發生時以制定有效地決策和有效地執行任務為前提,而不是以獲勝、占上風或利益沖突為前提的,那么它反過來會促進績效和更具創造力的行為。
第二,在認知風格方面Amabile認為,在其創造力結構模式研究中則將認知風格看成創造技能的組成部分,并歸納出有利于創造的認知風格的特點:(1)打破知覺定勢;(2)打破認知定勢;(3)理解和欣賞復雜性;(4)盡量保持選擇的開放性;(5)延遲評價;(6)善于對信息進行多途徑歸類;(7)準確記憶信息材料;(8)突破舊“版本”;(9)有創造性地接受。
第三,在團隊創造氣氛方面ro-Osire;Orono,Ocker;傅世俠和羅玲玲;王黎螢,陳勁認為,通過信息分享、安全、互相影響和經常互動等子維度,是成員特征和成員互動對創造力產生重要影響;團隊任務和團隊環境對成員創造力發揮影響;團隊任務特征、成員特征、團隊互動以及領導支持和組織激勵制度是團隊創造氣氛的主要構成,但不同的團隊創造氣氛的具體內容有差異;科技團體創造氣氛的組成主要包括外部氣氛,內部氣氛和其它氣氛;不同團隊創造氣氛通過任務式和協作式兩類共享心智模型的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間接影響研發團隊創造力。
第四,在沖突與反饋方面Mumford,Gustafson;Nemeth,Owens;Tjosvold認為,對創造力和創新來說,對競爭觀點的恰當處理是關鍵問題;與任務有關的有意爭論在合作性的團體背景下會提高決策制定的質量和創造力;與任務的有關的沖突會使團體成員重新評估現狀,調整目標、策略、過程,以更好的適應現有情況。Farr,Ford;George,Zhou認為反饋對個體創造性業績有著有力地影響;有四個關鍵因素激發了接收反饋的員工的創造力,包括:反饋可以激發接受者的內在動機;可以影響員工的情緒;可以向員工澄清創造力產出的標準;可以促進接收者對創造力相關技巧和策略的掌握。
以上研究傾向于“解決團隊創造力的輸入端的表象特征,卻無法揭示其加工過程的黑箱”(王黎螢和陳勁,2010),即缺少針對影響團隊創造力作用機理的挖掘。第一,以上研究主要以Amabile和Woodman分別提出的兩個模型為基礎,同時可以看出對于創造力的研究已經由個體應具有什么樣的特征逐漸深入團體創造力的本質是什么。在早期社會和人格心理學研究領域中,主要以個體特征為主要研究對象,隨著對創新的認識和重視,創造力的研究重點有其構成,轉變為如何激發個體創造力,最終使團體創造力的效率最大化,達到“1+1+1>3”協同效應。第二,團體創造力的本質是,團隊以組織的形式將不同個體的知識和能力整合起來,通過發揮協同效應是整體的性能加以改善,基于認知視角的理論將“黑箱”逐漸打開。通過對認知理論的研究,特別是促進團隊協同合作的內隱認知的研究,如內因協同、共享心智和集體理解等概念的提出,對探索個體創造力與團體創造力的互動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第三,在團隊創新過程中,團隊創造氣氛會影響成員的動機、行為和態度。提升團隊創造力的另一驅動力就是激發團隊創造力的氣氛,可以根據不同的團隊構成和任務情景綜合創新的內外部氣氛。第四,員工的新奇想法往往是企業創新、變革及競爭力的基礎(Woodman,1993)。這些想法就是個體的反饋。關于反饋對創造力的影響的研究尚處于萌芽期,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與創造力相關的反饋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變為團體創造力的有效催化劑,管理者應有意的培養和提高個體的這種能力。第七,從整體上來看對沖突的相關研究,在個體都積極參與的氣氛中,適當的任務有關的沖突和適當的少數異議持有者,會通過鼓勵爭論而產生創新,同時也會使個體成員通過換位思考得到有益的信息,進而產生創造性解決問題的途徑。
五、研究展望
第一,基于內隱協調的多層次的創造力研究正在成為主要的研究趨勢。研究團體創造力時,對于由多種個體組成的一個團體來說,他們的這種“耦合”或者“聚集”,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分工的越來越細,同時合作越來越重要的,特別是跨專業的合作,內隱協調可以使不同層次的創造個體有序運行,實現“1+1+1>3”的協調效應,進而改變團體創造力,這就需要創建一個能夠整合如個體創造力、團體創造力和中間變量在內的多個模塊的模型。第二,細化對于創造力研究過程中影響因素的測量、設計和方法的研究是未來的研究趨勢。無論對創造力的研究是在實驗室中進行還是在組織中進行,都要對各影響因素進行設計和測量。在不同的行業和國家文化背景下,量表的開發和因素的選取應有不同的選擇,細化和豐富這些量表和方法還需要大量的實證研究。此外,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創造力都是好的嗎?都具有激勵性嗎?創造力一定會帶來績效的提高和組織效率的高效嗎?
[1]Basadur,M.S.,Graen,G.B.,&Green,S.G.(1982).Training in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Effects on ide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in an applied research organization.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30,41-70.
[2]陳德輝,王續琨.組織創造力的模型建構與實證分析.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2.09.第33卷第09期
[3]傅世俠,羅玲玲,孫雍君.科技團體創造力評估模型研究[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5,21(2):79-82
[4]王黎螢,陳勁.知識型員工心理契約結構探索和激勵機制研究[J].經濟管理,2008,(1):17-21.
[5]王黎螢,陳勁.2010c國內外團隊創造力研究述評。研究與發展管理,22(4):62-68
[6]WOODMAN R W,SAWYER JE,GRIFFIN R W.Toward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3,18(2):293ˉ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