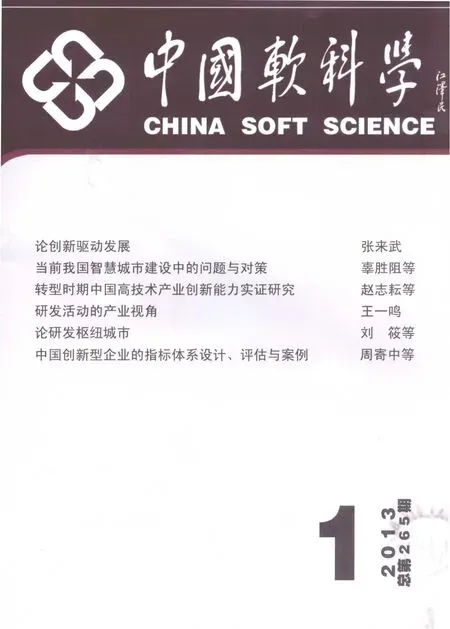研發活動的產業視角:一種新的象限模型
王一鳴
(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北京100084)
一、后學院科學背景下研發產業的形成
在19世紀中期以前,基本上所有的科學家都是業余愛好者(amateurs),幾乎沒有人依靠研究科學而謀生[1]。學院科學(academic science)標榜自己是為科學而科學的純學術科學,科學家的形象往往被建構成為一幅理想圖像:科學家都是“為科學而科學”(science for science's sake)的純粹意義上的科學家[2]。科學研究活動此時主要是一種業余的個體活動。在學院科學的理想化圖景中,科學家的職責僅限于進行本身的工作,了解科學而不是涉及國家或企業的研究事物。
齊曼(J.Ziman)通過研究科學發展的演變過程,認為經歷了200年左右發展歷程的學院科學發展轉化為具有新特征的后學院科學(post-academic science);他認為,后學院科學是學院科學向產業領域的延伸,是與實踐網絡緊密纏結在一起的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1]。而科學作為一種知識的生產方式,由過去的學院模式發展為后學院模式。正如齊曼所言(1996):學院科學正在經歷一場革命,它正在為后學院科學讓路,它與前者在社會學和哲學上不同,它將產生一種全新的知識概念[3]。吉本斯(M.Gibbons)等人認為,當前的科學研究正在形成模式2的知識生產模式,模式1是傳統的知識生產方式,主要是基于單學科內以認知為目的的知識生產。而模式2的生產方式是跨學科的(trans-disciplinarity),與模式1相比,模式2的知識生產擔當了更多的社會責任,涵蓋了范圍更廣的、臨時性的、混雜的從業者,他們在一些由特定的、本土的語境所定義的問題上進行合作[4]。這表明,科學研究和知識的生產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8年發布的《關于科學技術統計國際標準的建議》,研究與開發(R&D,簡稱研發)是一種重要的科技活動。科學技術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推動力,研發則是科技進步的的直接源泉[5]。后學院科學中的研發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經濟活動,不僅需要成本并且也會產生極大的經濟后果。科(D.Coe)和赫爾普曼(E.Helpman)等人進行了大量研究以量化技術變化與生產率增長之間的關系,他們研究發現,1990年西方發達國家代表——七國集團(G7)國家的國內研發支出的回報率平均為123%,而較小的幾個國家平均為85%[6]。這種有投入和產出的研發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產業活動。
某種意義上,創新就是研發和產業的有機結合。馬克盧普(F.Machlup)將研發活動包含在知識產業的知識生產中[7],美國經濟學家波拉特將馬克盧普提出的“知識產業”劃為國民經濟的第四產業,其中包括教育、研究與發展、信息、專家咨詢、專門建議等方面的服務。同時,我國學者胡鞍鋼等也認為知識產業包含R&D產業[3]。在后學院科學的背景下,商業與產業利益向學術與非學術研究的逐漸滲透,也使得研發與產業間的界限不斷模糊,這也導致了“研發產業”這種混合共同體的誕生,也即Callon等所說的“技術——經濟”網絡[3]。
研發產業作為獨立的產業形態被納入產業分類體系可追溯至歐共體(歐盟前身)于1970年頒布的NACE(歐共體內部按經濟活動劃分的產業分類,最新版本為2007年版:NACE Rev.2),代碼為94;我國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與代碼(GBT4754-2002)》也將研究與試驗發展納入產業分列目錄中,代碼為75;由此可見,相對于其他傳統產業,研發產業尚屬于新興產業形態,且屬于新興服務業之列[8]。
在目前的研究中,國外學者對研發產業的定義暫未發現,只有為數不多的國內學者對研發產業進行了定義。高汝熹定義研發產業是指從事R&D活動的企業和組織的集合[9]。柳卸林等認為研發產業是指直接從事研究與開發活動,并以研發活動的產出為主要收入的行業,產業主體包括獨立的研發型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企業中直接從事研發活動的機構,研發產業的投入主要是研究開發經費,產出主要是論文、各類專利、新產品和專業技術等[10]。李京文等人認為研發產業是從事R&D活動、并提供產品或服務的企業和機構的集合[11]。黃魯成等人認為研發產業是指從事R&D經營活動,提供智力成果、技術服務和現代商務服務的組織的集合,組織可以是獨立的研發型企業,也可以是高等學校、科研院所、企業中從事研發活動的機構[12]。
以上的定義都強調了研發產業的主體和服務行業的性質。本文主要采用柳卸林等的定義劃分研發產業主體,認為包括大學(高校)、科研院所、企業內研發機構和獨立的研發型企業或機構。
二、研發產業視角中的新巴斯德象限
美國學者D.E.司托克斯(D.E.Stokes)在考慮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的關系時,提出了科學研究的二維象限圖,如圖1所示,一般被簡稱為巴斯德象限[13]。他主要是針對美國前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主任萬尼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1945年出版的《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中的科學研究的線性模型提出的。布什提出了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的線性模型[14]。布什強調,基礎研究是技術進步的主要源泉,基礎研究應當從過早考慮實用價值的短視目標中解放出來,然后通過應用研究與開發的中間環節,轉變為滿足社會經濟與軍事等發展的技術發明。這種從基礎研究向應用研究延伸的過程便是以前廣為接受的“線性模型”。但是科學史上的眾多實例表明,布什的線性模型觀點存在著缺陷,必須進一步剖析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關系。
司托克斯從研發的起因角度,提出了研發的二維象限模型。他將純基礎研究的稱為玻爾象限(Ⅰ象限),指的是只受追求基本知識需求的引導,不考慮實際應用,因為玻爾對于原子結構模型的探求,是一種代表自然科學家們的純研究思想;將世界上第一所大學波倫亞(Bologna)大學于公元1158年在意大利波倫亞市誕生,其后巴黎大學(1160年)、牛津大學(1167年)等先后成立。這些大學的出現,使得科學成為一種獨特的活動,為科學制度化奠定了基礎。此后,以1560年在那不勒應用引起的基礎研究稱為巴斯德象限(Ⅱ象限),因為從事生物學前沿研究的巴斯德,很多時候是來源于應用研究、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而作為對于二維象限圖中的右下角的Ⅲ象限,司托克斯將其稱為愛迪生象限,指的是純應用目的引起的研究,例如愛迪生當年進行的就是具有商業性利潤的電照明研究,而不是去追究他們所發現東西的更深層的科學意義。對于左下角的Ⅳ象限包含既不是認識目的激發的研究,也不是應用目的激發的研究,但它并不是空的。這一象限包含那種系統探索特殊現象的研究,既不考慮一般的解釋目的,也不考慮其結果會有什么實際應用。其可能包含類似皮特森那樣的進行鳥類、昆蟲和發病率的高度系統化的研究,由于太有限的實例所以沒有命名這個象限。

圖1 司托克斯的科學研究二維象限圖

圖2 研發產業視角下的新司托克斯二維象限圖
司托克斯的科學研究的二維象限圖主要仍是描述學院科學時的科學研究起因的。在后學院科學尤其是知識經濟的大背景下,關于科學技術的研發活動有了新的發展。研發活動的契約性和商品化進一步加強,導致了研發產業的形成,具體見圖2。斯建立的第一個自然科學學術組織——自然秘密研究會和1603年在羅馬建立的林切學院為代表,專門的科學學院開始興起。科學學院的出現使得學術活動和實踐活動統一起來。1810年,世界上第一個研究型大學柏林大學成立;柏林大學樹立了創造知識和傳授知識相統一的現代大學理念。研發活動開始正式進入大學,成為大學的一項新的職能[6]。同時,科學對經濟、社會的推動作用,也使得各國政府加大對大學和科研院所的資助,并在政府部門建立相應的科研機構。例如法國的科學院下屬的科研機構,美國衛生部的國立衛生研究院以及大批國立實驗室,中國的科學院和工程院下屬的科研機構。從研發活動的投入上看,美國的這些科研院所是美國研發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有國家實驗室720多家,1500多個獨立的研發設施,對國家實驗室每一年的投入經費占到了當年聯邦政府研究總經費的1/3,它是美國除產業界研發機構之外的第二大研發機構體系[15]。這些大學和科研院所也成為研發產業的一大主體。新玻爾象限指的即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學院科學時代的玻爾象限中的科學家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任職,但漸漸的接受國家資助,從個人的興趣愛好到完成資助人的研發任務,以課題或者項目的方式獲得資金資助,科研人員和資助者之間存在著較強的契約關系。這種契約關系并不完全等同于萬尼爾·布什認為的政治和科學之間的“社會契約”[14],而是這種“社會契約”關系在后學院科學時代的新發展。在這種新的契約關系中,研發人員被要求從事國家或企業等指定的具有特定利益的研發問題,而不是像學院時代中的自由選題的學術研究。當然,這種研發活動并不以必然的以交易和商品化為基礎。
世界上第一個設立于企業內部的實驗室,即由拉瓦錫在擔任硝石火藥廠總監時于1755年在炮兵工廠設立的;其后設立的比較著名的企業內實驗室有1882年西門子(V.Siemens)的內部實驗室,1900年美國通用電器公司(GE)設立的工業實驗室[6]。研發活動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其規模和影響,投入和產出效益都越來越大。研發活動也從以前只是科學家和工程師關注的事情,變成為政府、企業和整個社會關注的事情。自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德國和美國掀起一股企業開辦研發機構的浪潮,研發開始作為企業的一種職能被內部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大企業內部的研發活動和科技成果產業化一直是世界技術創新的主導力量,且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推動力量[16]。例如,美國20世紀60年代中期R&D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將近3%[17],企業廣泛設立科學中心,工業實驗室得到了大發展。20世紀60年代,西方世界的重大科技發明有67%首先在美國研究成功,有75%在美國首先使用[18]。在這一時期,以計算機與微電子為代表的科技革命首先誕生于企業,尤其以硅谷企業為代表。從19世紀后期開始到20世紀前半葉,德國和美國的一些大企業的研發活動主要是一種企業的內部研發。并且這些工業化國家企業中專門從事研發的實驗室已經從最初的化學和電力工業逐漸發展到整個制造業,成為制造業中大多數大企業特有的一部分[19]。企業內的研發機構構成了新愛迪生象限。新愛迪生象限內的研發產業主體主要是從事企業自身的研發任務,在企業內部的邊界內,主要是行政命令式的,沒有契約式關系。同時由于知識產權等的保護與核心技術的競爭防范需要,企業內部研發機構產出的成果一般供本企業使用,但如果出讓給外部企業或機構,收取專利費用或技術轉讓費用等,獲得經濟收益,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商品化活動。
隨著科技研發的不斷投入與研發活動的加強,研發活動在不同產業中都占有重要位置。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歐美大企業內部化的大規模研發活動是世界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以信息通信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對歐美國家企業的內部化研發模式產生了沖擊。在一些新興產業,科學研究到產業化的路徑被壓縮;在一些領域,比如生物技術領域,基礎研究成果甚至可以直接轉化為商業產品。同時,技術革命和全球競爭的加劇導致商業環境變得日益動蕩、產品生命周期縮短;研發活動日益呈現出專業性和復雜性,并由此帶來了研發活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另外由于競爭的不斷加劇,還造成了研發活動必須具有高效性。這也迫使企業必須開始通過提高研發速度和效率來獲得競爭優勢。在這種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企業研發外部化(R&D outsourcing)的趨勢逐漸顯現出來。研發外部化是指企業將部分知識創新、新技術應用的活動,逐漸通過市場由其他企業完成。企業與其他外部研發力量合作或委托研發,通過并購、購買等手段從外部直接獲得研發成果的比重越來越高。比如英國企業在1995年的研發支出中有10%是外包給其他機構完成[20]。1998年,美國新藥研發經費的20%是用于外部研發[10]。隨著研發活動外部化,也出現了大量以研發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企業,也即研發外包型企業,這是一種獨立的研發型企業。例如美國硅谷等的一大批純設計的集成電路公司(design house)以及一些醫藥研發公司。這種從研發活動的內部化到外部化的過程中,包含著商品化的交易過程;研發的商品化程度不斷加強。這些新型的獨立研發型企業構成了新巴斯德象限。它們是以研發新知識、新產品并商品化作為收入主要來源的,由于研發活動的需求是從外界輸入,因此存在著與研發需求者之間的強契約關系。
至于新的Ⅳ象限,也不是空的,在知識經濟背景下,對于研發活動仍然存在一些出于科研興趣、不以契約為主導、不以商品化為目的的研發個體和研發組織,例如一些高校或科研院所中學院科學意識濃厚的科學家或者非營利組織。
在學院科學到后學院科學的背景下,研發活動的主體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從大學、研究院所到企業內部研發機構和獨立的研發型企業或機構。從研發活動的產業化視角來看,在這個演變的進程中,打破了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之間的區別,研發的契約性和商業化程度得到了不斷的提高,也進一步促進研發活動成為一種產業。從研發活動的契約性和商品化角度來看,將這些主體放置于新司托克斯的科學研究的二維象限中,如圖2所示。研發活動的主體演進與產業化進程,既包含著人們對研發活動的主體選擇性及其歷史復雜性,也展現出對于追求更高效的研發效益而不斷驅動著研發主體和模式演進的內在機制。
三、演進的新巴斯德象限與研發產業國際比較
新巴斯德象限圖不是靜態的,而是運動和演進的。愛迪生象限原先只是進行自己企業內部的應用研究,并不將研究產品作為一種商品進行買賣。同樣的玻爾象限中的科學家進行的基礎研究也并不是以交易為主要目的。但是在知識經濟下,研發活動大多具有契約性,并且已經作為一種商品進行交易,直接導致并繁榮了研發產業。而在當代,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邊界早已模糊,尤其是在生物醫藥、有機化學等領域。所以可以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都看作是一種契約式的科研活動,并且在產業化的進程中有了新的進展,即開始商品化。這些契約和商品化的趨勢都導致了新玻爾象限和新愛迪生象限向新巴斯德象限的演進。
從國家層面來看,在整個研發產業的主體中,歐美發達國家的研發活動的投資和活動主要部分集中在新愛迪生象限(Ⅲ象限),并在向新巴斯德象限(Ⅱ象限)運動。事實上,美國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研發經費來自企業,這相當于其他國家的研發支出的總和。而且,有研究指出,大約有四分之三的研究開發工作是在企業完成的;根據華盛頓工業研究所的調查數字顯示,目前僅僅在美國,就有15000家企業研究實驗室。估計這些實驗室雇有75萬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占美國全國專業技術人員總人數的70%。這些企業研究實驗室是美國研發能力和研發產業的基礎和強大動力[21]。另一方面,關于研發的外包趨勢也在不斷加強。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羅伯茨教授在1999年進行的對北美、日本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年研發收入超過1億美元的244家公司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越來越多的企業傾向于向外部尋找技術的來源[22]。根據歐洲委員會報告(2005),從1997到2002年,OECD各成員國研發以12%的速度增長。波蘭、丹麥、美國和瑞士等國家,研發服務外包的增長率達到30%。在美國,接近40%的業務研發在服務性產業完成;在歐洲,大概為15%左右[16]。2005年8月,沃里克商學院對歐美及亞太1200家組織調查得出的重要結論之一是,IT外包與主流商業外包活動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23]。有學者在研究荷蘭605家中小企業的開放式創新實施過程中,發現288家制造業型企業中有59%企業采取研發外包,317家服務型企業中有43%采取研發外包,并且年增長率達到 22%[24]。有些外國學者(Subramony S,2004)認為,中國將成為下一個外包潮流的發源地,而由Diamond Cluster國際所作的IT外包調研表明,中國將成為繼美國、印度之后的第三大研發外包服務國[10]。杜德斌等提出一種假設,認為在未來,整體上研發仍是會繼續增長,但是內部性的研發活動所占比重會越來越小,而外部性的研發活動會占主導[25](見圖3)。這在歐洲研發管理協會(EIRMA)2004年對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代表的全球研發活動外部化的歷史與趨勢的研究成果中也得到驗證(見圖4)[26]:在企業建立自己的研發機構之前,一些研發成果都是從外部或者通過合作獲得,比如大學和科研院所;到了20世紀中期,企業內部研發機構的主導性作用體現出來,研發的外部化不斷減少,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降到最低,只占整個研發支出的3%左右;在20世紀后期又開始了不斷的上升趨勢。

圖3 研發活動趨勢[25]

圖4 全球研發外部化的歷史與趨勢
研發外部化的增長促生了更多的獨立的研發型企業和從事合同服務的契約式企業。這些都表明,在歐美國家,新巴斯德象限是一個研發產業的增長點,歐美發達國家的研發活動正在從新愛迪生象限向新巴斯德象限運動(如圖5所示)。
我國企業研發能力經過多年的建設,已經取得一定的成績。進入21世紀,我國企業R&D經費支出占全國R&D經費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9年,這一比重已達到71.7%。2009年,我國的R&D經費支出總額中,各類企業支出為4162.7億元,比2008年增加了25.7%。2010年,我國共投入R&D經費7062.6億元,比上年增加1260.5億元,增長21.7%;其中,各類企業投入R&D經費5185.5億元,比上年增長22.1%;企業經費所占比重達到了73.4%[27]。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在近幾年,我國企業的研發費用投入較大,增速較快,所占比重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另外,從科技人員分布來看,2008年我國R&D人員在三大執行部門的分布情況是:企業約占73.2%,研究機構占13.2%,高等學校占13.5%。研究機構自1999年進行改制改革以來,其R&D人員數量占全國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高等學校的R&D人員雖然數量增長,但占全國的比重同樣在逐年下降,唯有企業R&D人員數量及其占全國的比重在不斷增長[28]。

圖5 運動與演進的新司托克斯二維象限圖
但是,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思維意識的影響下,由于研發機構與生產單位的分立,導致企業尤其是大中型國有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一個單純的或僅僅進行少量研發活動的生產單位的局面,這與發達國家的企業從一開始就是僅僅跟隨市場變化的、具有長期的“內生”于市場的研發行為的狀況不同。這種研發機構與生產單位的割裂影響仍然長期存在,導致我國大部分企業自身的研發能力仍然很弱,整體上的創新能力仍然有待繼續發展和加強。因此,在實質上,我國研發產業仍然是以新玻爾象限(Ⅰ象限)為主要特征,正在向新愛迪生象限(Ⅱ象限)運動(如圖5所示)。
這其中,企業內部研發機構的缺乏是一個重要原因。從整體而言,我國企業仍處于世界產業鏈的中低端,很多高新技術企業還是沒有研發機構的組裝加工車間。2006年,在我國3萬多家大中型工業企業中,有R&D活動的企業只占24%,而設有研發機構的企業只占23%[29]。另外有關數據顯示,我國中小企業有研發活動的企業比例只占28%左右,開展研發活動的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平均不到1%,而國際上一般認為,企業的研發費用占其銷售收入的2%,企業才能基本生存;當達到5%以上時,才具有競爭力[30-31]。從中外數據比較來看,發達國家企業研發經費占銷售額的比重一般為5%左右,高科技企業則達到7%-8%,有的甚至超過了10%。例如 ,美國孟山都公司研發經費占銷售額的比重達22%,微軟公司為17%,愛立信公司為15%,朗訊公司為12%;而目前即使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上海地區,其工業企業該指標值也僅為2.5%[32]。這與發達國家的比例還有很大差距。不僅美國企業內研發機構占有主體地位,并且日本、韓國等也具有類似特征。例如,根據日本科學技術廳的調查,20世紀70年代以后實施研究開發的企業中,約有70%的企業擁有獨立研究所,而且還有按不同職能成立的專業研究所,企業在應用開發領域逐步占據主導地位[33]。在韓國,企業研究機構從1983年的100家左右,發展到2004年超過了10000家,2008年更是超過16000家;其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小企業的研究所數量增加迅速,所占比重也不斷提高,從1981年的0起步,1988年占到了所有企業研究所的53.3%,1998年占到78.7%,2008年占到93.9%。中小企業中研究機構的興建,在總體上幫助韓國在20世紀80年代后逐步確立并加強了企業研發和創新主體的地位[34]。由此來看,我國與發達國家在企業內研發機構的建設上這種差距是非常明顯的。
因此,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企業內研發機構的主體地位正在形成,但仍有待繼續加強和完善。從總體上來說,我國仍處于一個研發產業從新玻爾象限向新愛迪生象限演進的過程(見圖5)。在注意到美國等發達國家從新愛迪生象限向新巴斯德象限演進的進程后,我國在鞏固自己研發活動的主要部分從新玻爾象限向新愛迪生象限轉變的同時,也需要追趕國際形勢,向新巴斯德象限積極演進。
四、結語
西方發達國家代表——七國集團(G7)早已進入“服務經濟”時代。G7中第三產業比重已占到國民經濟的70%以上,并且也是增長最快的。例如,2005年G7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為1.71%,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為26.02%,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為72.28%[35]。這些表明了服務業的大發展在發達國家是一種主流。為將我國建設為工業強國,實現經濟轉型升級,中央領導多次強調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而研發產業就是一個高端的生產性服務業;大力發展研發產業,正當此時。研發產業由于其高端的科技含量與研發服務能力,以及緊密聯系市場需求的特性,使得它即使在面對經濟或金融危機時,也能穩步增長。這對我國目前所面對的國際經濟形勢和自身的經濟轉型戰略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在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中,美國以研發服務為主體的科技服務業(R&D service industry)受金融危機影響不大,基本保持平穩增長,2008年全年實現總收入為8827.51億美元,比2007 年增長了15.2%[36]。
進入21世紀以來,發達國家為爭奪和利用全球科技資源,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大了向中國、印度等新興發展中國家研發轉移的力度。根據聯合國貿發組織的調查,62%的跨國公司將中國作為2005-2009年設立海外研發機構的首選地。截至2007年底,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已達到1160家[37]。近期,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出版的《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中國2011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再創歷史新高,進入服務業的外國直接投資首次超過了制造業[38]。這些外部環境為我國企業自身的研發能力帶來挑戰,也為我國的研發產業向新巴斯德象限演進提供了一個契機。
[1][美]約翰·齊曼著.真科學[M].曾國屏等譯.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
[2][美]R.K.默頓著.科學社會學[M].魯旭東,林聚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3]胡鞍鋼主編.知識與發展:21世紀新追趕戰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4][美]邁克爾·吉本斯等 著.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M].陳洪捷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陳勁主編.研究與開發管理[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6]趙紅光.R&D產業形成與發展研究[D].北京交通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7][美]弗里茨·馬克盧普 著.美國的知識生產與分配[M].孫耀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8]田先鈺.R&D產業及其組織與管理研究[D].江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論文,2008.
[9]高汝熹,張國安,謝曙光.上海 R&D產業發展前景[J].上海經濟研究,2001,(9):22 -28.
[10]馬 林.研發產業初論[M].北京: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
[11]李京文,黃魯成.關于發展北京 R&D產業的思考[J].中國軟科學,2004,(8):122 -127.
[12]黃魯成,陳 曦.研發產業主體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8,25(9):26 -33.
[13][美]D.E.司托克斯著.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巴斯德象限[M].周春彥等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14][美]萬尼爾·布什等著.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5]呂波曹慶萍.美國與德國科技研發體系比較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05,(1):135 -139.
[16]伍 蓓,陳 勁.研發外包模式、機理及動態演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17]樊春良.全球化時代的科技政策[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5.
[18][美]理查德oR.尼爾森著.國家(地區)創新體系:比較分析[M].曾國屏等譯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
[19][美]克利斯·弗里曼等著.工業創新經濟學[M].華宏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0]Jeremy Howells,Dimitri Gagliardi,Khaleel Malik.The Growth and Management of R&D Outsourcing:Evidence from UK Pharmaceuticals[J].R&D Management,2008,38(2):205-219.
[21][美]邁克爾·克羅等著.美國國家創新體系中的研究與開發實驗室——設計帶來的局限[M].高云鵬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
[22]劉建兵,柳卸林.企業研究與開發的外部化及對中國的啟示[J].科學學研究,2005,(3),366-371.
[23]杜德斌,孫一飛,盛 壘.跨國公司在華R&D機構的空間集聚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0,19(3):16-21.
[24]Vareska van de Vrande,etc.Open Innovation in SMEs:Trends,Motives and Management Chanllenges[J].Technovation,2009(29):423-437.
[25]杜德斌,周天瑜,王 勇,盛 壘.世界R&D產業的發展現狀及趨勢[J].世界地理研究,2007,16(1):1-7.
[26]Directorate General Joint Research Center.Monitoring Industrial Research:The Annual Digest of Industrial R&D 2006[R].European Communities,2006.
[27]科技部.2010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EB/OL].http://www.most.gov.cn/kjbgz/201109/t20110927_89857.htm.2011-09-27/2012-03-07.
[28]科技部發展計劃司.科技統計報告2009年第28期[EB/OL]. http://www.most.gov.cn/kjtj/tjbg/201003/P020100316386691314647.pdf.2009-12-30/2012-03-17.
[29]李新男.促進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建設創新型國家.中國科技產業[J].2009,(2):26-30.
[30]曾永飛.我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研發投入不足的原因分析及對策[J].科技創業,2009,(2):18-19.
[31]徐冠華.中國企業目前難當創新主體[J].企業家天地,2007,(3):16 -17.
[32]杜德斌等.上海研發產業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J].遼寧科技統計,2008,(2):13 -18.
[33]韓中和.變革企業的研發組織——日本企業研發組織變革的啟示[J].研究與發展管理,2002,(12):22-28.
[34]李東華.韓國科技發展模式與經驗——從引進到創新的跨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35]馬風華.第二產業生產服務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
[36]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等編著.2009世界服務業重點行業發展動態[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37]趙 剛.怎樣對待國際研發產業對華轉移[N].科技日報,2009-10-25(2).
[38]中國網.2012年世界投資報告發布 中國吸引外資再創新高[EB/OL].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gnjj/20120706/853878.shtml.2012-07-06/2012-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