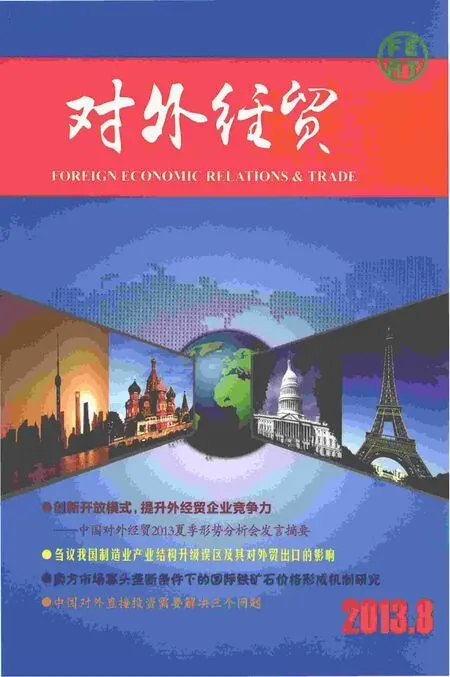產品內貿易與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分析
萬亞晨
(天津商業大學經濟學院,天津300134)
產品內分工是國際化大分工背景下的產物,是指同一產品在不同生產階段之間的國際分工,可以通過不同國家間的非關聯企業完成,也可以在跨國公司內部實現。而隨著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的發展,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分工也變成一種不可忽視的國際產業分工方式,產品內貿易是其主要貿易形式。產品內貿易分工的生產形式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前提條件:一是產品的生產需要經過至少兩個以上的連續階段;二是產品生產跨越國界,至少有兩個國家參與其生產過程,提供價值增值,每個國家專業化于一個以上的生產階段,但不是完成所有的生產階段;三是至少跨越國界一次,即至少一個國家在工序生產中運用了國外進口投入品,或出口的產品作為另一國家生產中的投入品[1]。
在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產品內國際分工與貿易中,各國的分工地位是不平等的。跨國公司憑借自身強大的技術、資金、渠道等優勢,根據發展中國家的地區優勢與要素稟賦特點,將自己處于成熟階段與標準化階段的產品分布于各發展中國家,而自身長期占據附加值較高的高端價值鏈戰略性增值環節。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簡單的加工制造等低附加值環節,只能依靠產品價值鏈轉移過程中的技術外溢與知識擴散效應帶動經濟增長,從長遠來看處于被動“被鎖定”狀態,將逐漸在新型國際分工中被發達國家邊緣化,失去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域之間比較優勢是相對變化的,資本的逐利性將導致跨國公司撤資,隨之而來發展中國家面臨跨國公司撤資后造成的產業結構“空心化”帶來的威脅[2]。因此,在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國際分工中,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分工和貿易的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才是長遠之計。
改革開放以來,產品內貿易促使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我國產業發展也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為進一步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本文主要研究產業結構變動與產品內貿易之間的關系,分析我國產業結構的演變趨勢,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我國產品內貿易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把握國際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轉化的機遇下,結合自身勞動力稟賦優勢,積極融入產品內分工的全球化生產中,發展成為了世界上重要的加工組裝基地,因此,在我國貿易實踐中產品內貿易通常又被稱為加工貿易。總的來說,我國產品內貿易發展具有以下特點:
(一)貿易規模持續擴大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的加工貿易發展突飛猛進,加工貿易總額從1981年的26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13052.2億美元,增長超過了500倍,占全國貿易比重從1981年的6%躍升到2011年的34% 。同時我國開始注重培養加工貿易前后相關產業的零部件配套能力,延長價值鏈,形成產業集群。
(二)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產品內貿易的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眾多跨國公司為了充分利用我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紛紛在華投資建廠,這是我國產品內貿易發展的重要原因。如表1所示,我國FDI由1996年的417.26億美元提高到2011年的1160.11億美元,產品內貿易額也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由1996年的1278.6億美元提高到2011年的13052.2億美元。

表1 1996—2011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與產品內貿易額單位:億美元
二、產品內貿易與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及其估計
本文首先計算產品內貿易指數和產業結構變動指數,并在對數據進行相關預處理的前提下以此作為實證分析產品內貿易與產業結構升級影響關系的指標,通過擬合歷年產品內貿易指數與產業結構變動指數得出擬合方程,進而來驗證產品內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產品內貿易指數X=NIX/IX
其中,IX為我國進出口額之和;NIX為我國產品內貿易進出口額之和,產品內貿易指數的取值范圍是[0,1]。該產業產品內貿易所占比重越大,該指數越接近于1;產品內貿易所占比重越小,該指數越接近于0。鑒于統計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以加工貿易額代替產品內貿易額。
響應快捷化:①對當班發生的變化情況必須詳細記錄發生時間、地點、影響范圍,按變化性質與要求及時匯報,立即啟動響應程序;②對上一班延續的變化項目,要詳細跟蹤落實變化進展情況,確保閉合管理;③發生瓦斯等有害氣體報警或超限時,必須在3分鐘之內匯報上級部門并及時落實事故原因;④對所有變化環節響應,全部規范時間標準,要求所有響應步驟全部在規定時間內完成。
產業結構變動指數Y=CTV/ITV
其中,CTV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產值;ITV為工業總產值。本文選取了12個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包括:煙草制品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石油加工、醫藥制造業、造紙及紙制品業、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纖維制造業、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信設備、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工業總產值之和來代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產值[3]。該指數上升說明我國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升級,該指數下降則說明我國產業結構沒有得到優化升級。如表2所示,我國產品內貿易指數1996—2011年呈現先增加而后下降的趨勢,表明產品內貿易比重呈現下降趨勢,產業結構變動指數也是呈現下降趨勢。
根據計量經濟學模型,產品內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實證分析模型為:

其中:α,β,γ表常數項,t代表時間趨勢,U代表擾動項,Y代表產業結構變動指數,X代表產品內貿易指數。

圖1 1996—2011年我國產品內貿易指數與產業結構變動指數變化趨勢
根據計量經濟學知識,利用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得出結果如下:

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
設 H0:γ =0,H1:γ≠0
t=3.95,查 t表得 tc=2.12
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
設 H0:β=γ=0,H1:β≠γ≠0
F=32.3,查F表得Fc=3.81
因為32.3>3.81,即總體回歸方程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429560 0.132512 3.241666 0.0064 LNX 0.591292 0.149379 3.958325 0.0016 LNT -0.273548 0.043126 -6 343031 0 0000 R -squared 0.832668 Mean dependent var -0 535033 Adiusted R -squared 0.806924 S.D.dependent var 0 296710 S.E.of regression 0.130376 Akaike info criterion -1.069433 Sum squared resid 0.220972 Schwarz criterion -0.924573 Log likelihood 11 55547 F -statistic 32.34486 Durbin-Watson stat 0.923235 Prob(F-statistic)0.000009
(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由上文擬合方程知產品內貿易指數與產業結構變動指數呈正相關關系。根據計量經濟學知識可知,相關不一定存在因果關系。本文借助Granger因果分析對我國產品內貿易與產業結構之間的因果關系作進一步檢驗,檢驗結果如下:


Null Hypothesis:Obs F-Statistic Probability LN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Y 14 4.44820 0.04536 LNY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X 3.29681 0.08430
查F統計量表可知,F統計量為3.89。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檢驗結果拒絕了LNX不是LNY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設,但接受了LNY不是LNX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設,表明產品內貿易指數是產業結構升級指數的Granger原因,即產品內貿易指數與產業結構變動存在因果關系,它們之間存在較大的正相關關系;而產業結構升級指數不是產品內貿易指數的Granger原因,它們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
(三)經濟學意義分析
根據結果可知,方程的擬合優度為0.83,F檢驗值為32.3,其相應數值都通過了系數顯著性、方程顯著性檢驗等,說明方程的估計及參數估計是合理有效的,產業結構變動指數和產品內貿易指數作為解釋變量是顯著的,同時產品內貿易指數與產業結構變動指數存在長期的因果關系,產品內貿易指數對于產業結構升級指數的長期彈性為0.59。其經濟意義是,1996—2011年期間,產品內貿易出口額占我國總出口額的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我國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工業產值占我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就會上升0.59個百分點。
三、結論與對策建議
在產品內分工和貿易的前提下,如何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要實現產業的有效升級,首先必須結合我國的資源稟賦等特點,以及我國參與產品內貿易的現實情況,全方面多角度地采取有效促進措施。
(一)加強“干中學”,順應全球產業轉移趨勢
日本學者赤松要的雁行模式理論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在產品內貿易下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途徑。他提出發展中國家特定產業的生命周期一般由四個階段構成:進口—進口替代—出口—“反進口”[4]。第一階段,發展中國家某些產業剛剛起步,必須依靠進口過程中的技術外溢促進產業發展;第二階段,隨著產業的壯大,通過“干中學”提高管理技術水平,形成競爭優勢;第三階段,伴隨著技術的成熟,逐步將產業轉移到國外發展;第四階段,本國的需求靠“反進口”滿足。我國一方面必須順應全球化產業轉移趨勢,抓住機遇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我國幅員遼闊,東西中部的發展水平明顯不平衡,因此我國可以借鑒雁行理論模式,在我國內部實現產業梯度轉移,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二)優化產業技術結構,發揮技術的帶動作用
由于要素稟賦差異及發展歷史等原因,全球產業價值鏈逐漸形成,不同國家的企業分別嵌入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不同環節。一般而言,發達國家依靠自身的比較優勢及先發優勢,牢牢控制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環節,居于壟斷地位,而在市場充分競爭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價值環節有很強的替代性,在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獲得的利益較少。因此,應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提高我國在國際產品內分工中的地位,堅持自主創新、集成創新與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相結合的路徑是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必由之路,是逐步擺脫被發達國家“邊緣化”的不二選擇。
(三)培育產業集群,發揮產業集群的輻射和帶動作用
當前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產業集群絕大多數處于國際產品內分工的低端,創新、抗風險能力差,路徑依賴現象嚴重。因此客觀上要求我國今后在產業集群建設的同時,必須注重產業集群內部中產業鏈條的完整化,形成上下游產業鏈間的相互拉動效應,提升產業集群的能力。同時通過產業集群的集體行動及跨國公司各廠商之間密切的關系,加快管理與技術創新,增強集群的動態競爭優勢,實現產業集群在國際產品內分工中的升級[5]。
(四)加大政策扶持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從產品內分工的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要追趕發達國家,政府必須積極引導并給予大力扶持。一方面政策上仍要鼓勵引進外資,促使跨國公司在我國投資,進而通過知識、技術等溢出效應,推動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國企業知識產權意識不強,導致自主品牌在國內遭侵權、在國外遭惡意搶注的情況屢見不鮮。因此必須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同時扶持產業內主導企業積極參與國際技術標準的制定。
[1]田文.產品內貿易的定義、計量及比較分析[J].財貿經濟,2005(5).
[2]黃志啟.產品內貿易、產品內分工與產業結構升級[J].生產力研究,2011,(12).
[3]賈文文,周升起.產品內貿易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J].價值工程,2011(4).
[4]高澤金,夏明國.產品內貿易與中國產業結構升級[J].科技創業,2011(5).
[5]安哥軍,趙景峰.產品內貿易、分工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研究[J].中國流通經濟,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