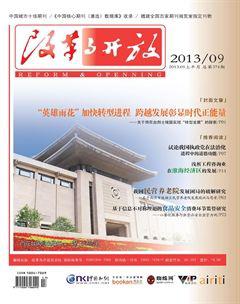政社分開:政府對社會組織管理動態
韓沛錕
摘要:在政府長期以來的雙重管理體制之下,社會組織呈現官民二重性特征。十八大以來,政社分開成了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也成了今后政府對社會組織管理的價值指導。政社分開,不是政社割裂和政社對立,而是政社合作。政社分開的最終目的是社會組織獲得充分的管理自主權,在政府引導監督和制度規范內,與政府進行積極溝通聯動。政府與社會組織的有效合作,將是十八大以后政府對社會組織管理的趨勢所在。
關鍵詞:雙重管理;社會組織;政社分開
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巨大變革的今天,伴隨著利益多元和民主進程的加快,人民對于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和政治參與的訴求不斷增強。然而,由于政府制度供給的不足和管理方法的落后,人民利益訴求和信訪渠道的不暢致使矛盾頻發,各種社會問題凸顯。因而,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已成為前沿命題和嶄新課題擺在面前。近年來,社會組織快速發展,政府對社會組織管理創新也不斷變化。十八大以來,無論從政策上,還是領導人的講話中,都能看到政府對社會組織管理的重大變化,包括對社會組織的態度、具體管理辦法等方面。
一、社會組織的界定與現狀剖析
1.概念界定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中要求,“加強和改進對各類社會組織的管理和監督”。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中更加明確提出:“健全社會組織,增強服務社會功能。堅持培育發展和管理監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會組織的政策,發揮各類社會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這里所說的社會組織,是此前政府使用的與之對應的“民間組織”,包括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廣義的社會組織為政府之外的、以非營利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的組織,而本文采用的社會組織的概念,是指從廣義社會組織中剔除掉“政府性較強的”“人民團體”“免登記社團”和“事業單位”而得到的狹義社會組織。文章所討論的政社關系亦指政府與狹義社會組織間關系。
2.現狀剖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組織數量明顯增長。截止2013年一季度,全國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50.1076萬個,其中社會團體27.2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22.6萬個、基金會3076個,與1988年我國社會組織數量4446個相比,大約增長了113倍。此外,還存在大量未登記但以社會組織名義活動的組織和在華活動的境外社會組織。
盡管我國社會組織數量上已經有了較大積累且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總體上看,能有效發揮作用的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社會組織十分有限。康曉光認為,當前我國非政府組織整體發育水平明顯進步,但仍較為初級,并呈現不均衡性、弱自主性、弱挑戰性等特征。
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組織發展呈現波動性特征,其與政府的互動過程深受政府政策影響和制約。政府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并限制社會組織發展,強國家-弱社會的社會格局難以改變。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基本采用雙重管理的框架。在政府的管制模式下,社會組織缺乏獨立性。而這樣的管理體制也形成了社會組織法律框架的特征:(1)政府主導;(2)雙重管理;(3)行政分割;(4)限制競爭;(5)強制年檢。
基于這種雙重管理體制,社會組織呈現官民二重性特征。社會組織所掌控的資源有限,動員能力不足。根據薩拉蒙的調查,所有社會組織收入中的34%來自于公共部門,由政府資助。因此,社會組織帶有較強的依附性特征,因需求而主動掛靠政府機關,主動放棄獨立性和自主性。在政府機構改革中從政府系統中剝離出來或由政府自上而下籌建的組織,往往作為政府附屬機構發生作用,官民二重性色彩更為濃烈。
社會組織在中國的發展困境也深深地受到政治文化的影響。我國自古以來雖有互助、結社、民間公益的傳統,但長期以來的中央集權政治傳統形成了“極強國家、極弱社會”的權力格局,極大地束縛了我國民間社會組織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政府基本因襲著“全能政府”的角色,不存在西方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組織。基于這樣的政治文化,民眾將官辦性質濃的社會組織視為第二政府(如婦聯),而對實力弱小的草根組織往往持懷疑態度,甚至不承認或忽略其在公共治理中的地位,因而社會組織難以得到深層次的認同。植根于政治文化的制度安排也不利于社會組織以政治社團的形式參與政府決策。
二、政社分開:十八大以來的政策風向分析
1.十八大報告關于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表述
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自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一直是社會管理格局的內涵。十八大報告在原來的基礎上增加了“法治保障”,而且將“社會管理格局”改為“社會管理體制”,表述更加準確,內涵更加豐富,突出了依法進行社會管理的理念。在此基礎上,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第一次提出了現代社會組織和現代社會組織體制這兩個概念,也是第一次提出了“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新要求,預示著社會組織發展要走法治化道路,必將推動社會組織領域的立法工作及社會組織內部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提升社會組織治理、發展和服務能力,更好地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與政府、市場一道形成多元參與、共同治理的格局。總之,十八大報告將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中來,不僅再次明確了政社分開的社會組織體制,更提出要用法律來予以制度化保障。
2.李克強防艾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2012年11月26日,李克強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講話提出,防治艾滋病必須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他認為,“用社會的力量辦好社會的事情,是推動社會體制改革、加強社會建設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艾滋病傳播途徑更隱蔽、更私密等新的情況下,社會組織參與艾滋病防治更具有獨特作用。”在肯定社會組織參與社會事務的路徑選擇上,總理提出,要探索完善有效機制,在資金、技術等方面給社會組織以扶持,研究建立防艾基金,多元出資給予支持。要創新財政投入方式,更多地向社會購買服務,完善對公益性組織的稅收減免政策,對參與公益活動多的大學生,在就業方面也要予以支持,這不僅有利于增強防艾力量,也可為整個社會領域的改革積累經驗。
李克強在防艾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主要突出了以下三點:第一,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公共事務和公益領域中的作用是一種必然選擇。第二,在公共事務應對和處理中,政府理應簡政放權,探討公共產品提供的多元路徑,社會力量可以辦好的事情,政府要加強資金支持和政策指導調動社會力量來加以應對參與。第三,要積極鼓勵公益性社會組織的發展,同時引導大學生投身公益領域開辟就業新渠道。他的這番講話肯定了社會組織自身乃至于和政府積極合作的重要意義。
3.《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相關制度安排
2013年3月1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該方案在有關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方面提出了許多頗有意義的制度安排。
首先,在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改革方面,方案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逐步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強化行業自律,使其真正成為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主體。探索一業多會,引入競爭機制。”
其次,在社會組織發展引導方面,方案提出“重點培育、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這些組織的成立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民政部門要依法加強登記審查和監督管理,切實履行責任。
第三,在社會組織的法律保障方面,方案提出“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健全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管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健全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推動社會組織完善內部治理結構。”
《方案》中有關社會組織管理方面的制度安排,雖然在社會組織的登記上,并沒有完全打破雙重管理體制,但已經呈現出了雙重管理的松動態勢,將有利于公益服務、行業協會類等社會組織的發展。《方案》重在優化政府職能,進一步調整國家與社會關系,為政社分開提供了政策、法律的制度化保障。
三、對政社分開的概念辨析
通過十八大以來的政策風向分析,政社分開成了當前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也成了今后政府對社會組織管理的價值指導。究竟什么是政社分開?這個關鍵的概念,有必要對其進行辨析。
其一,政社分開并不是政社割裂,而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政社溝通。國家與社會之間是難以劃出絕對明晰的界限。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完全相互獨立也不是我們所追求的。我們所追求的政社分開是指社會組織不成為政府的附庸,而有自己相對獨立的自主權,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購買者不是同一的,要打破內部市場問題。因此,政社分開,是為了調動社會組織的積極性,來營造政府同社會組織多元互動的生動局面。
其二,政社分開并不是政社對立,而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政社合作。政社分開是大勢所趨,政社關系的重新調整,給予社會組織較多自主權以充分發揮其活力,但必須明確的是,這種政社分離,并不是一種敵對。西方普遍認為“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而在中國,政府是國家治理的主體,傳統中國文化浸染下的政府扮演著家長的角色,并為人民大眾廣泛接受。即便從現代意義上來講,社會組織的生存發展離不開政府資金和政策的支持。因此,對于社會組織而言,政府并不是對立面和敵人,二者應該是一種公共服務的伙伴關系,政社分離是為了更好地合作。
其三,政社分開主要是指社會組織管理權與政府相分離,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監督引導仍是必要的。官辦社會組織,如中國扶貧基金會,但凡擁有著較為獨立的管理、決策權限,其所產生的效益反倒比民辦社會組織要好。因此,政社分開,不一定說官辦社會組織要與掛靠單位絕對脫鉤,而是說在管理權上,主管單位不予干涉,保證其擁有獨立的法人治理結構。對于民辦社會組織,或者說官方背景較淡的社會組織,政社分開制度框架內所擁有當然的法人治理結構的同時,也并不意味著不受政府的監督引導,也要受到法律規范、問責制度的調節。
因此,政社分開最終目的是社會組織獲得充分的管理自主權,在政府引導監督和制度規范內,與政府進行積極溝通聯動,參與到公共事務處理應對中去,同政府進行有效合作。這將是十八大以后政府對社會組織管理的趨勢所在。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