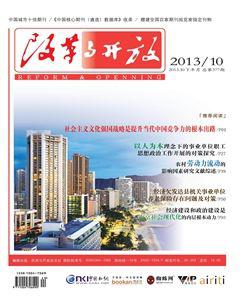“父子相為隱”中的“隱”與“直”
曹洋
摘 要:“親親相隱”是近年來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爭論導致了對儒家倫理的不同認識與評判。許多因此生發的對儒家哲學的詬病正是出于對“隱”與“直”二字的望文生義式的片面理解,因此回到原初語境,闡釋孔子之本義,“隱”為沉默、回避,“可與言而不言”,故最為切近中道、直道。如此,方能超越立場評判,明辨學術事實。
關鍵詞:父子相為隱;隱;直;儒家倫理
自本世紀初,學界關于“親親相隱”的是非問題之爭論,因其既關涉儒家倫理的歷史及其價值,而且關乎當今社會的倫理與法律等諸多現實問題,得到了學者們集中而深刻的關注。面對極其復雜而尖銳的爭論,應超越立場之評判,而明辨學術之事實。“親親相隱”即“親親相為隱”,由“父子相為隱”引申而來。“父子相為隱”出自《論語》之“子路篇”:“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第18章)孔子在明確表示了“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的態度之后,其所認同的“隱”與“直”所謂何意呢?
一、“親親相隱”之“隱”
對于本章中的“隱”字之含義,古往今來的學者爭論紛雜,而這些不同的理解正是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倫理觀形成不同評判的主要依據。本文將面對學界已有的對“隱”字的理解,結合對“隱”字之字源本義,及其在《論語》其他各章出現之含義的考察,回到本章的原初語境具體分析“親親相隱”之“隱”。
在《康熙字典》等字典、辭典中,“隱”字有匿、微、度、藏、私、去、蔽、諱、痛等諸多含義。學界關于“隱”字含義的理解,形成最早也是最為廣泛接受的觀點當屬認為“隱”字為“隱瞞”之含義。自朱熹《論語集注》及至現當代的李澤厚、楊伯峻等諸多學者譯注《論語》,皆以“隱瞞”釋“隱”,如錢穆在《論語新解》一書中將本句釋為:“隱,隱藏義。”,“父親替兒子隱瞞, 兒子替父親隱瞞。”[2](341) 此外,也有部分學者提出,“隱”字作為“潔身自好”,“審度考慮”,“代為受過”,通假為“櫽”作“矯正”之義等觀點,并做出了相關論述。
在《論語》中,“隱”字分別在五篇七章中出現,共九次。通過對《論語》中“隱”字出現的幾處原文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論語》中的“隱”字,無外乎兩種含義:一是,與“見”、“行義”等相對應的“隱”、“隱居”、“隱者”等,即隱居、不見、不行的含義,是行為生活意義上的;二是,與“言”、“證”相對應的“不言”、“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即不顯、不言的含義,是言語思想意義上的。“隱”字作隱居、不顯等第一層含義的語句有: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第13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論語·季氏》第11章)
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執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第7章)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第8章)
“隱”字作沉默、言語不顯之含義的語句有: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論語·述而》第23章)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第18章)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季氏》第6章)
結合《論語》中孔子使用“隱”字所表達的含義,可見,本文所討論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一句中,“隱”字與葉公所言的“子證之”的“證”之相對應,表知而不言的沉默之義,而非學界通常所認為的父親與兒子相互隱藏、窩藏。隱藏、窩藏是故意隱藏真相,明知故犯,不說實話,而孔子“隱”字在此處的含義原本是沉默、回避,不是主動去幫助親人隱瞞罪行,而是自己的“可與言而不言”。但正是因為對“隱”字有前述隱瞞、隱藏之誤讀,才導致了部分學者對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倫理觀的詬病,指責其是中國腐敗的根源,觸犯、違反法律的文化來源。但是,實際上,按照孔子本義的“可與言而不言”,是既符合情理父子孝親之情理,而又符合血緣關系而豁免告發的義務之法理的。
二、“直躬者”、“ 吾黨之直者”與“直在其中矣”
“直”字在《論語》中共出現二十二次,在不同章句中出現所表達的含義也各有差異:既有社會原則與道義層面上的公正、正直之義;也有真實而真切的情感層面上的率真、直率之義;還有“直道”之“直”作為一個德目,既發乎情又不失于理。在本文所討論的“葉公語孔子”一章中,“隱”字就出現了三次,分別是“直躬者”、“ 吾黨之直者”與“直在其中矣”,下面將分別討論這三個“直”字的含義。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者”就是直躬的人,即“以直為躬”,而“躬”為“躬行之義”。“直”的本義是正見。此處,葉公認為,父親把鄰人誤闖自己家的羊留了下來,作為兒子出來指證自己父親的“罪行”,就是“直躬者”。葉公所認為的直躬之人,就是行事符合社會的規范與準則,遵循并且維護道義原則與禮樂規范的公正、正直之人。但是,這樣的“直躬者”“義必公正, 心不偏黨也” (《韓非子·解老》),是缺少率真的真實情感之人,機械、固執地以“直”作為自己的行事準則,甚至會為了維護禮樂制度,而毫無自然親情,無視親情倫理,故為孔子所不滿。進而,孔子提出自己心中的“直者”,“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孔子借“吾黨之直者”來表明自己理想狀態的直者之所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理解孔子的態度的關鍵就在于“直在其中矣”。和通常將“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隱”錯誤地理解為隱瞞、窩藏之義,相對地將孔子的這句話望文生義地理解為,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以及父子之間的相互包庇與窩藏是正當的,從而以此為依據,指責以孔子奠基的儒家倫理首開包庇之先河,有違現代法治,甚至是中國腐敗的深層文化傳統根源。但實際上,孔子在這里的意思是,面對至親之人的順手牽羊的行為,選擇消極的不作為,沉默與回避是“親親之情”的自然流露與真切體現。更重要的是,這種“知而不言”對于一個處在倫理困境,即同時面對被攘羊者與攘羊之親的人來說,是最切中中道的做法,蓋因其既不傷乎于情,又合乎于法,這其間自然地內含著“直在其中矣”。
值得說明的是,“親親相隱”的界限問題。一方面,“隱”是沉默、回避,是“可與言而不言”,在程度上是消極的不作為,而不是主動、積極地幫助親人隱瞞罪行,也就是法律所認可的知情“沉默權”。另一方面,聯系另一個同樣飽受爭議的舜“竊負而逃”的故事,當父親不是順手牽羊的小事,而是殺人之大罪,此時,“隱”的結果的限度應是“不以小道害大道”,“不以小愛害大愛”。
參考文獻
[1] 四書章句集注[M].中華書局,1983.
[2] 錢穆.論語新解[M].三聯書店,2002.
[3] 郭齊勇主編.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J].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 張志強,郭齊勇.也談“親親相隱”與“而任”—— 與梁濤先生商榷[J].哲學研究,2013(04).
[5] 梁濤.“親親相隱”與“隱而任之”[J]. 哲學研究,2012(10).
[6] 林桂榛.“父子相為隱”與親屬間舉證——親情、法律、正義的倫理中道問題[J].現代哲學,2010(6).
(作者單位:中共沈陽市委黨校)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