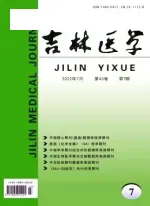腹部外科患者的個體化腸外與腸內治療
韓小英,徐 嵐 (天津市第三醫院營養科,天津 300250)
腹部外科患者因消化系統的病變會影響機體對營養物質的吸收和代謝,術后由于創傷應激反應,機體處于高分解代謝狀態,因此營養治療已成為腹部外科綜合治療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選擇營養治療方式和時間,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營養狀態以及如何維持機體正常的免疫功能是目前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本研究結合近年腸外(PN)、腸內營養(EN)領域的研究成果,2009年1月~2011年12月對我院48例腹部外科手術患者應用個體化營養治療,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依據住院患者的營養風險篩查2002(NRS 2002)對2009年1月~2011年12月我院普外科有營養風險的腹部手術患者48例,其中胃大部切除術10例,胃腸穿孔修補術4例,胃癌根治術10例,胰十二指腸切除術2例,腸粘連松解術6例,小腸部分切除術3例,結腸癌根治術8例,直腸癌根治術5例。隨機分為兩組,每組24例。治療組為腸內營養(EN)+腸外營養(PN)+治療膳食,男15例,女9例,年齡(61±17)歲;對照組為PN+治療膳食,男14例,女10例,年齡(59±20)歲。患者的肝腎功能均正常,無合并糖尿病、甲狀腺功能亢進等代謝性疾病,年齡、性別和病程等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營養治療方法:營養治療在術后48 h,患者呼吸、循環相對穩定與內環境紊亂基本糾正后才進行。兩組患者供給總氮量0.15~0.2 g/(kg·d)。非蛋白質熱量按 83.7~105 kJ/(kg·d),非蛋白質熱量:氮為418 ~627 kJ∶1 g。
EN:營養治療第1天滴注等滲糖鹽水500 ml,以20~40 ml/h勻速滴入;第2天始根據飼養管位置不同(鼻胃管、鼻腸管、空腸造瘺管等),給予能全素(整蛋白型)或百普素(短肽型)配制濃度5%的腸內營養液500 ml,滴速為20~40 ml/h,以后逐漸增加至濃度20% ~25%,滴速80~100 ml/h。
PN:以8.5%樂凡命、支鏈氨基酸為氮源,以50%葡萄糖、10%葡萄糖、5%葡萄糖、20%、30%脂肪乳劑為雙能源供熱,葡萄糖與脂肪乳劑所提供的熱量分別占總熱量的60%和40%;營養液還包括鈉、鉀、鈣、鎂、磷、微量元素、水溶性維生素、脂溶性維生素、谷氨酰胺雙肽等注射液;胰島素按1 U比4~10 g葡萄糖加入營養液,液體量根據患者每天出入量情況進行調整。上述基質在本科室層流凈化臺內,按照無菌操作配制,加入3 L靜脈營養袋中。外周靜脈或中心靜脈12~24 h連續輸完。
治療膳食:密切觀察患者腸道功能,逐步開始清流食、流食、軟飯及相關疾病的治療膳食。
治療組為EN+PN+治療膳食,早期先計算EN入量,不足的部分PN補足;在患者耐受的情況下逐漸增加EN量,減少PN,并適時增加治療膳食量。對照組為PN+治療膳食,早期以PN為主;在患者耐受的情況下逐漸增加治療膳食量,減少PN。兩組均應綜合患者每天生理需要和體液丟失量、臨床液體量確定PN、EN及治療膳食量。
1.3 監測指標:所有患者均于手術前、手術后1 d、治療后14 d(7∶00)抽取靜脈血,檢測營養指標:血清白蛋白(ALB)、血紅蛋白(Hb),外周血淋巴細胞總數(LC),并用皮摺厚度計測量三頭肌皮褶厚度(TSF);免疫指標:血漿IgG、IgM和IgA。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和組內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營養指標:兩組患者術后第1天血清白蛋白、外周血淋巴細胞總數水平均顯著低于術前(P<0.05);治療后14 d,治療組ALB、Hb、LC和TSF值均高于對照組,ALB顯著高于對照組(P <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術前、術后1 d、治療14 dALB、Hb、LC、TSF水平()

表1 兩組患者術前、術后1 d、治療14 dALB、Hb、LC、TSF水平()
注:與對照組比較,①P<0.05;與術前比較,②P<0.05
組別 時間 Alb(g/L) Hb(g/L) LC(×109/L) TSF(mm)對照組 術前 36.16±3.96 122.21±14.32 2.68±0.67 11.96±2.36術后1 d 29.32±3.25② 111.23±12.62 1.39±0.58② 11.80±2.69治療14 d 35.91±4.14 118.45±16.21 2.58±0.87 11.86±3.21治療組 術前 36.62±3.52 123.26±16.39 2.75±0.62 12.01±2.45術后1 d 29.61±3.67② 112.34±13.25 1.45±0.27② 12.88±2.63治療14 d 39.46±3.02①124.43±15.64 2.65±0.49 12.09±3.29
2.2 免疫指標:兩組患者術后第1天IgG、IgM、IgA均下降,治療后14 d治療組IgG、IgA治療組恢復較快并超過術前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術前、術后1 d、治療14 d血清IgA、IgG和IgM的變化()

表2 兩組患者術前、術后1 d、治療14 d血清IgA、IgG和IgM的變化()
注:與對照組比較,①P<0.05
組別 時間 IgG(g/L) IgM(g/L) IgA(g/L)10.86±2.88 1.15±0.45 2.38±0.74術后1 d 9.28±2.36 0.96±0.68 1.99±0.68治療14 d 9.86±2.75 0.99±0.62 2.01±0.85治療組 術前 10.66±2.67 1.18±0.54 2.47±0.98術后1 d 9.62±3.05 1.01±0.63 2.12±0.78治療14 d 14.30±3.36① 1.10±0.49 2.78±1.02對照組 術前①
3 討論
以往對圍手術期患者區分營養不良級別僅靠一般經驗,缺乏規范。歐洲腸外腸內營養學會營養風險篩查專題組在對128個關于營養支持與臨床結局隨機對照研究報告分析的基礎上,建立了營養風險篩查2002(Nutritional Risk Screening 2002,NRS2002),這是國際上第一個采用循證醫學資料開發的營養風險篩查工具。從三個方面對住院患者進行營養風險篩查評分:①營養受損狀況:包括BMI、近期體重及進食變化(0~3分);②疾病嚴重程度(0~3分);③年齡(≥70歲,1分)[1]。評分≥3分認為存在營養風險,營養風險包括:已經存在的營養不足和與手術或疾病有關的潛在的代謝及營養改變,可影響患者的臨床結局[2]。本研究依據NRS2002對外科住院患者進行營養篩查,進行營養評價,制訂營養治療計劃,給予臨床營養治療。
營養治療主要有腸外營養(PN)和腸內營養(EN)(廣義上應包括管飼和經口進食)兩個途徑。EN與PN相比,前者有助于維持腸道黏膜細胞結構與功能的完整性,維護腸道黏膜屏障功能,刺激消化液和胃腸道激素分泌,增加內臟血流量,使代謝更符合生理需求,可減少肝、膽并發癥的發生[3]。此外,EN具有技術操作簡單、并發癥少和費用低等優點。目前,“當腸道有功能時,利用它”已成為臨床營養治療的共識。但腹部外科患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腸功能障礙,主要包括腸道運動和消化、吸收功能的限制,這都使EN難以實施,盡管理論上認為術后6 h腸功能即恢復,但在實際應用中仍應視患者具體情況而定,主要是腸功能恢復的情況。因此,EN不應盲目追求在術后早期開始,應以腸功能恢復、患者能耐受為實施條件,營養治療的時機則推崇應激后24~72 h內以維護患者內環境的穩定為主,當患者的生命體征、水電解質和酸堿失衡糾正后再進行營養治療[4]。本研究的營養治療均在術后48 h進行。
患者術后EN大多需5~7 d的適應時間,循序漸進的方式增加喂養的濃度、滴數、及滲透壓等,可避免胃潴留、腹瀉等并發癥的出現。每天能量需求的30%以上由EN提供時,可滿足機體維護腸黏膜屏障功能的需要。國內和歐洲的指南中推薦對于有營養支持指征的患者,當EN無法滿足能量需要(<60%)時,建議考慮聯合應用 PN[5]。因此,本研究治療組患者,術后早期PN可保證營養供給,這時PN便成為營養治療的主要途徑;逐步過渡到EN、PN共存,營養成分互補;并根據患者耐受情況適時添加治療膳食,總熱量及營養基質是二者的相加。聯合PN和EN可優勢互補,優化營養治療療效。因此,當前營養支持途徑的選擇標準是“采用全營養支持,首選EN,必要時腸內與腸外營養聯合應用”[6]。
本研究表明:兩組患者術后第1天的各項體液免疫指標及營養指標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提示患者在術后早期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免疫抑制現象、營養不良現象,提示患者需營養治療。研究發現:營養治療14 d,兩組患者營養指標均較術后第1天升高,而且治療組IgA、IgG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治療組患者 ALB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提示營養治療能調節蛋白質合成,促進機體組織愈合,從而防止細菌易位和腸毒素進入血循環,增強機體的免疫能力,減少術后并發癥的發生和改善預后,而EN和PN聯合應用效果更為顯著。
綜上所述,要根據疾病的不同病因、不同時期,合理地選擇營養治療方式,及時地調整EN、PN的比例,使EN、PN在營養治療應用中相輔相成,使營養治療更加合理,同時也能減少營養治療并發癥的發生,促進患者術后更好的康復。
[1]Kondrup J.ESPEN Guidelines for Nutrition Screening 2002[J].Clinical Nutrition,2003,22(4):415.
[2]中華醫學會.臨床診療指南:腸外腸內學分冊[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16-18.
[3]孫 新,楊忠明,黃曼玲.合理腸內營養對危重患者蛋白質不良的改善[J].吉林醫學,2012,33(19):4037.
[4]秦環龍,楊 俊.外科營養的新進展[J].臨床外科雜志,2010,18(1):14.
[5]唐大年,朱明煒,孫建華,等.有營養風險患者術后腸內、腸外營養支持模式與不經篩查術后全部應用腸外營養對結直腸癌患者結局的影響:60例回顧性研究[J].中華臨床營養雜志,2011,19(6):355.
[6]黎介壽.臨床營養支持策略的變遷[J].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2009,16(12):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