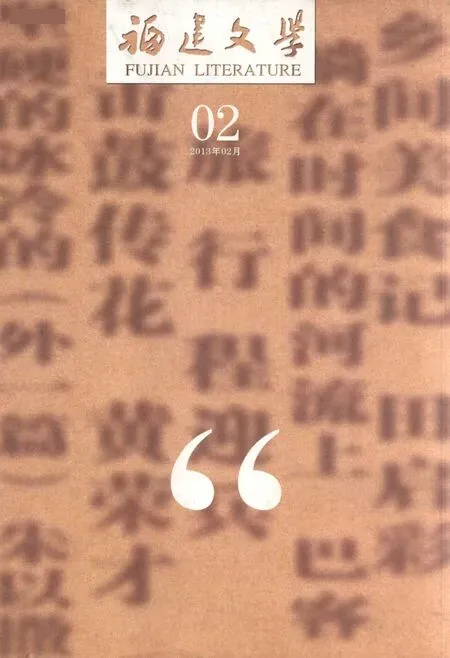堅硬冰冷中的守望和撫摸——我看朱以撒散文新作
□戴冠青
一直很喜歡讀朱以撒的散文,常常讀著讀著,就坐不住了,不由抬頭凝望遠方,試圖穿越歷史風云,為那個執迷不悟郁郁獨行直至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心灰意冷自我消失的屈原老頭而嘆息,為那個本該超塵拔俗激情蕩漾如大鵬振翮的詩人李白誤入長安屈己于人倍感壓抑而感慨,又為他終于走出長安回歸心靈自由回復詩人本性生命豪氣而歡欣。在朱以撒那些冷靜得有些冷峻的文字深處,總是有一種沉甸甸的力量在打動你,激發你去重新審視歷史思考文化,由此得到一種感悟和超越。
朱以撒的新作依然延續著這種冷靜審視歷史文化的敘事風格,我們依然可以從中感受到散文家生命歷程中發人深省的文化思考和獨特發現,只是更多了一份溫暖的訴求和對真實的尊重。在《堅硬的冰冷的》一文中,他從鄒城那些兩漢、北魏、北齊、北周的碑刻和漢畫像上發現了古人以付諸石頭的想象來延續其精神生命、傳達美好理想的智慧,“一個家族,或者一代人,把那些超越現實的想法放置在石頭上,實在智慧不過了。彼岸那個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誰也不清楚,可是想象幫助了現實生活中的人,把現實的、非現實的都付諸石上”,“漢畫像是漢代人生活和理想的縮影,我們可以清晰地區別那些生活在地面上的人,還有那些生活在天上的神仙,或者人和神仙都處于一個時空。這無疑是生之為人最美的憧憬”。因為石頭是堅硬的,不易銷蝕的,這就讓今人感受到了古人的生命溫度,所以散文家感嘆,再堅硬的東西也抵不過柔軟的生命,“柔軟的人和堅硬的石頭相遇,最終還是柔軟的人取勝——把各式場景,虛的實的,真的幻的都搬到石頭上,細如發絲的線委曲蜿蜒,像是要升到天堂上了”,石頭“儲存了一個時代人群的豐富信息”。是的,時光不可抗拒,誰也不可能長命百歲,但聰明的古人把他們柔軟的生命軌跡和人生憧憬留在了堅硬的石頭上,讓現代人能夠和古人相遇,讓生命能夠延續,讓歷史能夠留存,“正是倚仗堅硬的石頭,使我們如同親臨當時的人間生活,與一千多年前的人相遇,看他們鼓樂吹笙車馬出行的莊重,聽他們捕魚狩獵殺雞剝狗的歡樂。石頭對抗了時光,使那些光景還在寂靜的碑廊里,給滿懷希望的我們有了一個不虛此行的快樂”。在這里,朱以撒以一個文化學者的獨特眼光,在很多人常常錯過甚至無視的堅硬的冰冷的石頭上發現了生命的柔軟和溫度,發現了文化延續和存留的頑強和堅韌,讓我們守望和珍惜,其中所透露的人文情感十分動人。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散文家在敘事中巧妙地通過堅硬與柔軟的碰撞,構成了一個富有張力的藝術空間,引讀者流連其中,深入感受歷史文化帶給今人的無窮魅力。
在朱以撒另一篇紀游莫高窟的散文《懸念》中,散文家則告訴我們,歷史的東西就應該讓它歷史地存在,也許歷史會老去,洞窟也會荒涼,因為歲月是無情的。但荒涼的才是滄桑的,才是真實的,才是厚重的,才是自由的,會激發你的想法,你愛怎么想就怎么想,愛怎么創造就怎么創造,如他筆下早先在莫高窟臨摹的張大千,那時莫高窟尚未被改造,“他的自由度那么大,此窟進彼窟出,許多洞窟的秘密被他探得,他完全忘記了洞窟外呼呼作響的寒風”。也因此這個神秘的洞窟才有懸念,才能帶給遠行者種種新的生存體驗。如今,熙熙攘攘的人群涌進來,洞窟也被一次又一次的修葺弄得面目全非,秘密也沒有了,“一個封閉的小洞窟,如果沒有被發現,百年千年可以一直平安無事。秘密不被揭開是最好的,沒有波瀾漣漪,沒有雞飛狗叫。前人把秘密藏在洞窟里,本意就是不為人知。黑暗是對秘密最好的守護,一遇見陽光,秘密就消解了,再無懸念可言”。我想,散文家通過莫高窟的變遷似乎在告訴我們,原生態的才是真實的,哪怕會衰敗會荒涼,也是順應天時合乎規律的,“洞窟建在荒涼處,本身就是對外人的一種阻隔和謝絕,應時而起應時而衰,順天守時是最基本的規律”,“今人想替古人出場,那是一定要露破綻的”。歷史文化是守望的,而不是去叨擾和改造的。在這里,朱以撒以一個遠行者在昏暗洞窟中的獨特發現和深刻感悟,深沉地傳達出他對今人在古文化面前的無知和無惜的痛心,傳達出一個人文學者對歷史真實的尊重,其中的文化批判色彩看似溫和卻十分有力。
用手感覺歷史的滄桑,感覺文化的厚重,這是朱以撒散文的一個獨特視角。在他的石頭書寫中,我注意到了他常常用的一個詞“撫摸”,或者是“摩挲”。他說:“現在我像面對一位滄桑老人了,我撫摸這些凹凸不一的刻痕,就像撫摸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骨節,寒煙衰草,凄風淡月,再旺盛的生命陳放于此,都會慢慢鈍拙,老去。再往后的人來了,興許就沒有什么痕跡可尋了。”“唯有石頭,它的普遍和經濟,成了最適宜的寄寓。在堅硬中冰冷中撫摸,這真是一種長于自守之物,凝重是它的本性。”我們可以感受到,不管散文家在這里撫摸的是石頭上的刻痕,抑或是老人手背上的骨節,其實都是在觸摸歷史,在觸摸中感覺歷史的滄桑、凝重和生命無可奈何的蒼老,那種深情的撫摸,那份悲憫的情懷,讓人怦然心動。
但不僅僅于此,當我深入解讀時,我還感覺到了散文家在“撫摸”中的精神追求。他說:“石頭被熱愛,是不多的一些人的癖好,所到之處往往清冷,卻會在不斷地摩挲之中,溫熱起來。”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散文家“撫摸”的初衷所在,他正是希望通過“不斷的摩挲”,讓遠去的生命“溫熱起來”,讓埋藏在清冷的歷史深處的某種美好的東西復蘇。因為這種執著的撫摸,因為這種對生命溫暖的渴望和尋找,更因為對某種美好的東西被歷史遮蔽的無奈和傷感,讓朱以撒的散文具有一種讓人沉思的情感力量。
瑞士的原型批評理論家榮格曾在某些原始藝術中看到了“人類遠古生活的共同經驗”,是遠古社會人類心理經驗的結晶,是一種“種族的記憶”。同樣的,朱以撒也在這些古老的石頭藝術中發現了中國先民的生命軌跡和種族記憶。他筆下那些堅硬的冰冷的特別是那塊長年隱沒于荒野中的葛山摩崖石刻,讓我們深切感受到了千年前的書寫者和鑿刻工匠們那種平和沉靜、不急不躁、從容淡定的生存智慧和生命態度,他說:“我們更多的是欣賞它雍容的筆調,閑庭漫步式的從容,這位千年前的書寫者,還有一批承擔鑿刻的工匠,都是這般慢條斯理,不急不躁,展開手工細活。那時的山野沒有路徑,荊榛蒺藜塞途,要有多少誠心耐性,才能使這片摩崖開出一片花來。我把這種結果歸結為信仰的力量,或許降低一點,說是癡迷吧,使許多虛幻最后落實到實在的手工勞作之中。”他還在北朝的拓片中發現古人的生活態度,“我好幾次說,要在自己的書房,掛滿這些北朝的拓片,人居其中,時日久了,人的情調、筆調一定要發生變化。這是一種與時下不同的氣味,安和的、質樸的、不動聲色的”。其實,何止是發現,更多的是欣賞和追求,是散文家的審美胸襟和價值取向的獨特投射!
我們知道,文學作品不僅藝術地再現了客觀世界,也獨特地表現了作家的情感和審美理想,蘊涵著作家深刻的生命體驗和豐富的心理活動。由此可知,這一段平和內斂的訴說,與其說傳達的是古人的生存情狀,不如說是散文家自己的人生態度。在我的印象中,朱以撒一直是這樣一個追求質樸生活的人,他曾在第一本散文集《古典幽夢》的后記中說:“像我這般喜愛古風的人,既不想開空調,也不想用電風扇,以一把蒲扇消夏。一篇篇地重讀,回首向來寂寞處,竟然也心清如水涼意驟生。”在《懸念》中,同樣有這樣的表述:“這個年深日長的洞窟,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修葺,已經和老照片上的那種草莽模糊狀態大相徑庭了。我還是喜歡以前那個樣子,很真實,也很質樸潦倒。現在倒像是穿上一件新衣,擺一副架子。原先的味道嗅不到了——荒涼、蒼涼、悲涼,還有岑寂,這些洞窟里曾經有過的元素,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都沒有了。”對古風的熱愛,對“荒涼、蒼涼、悲涼,還有岑寂”這些原生態的念想,對曾經的真實質樸被改變甚至被改造的惋惜,都真切地傳達出了散文家的審美理想。在當今浮躁紛擾、急功近利的消費社會中,我想朱以撒對沉潛靜默的石碑和洞窟文化的審視和抒寫,也許表現的正是這樣一種試圖與浮躁現實抗衡的具有古代名士之風的平和淡定、返璞歸真的審美胸襟和生命追求。
當很多本應甘于寂寞,本應守護內心寧靜的文人也被當今熙熙攘攘的消費社會所裹挾而沉浮其中時,讓我們讀讀朱以撒的散文。也許他所傳達的審美胸襟和生命追求已被很多人所無視所淡忘,但卻是應該被喚回被守望的。我想,這應該是朱以撒散文最值得我們反復咀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