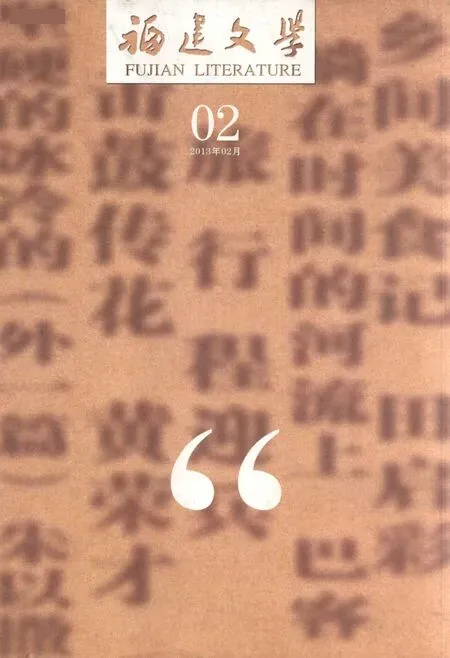穿越郁香巷
□劉會剛
郁香巷不到二百米長,三四米寬。因周遭高樓林立,里面難見陽光,長年陰濕,絲絲縷縷散發出甜腥而腐敗的氣息,但也是個吃穿用度的小世界,早點攤、水果店、美容室、刻印社、麻將館、首飾行、紅磨坊、沱江魚府、盛昌洗浴、全順租車、紅娘熱線、巾幗鐘點、木蘭家政……當然也有就著巷子兩邊擺地攤的小商販,賣一些光怪陸離的小玩意,煞是吸引人。
細女每天經過郁香巷,腳步總會慢下來,好像巷子兩邊形形色色花花綠綠的店鋪,粘住了她的目光,絆住了她的腳跟,稍不留神就會一個趔趄,撲到一個行色匆匆的人身上。好脾氣的,瞪一眼了事。不好說話的,就惡語相向。那次,她不小心踩到一個胖女人的腳。哎喲一聲尖叫,像京劇的唱腔,頓時劃破空曠的巷子。繼而是雷暴般的叱喝子彈般飛來,媽耶,疼死老娘……你個鄉巴佬,鄉巴佬,眼睛瞎了——細女驚恐萬狀,臉色慘白,一個勁地賠不是,對不起,大姐,對不起,俺不是有意的。在行人復雜目光的注視下,胖女人一手提著受傷的腳,一手捂著臉,齜牙咧嘴,好像臉也被踩了一腳,倒了八輩子霉,出門遇到一個鄉巴佬。胖女人說完,一拐一瘸地走了。這種情形雖不是經常發生,但也絕非偶然。這讓細女有些不自在,也有些迷離,她似乎有種預感,好比自己的身體,到了每月的那幾天,感覺就來了。每次有感覺時,她走進郁香巷總是特別小心,盡量一步一個腳印,與行人保持足夠的距離。即使這樣,擔心的事該來還是來了。因為,你不撞別人,不等于不被別人碰。
那次,一個冒失鬼,慌不擇路地沖進郁香巷,突然像頭發瘋的公牛,一下子頂翻了她,慣性使然,細女順勢撞向前面的行人,這下不得了,五六個人多米諾骨牌般倒下,要命的是,其中有位七十多歲的太婆。太婆似乎摔得很重,躺在地上,麻花般地扭成一團,痛苦地呻吟著。此時正是上班的高峰期,郁香巷瞬間被堵得嚴嚴實實,很快,警察趕來,將太婆送到醫院,經檢查,無甚大礙。虛驚一場。細女雖沒有蝕財,但耽誤了半天時間,扣了獎金,還遭到老板一頓訓斥。
細女打工的鹵菜店在城南的鬧市區,而她的租住屋位于城北的城中村,如果步行上班,穿過郁香巷,也就刻把鐘的樣子。當然有公交車可坐,可細女一次也沒有坐,不是不想坐,而是舍不得花一塊錢。穿越郁香巷上班,好處也有很多,除了省錢,還能省時,省力,更為關鍵的是,細女喜歡走郁香巷,每次走進人來人往熱鬧非凡的郁香巷,感覺很好。到底好在哪,細女說不出個所以然。其實呢,這是一條老巷,破舊,殘敗,如一個行將就木的老嫗,靜靜地臥在這個城市的深處。人們忘不了這條巷子,很大程度上,因它處于這座小城的中心,南來北往的人,喜歡穿越它,這叫抄近路,走捷徑。有想像力豐富的人,還把郁香巷想象成一個遲暮美人,現在它是老了,老掉牙了,老得體無完膚,地面常年積水,坑坑洼洼,不小心一腳踏上去,污水四濺,蚊蠅亂飛。可它也有年輕光景,風華絕代時,誰能想象得出它的風流與魅力?
細女不可能去想象郁香巷的前世,畢竟她才二十三歲,從農村進城不到三年時間,她只能看到郁香巷的今生。前世的郁香巷,前世的郁香巷的故事,與她無關。而她要做的,或者說,要想的,就是每天全力把鹵菜店的生意打理好。這是她做為一個打工妹,立足城市的唯一資本。這家鹵菜店設在一家大型超市內,一排玻璃櫥窗,擺滿了鹵雞鹵鴨鹵蛋鹵牛肉鹵花生米,每天都賣得精光,連個鹵雞翅膀尖都不剩。許是小城人油的葷的吃壞了胃,對鹵制品格外鐘情。盡管生意興隆,但老板發給細女的工資一成不變,每個月七百五十塊,不多不少,是這座小城的最低工資標準。因此,細女不得不節省,不得不計算,除了吃飯穿衣,她幾乎不敢花什么錢。逢年過節回老家看父母,也是兩提黃石港餅,或三袋白鴨皮蛋,都是這座小城的土特產。便宜,實惠,拿回老家八字門,張家分一點,李家送一點,既做了人情,又好看長臉。
說來也怪,每次回老家前,細女睡不香,吃不好,恨不得插上一雙翅膀飛回八字門。可在家呆了不到半天,她莫名其妙地變得抓狂起來,煩躁起來,看啄食的雞不是雞,看吃屎的狗不是狗,兩眼無神,雙唇發白。母親看在眼里,輕嘆一聲,默默地為她收拾行李。像對待貴客一樣,還不忘往她包里塞十幾個老母雞下的土雞蛋。這是自家養的雞下的,純粹的土雞蛋,個兒小,兩頭尖,有的還帶著雞屁股的余溫。細女當然不可能去體會雞蛋的個頭與溫度,她的心早已像鴿子一樣撲棱地飛回小城。當車子穩穩地駛入市區,城市的高樓大廈漸入眼簾時,細女風急浪高的心湖才漸漸平息下來,臉上像喝足了奶的嬰兒,露出富足而安詳的神態。小城有什么值得她如此貪戀呢。母親不明白,細女自己也說不好。她就是覺得,自己天生屬于城市,只是上帝誤將她像個棄嬰一樣丟在偏僻的農村,現在,她要找回原本屬于自己的生活,她要同以前的自己一刀兩斷,同老家八字門劃清界限。
城里的條件的確很好。恍惚中,細女覺得自己曾經在此生活過多年,一切都顯得是那么熟悉,很多地方還留有她鮮活的氣息和模糊的足跡。那錐子一樣聳立的高樓,那形態各異奪人眼球的招牌,那馬路上流水一樣延綿不斷的汽車,還有那穿著吊帶裙的女人招搖過市,這種裙子露肩露骨,性感十足,她以前只在電視里見過,沒想到在大街上像看大戲一樣舉目可見。最令她鐘情和糾結的,還是郁香巷,她喜歡郁香巷,就像喜歡城市,喜歡城市生活,沒有理由可講。可每次穿越郁香巷,她既心生歡喜,又莫名郁悶。為什么自己走進郁香巷,經常像頭迷失方向的羔羊,跌跌撞撞,找不著北呢?事情越是刻意避免,它偏偏奇怪地要發生。那天傍晚,她正走在郁香巷,突然感到身后有個硬物頂上來,軟軟的。回頭一看,嚇得差點一口氣沒緩過來。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男人,西裝革履,手里提著一個锃亮的公文包。身子緊貼著她,下身竟露出那個碩大的物件,像條猩紅的蟒蛇探出來,興奮地搖頭晃腦——流氓……細女猛地邊喊邊跑,一連沖倒多位行人,還撞翻了路邊的烤薯爐,大大小小的熟薯滾了一地。
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難道自己陷入了什么精神魔咒?抑或是神經幻覺?細女冷靜地思考了幾回,漸漸地悟出了什么,問題似乎不在自己,而在于郁香巷。這條巷子,對細女來說,充滿著神秘氣息,曖昧色彩,還有種虛無縹緲的玄機。如果有前世,她相信自己的前世一定與這條巷子有關系。直到有一天,細猴突現郁香巷,她才徹底明白,這的確不是一條普通的巷子。
那天傍晚,大約六點多鐘的樣子。太陽落下去,紅霞撲上來,回光返照使郁香巷里的光線正好,不明不暗,柔和,涼爽。巷子里的小攤小販,又開始擺弄起晚上的生意。攤上各式各樣的小玩意,閃閃發光,有的像小鳥一樣嘰嘰喳喳,有的像青蛙一樣呱呱呱呱,還有的發出激光一樣五彩的光。此時過往行人漸漸多了起來。細女下班后,本來是與同伴黃花一起走的,中途,一帥哥像個飛毛腿導彈,精準地攔截了黃花,拋下細女一個人無著無落地飛。黃花與細女一起賣鹵菜,也是從農村來的,年紀比細女小兩歲。黃花長得真像一朵春天里的黃色小花,常常引來各路蜂蝶嗡嗡嗡嗡,不絕于耳,讓細女既羨慕,又嫉妒。可她知道自己長得不如黃花,可能連黃花的一瓣花朵都不如,沒有男孩子會圍著她跳舞,更甭提采蜜獻殷勤了。這不免讓細女很郁悶,更多的時候是沉默。而此時,心里的潮水又開始泛濫成災。以前遇到好看的好玩的,她都要停下來,或干脆蹲下來,摸一摸,瞅兩眼,現在,她看什么都不順眼,恨不得插上翅膀飛出郁香巷,好像來來往往的人身上都長著長毛刺,稍不留神就會刺傷自己。
走了幾步,她感到身后有異樣的目光,像軟鏈子一樣,甩過來套住了她的雙腿,腳步竟有些踉踉蹌蹌。心里不由一緊。近段時間,報上經常刊登郁香巷有歹徒出沒的新聞。已經發生了幾起。其中,最殘忍的,是一個女的,身上二百多塊錢被搶外,還遭到幾名歹徒的強暴。這個惡性案件,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視,公安局長坐鎮指揮,誓言緝兇,給百姓一個滿意的答復。可過去了差不多兩個月,不聞鐘響不聽罄響,自然引發市民的更大恐慌。深夜,走郁香巷的人越來越少,即使走,也是三五成群的,結伴而行。細女緊張得要命,側身拐進一條胡同。這是郁香巷深處的一條胡同,這樣的胡同,巷子里有五六條,歹徒都是借著這些曲里拐彎的胡同作案,然后伺機逃跑。
細女屏住呼吸,探出頭,偷偷觀察郁香巷周圍的情況。人來人往,似無異常。此時天漸次暗下來,幾聲悶雷響過,天好像要下雨了。細女小心地吁了一口氣,走出胡同,加快腳步。快到巷口時,猛然斜插出一個人,樹樁一樣立在跟前。細女嚇得心快跳了出來,人傻傻的,呆立著。是細猴,那個像猴子一樣的男人。細女身子緊縮成一團,似乎遇到一條吐著長長信子的蛇。細猴蓄著長長的頭發,胡子拉碴,瞇著眼,嘴角叼著煙。裸露的胳膊上,紋著一條龍,發出熒藍色的幽光。細女退后兩步,本能扶住路旁一根電線桿。幾個月不見,她沒想到,細猴會變成這樣。簡直認不出來了。
細猴是個什么人呢。細猴與細女是小學同學,人瘦,皮膚黑得像個非洲人,是個從未拜過師但壘起屋來像模像樣的砌匠。這證明他是個精明的人,智商不低,在農村絕對是個吃得開的主,但細女一直瞧不起他,總取笑他吃沒吃相,坐沒坐相,走起路來像討飯一樣,干起活來像耍猴一樣,是個完全沒進化好的猴子。當然,細女對自己的長相,也是有數得很。寬臉龐,塌鼻梁,細眼睛,整個五官給人一種過度壓縮的失調感。好在,她個子高挑,這一筆將整個人脈改變了。胸有了,腰有了,臀有了,修長的雙腿也有了,這些也夠吸引花花男人的目光。細猴算其中厚顏無恥的一個,他曾經直截了當地對細女說,我猴,你丑,半斤對八兩,正可謂一個要皮絆,一個要絆皮。皮絆是當地人形容男女不正當關系的,細女聽了又急又氣,又氣又惱,又惱又恨,滿肚子委屈卻找不到詞兒來還擊,只有一個勁地呸呸呸呸呸呸呸,一連吐了十幾個呸,似乎要將那個夏天晚上的不堪之事像一口濃痰從嘴里吐出來。可越是這樣,那一幕如一枚鐵釘尖銳地嵌入細女的肉體與靈魂,成了一個永遠無法抹平的傷疤。
說起來都是露天電影惹的禍。當時鎮里正搞電影下鄉,多少年沒看露天電影的村民,似又回到了幾十前的激情燃燒的黑白世界。不過,有人覺得看電影不過癮,不如看人來得痛快。這人就是細猴,細猴趁著朦朧的夜色摸進細女家,手腳利索地把她睡了。這事放在城里,是驚天動地的大事,鐵定進號子吃牢飯,可在農村,事情變得復雜起來,曖昧起來。都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鄉親,你一言,我一語,七說八說,壞事竟說成了好事。知根知底,正好一對嘛,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細女父母清楚女兒的處境,長相擺在哪兒,人不傻但也不聰明,能找個靈光活泛的男人,也算是一種造化。就驢下坡答應了這門親事。細女開始極力反抗,可經不起父母的威逼利誘,細猴的死纏爛打,加上親戚朋友的好說歹說,竟半推半就同意了。不同意不行嗎?行,可以尋死。細女那天的確抓起一瓶敵敵畏,聞著氣味刺鼻的農藥,她害怕了。她不想死,她想活著。活著多好,每天累了能睡,渴了能喝,餓了能吃,她最愛吃向日葵瓜子,甜的,咸的,甚至是辣的,都愛吃,且百吃不厭。為此沒少挨母親的罵,一個女孩子,如此貪吃相,長大后如何嫁人?細女當然想嫁人,她還想長大后嫁個好男人,好好做愛,生個白白胖胖的兒子,然后一家人甜甜美美過日子。可現實與理想是兩回事。既然死不成,只有離家出走。一個黑黝黝的深夜,她一個人偷偷背起包裹進城了。進城后的細女,猶如找到了一個世外桃源。又驚又喜。幾經周折,最終找到一份鹵菜店的工作。生活環境變了,細女自身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她漸漸適應了城里的一切,也漸漸遠離了鄉村八字門,遠離了父母和土地,更遠離了那個像猴子一樣的男人,偶爾回老家見到細猴,雙手不自覺地驅趕,拍打,像要追打一只可惡的綠頭蒼蠅。吃不上嘴的細猴,有時急不可耐,直接進城找她。城里不比鄉下,打蠻纏經是行不通的。有一天,細猴費了好大勁找到細女的出租屋,欲像那個夏天的晚上霸王硬上弓,細女再不是那個膽小怕事的農村妹,她凜然伸出雙手,如兩把利劍,寒光閃閃,不讓細猴近身。畢竟男人力量大,對峙了幾分鐘,細女大汗淋漓,腿發軟,手抽筋。細猴見機撲食,將細女摁倒在床。手忙腳亂之際,細女使出最后一點力氣,扯開喉嚨吼了一嗓子,流氓,抓流氓——很快有腳步聲傳來,細猴嚇得提起褲子,溜得不見蹤影。從此再也不敢登門耍不軌行為了。
細猴死死地盯著她,目光中射出邪惡的意念。看來自上次強行騷擾后,這家伙色心不死,一直惦記著。細女抬腕看了看表,七點差一刻。郁香巷此時完全黑下來了,遠處近處的燈光都亮了起來。有歇斯底里般的音樂流出來,撞擊著行人的耳膜。細女暗中做了一次深呼吸,強迫自己鎮靜下來。她想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于是,高昂著頭,挺起胸脯,雙腿像兩根呼呼生風的雙截棍,走出郁香巷。
細女知道這個男人不會輕易放過自己。走了大約十幾米,果然,身后傳來一聲斷喝,站住……站住——細女站住了,但沒有轉身。這時她心里有數了,這個像猴子一樣的男人,不會拿她怎么樣。畢竟這是城市,是在大街上。細猴跟了上來,氣急敗壞的樣子,你,不是細女,你——到底是誰?
問話太突兀,細女一時拐不過彎來,不得不扭頭看了一眼細猴,想笑,卻笑不出來,臉上仍掛著一副不屑的神情。細猴的嘴臉軟了,用討好的語氣說,我知道你是細女,但真的不像細女,你,變了……變好看了。剛才你從郁香巷走出來,我真懷疑自己看錯人了。細女實在忍不住,笑了一下。人一笑,緊張的氣氛緩和了許多。細女輕蔑地說,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吧。細猴含糊不清地說,你……真的,變得——好看了。騙你我不得好死。其實,這幾天來,我一直在郁香巷蹲守,每次看你經過這里,我……簡直認不出你了,你變好看了,與以前不一樣了。細女心里隱隱升騰起一股甜絲絲的味道,就像三月三母親蒸的白饅頭,遠遠就能聞到那種透徹肺腑的清香與富足。她慢慢拿正眼瞧了一下細猴,若有所思地說,你的意思是,我每次穿過郁香巷,就變得好看了,不穿過郁香巷,就不好看了?聲音很輕,但語氣很重。細猴點點頭,又搖搖頭,最后又點點頭,囁嚅道,說不好……反正你——變得越來越好看了。說完,竹竿樣的身子一閃又一閃,消失在街角。
沒有細猴騷擾的日子,細女的生活過得平靜,踏實,也有規律。每天按時上班,準點下班,一到休息日,或窩在屋里美美地睡一覺,或約小妹黃花去逛街。是什么都不買的那種逛,走哪算哪,有啥看啥。有時,她腦海里會閃過那張猴子似的臉。不是忘不了這個男人,而是忘不了他說過的話。他說自己變好看了,越來越好看了,是真話,還是戲言,她相信這是真話。
其實,說她變好看了,不是細猴第一個說的。黃花不止一次說她變漂亮了。黃花說這話時,嘻嘻哈哈的,一點正經都沒有。為此細女沒在意。一個女人說另一個女人漂亮,就像一朵花說另一朵花艷麗,是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現在,這話從細猴嘴里說出來,從一個近乎流氓無賴嘴里說出來,且說得鄭重其事的,這就讓細女不能不當一回事了。她曾在出租屋里,拿出在郁香巷買的小圓鏡,一遍又一遍地照自己,鼻子還是那個塌鼻子,嘴唇還是那個厚嘴唇,小眼睛似乎比原來大了些,整張臉看上去,似乎與以前無甚區別,怎么別人都說自己變漂亮了呢。細女有些不解。可現實的情況是,別人都認為自己變了,變漂亮了。現在每次回老家,遠遠地還未到家門,就有村里老者或婦女,投來羨慕的目光,或喋喋不休地夸贊,這小妮子,到底喝了城里的江水,皮膚白了,也越來越漂亮了。那口氣,好像是,城里的江水,是美容護膚品,誰用誰就會變得好看。聽著這些溢美之詞,細女當然受用。更注重梳妝打扮了。原來,從不用描眉筆,基本不用唇膏,現在,每天上班前,在臉上涂涂抹抹要花半個小時,也不知涂抹了些什么。
自認為變好看的細女,再次走進郁香巷,感覺比在別的地方不一樣。到底有什么不一樣,她說不出來。只是覺得自己一舉手,一投足,都有不同尋常的內容。明顯的感覺是,她個子高,走在逼仄的郁香巷,有一種鶴立雞群的優越感。還有那雙修長的大腿,在郁香巷過往的千百雙各式各樣的大腿中,異常醒目,用熠熠生輝來形容一點不過分。更令她暗暗稱奇的是,一走進郁香巷,她無比興奮,渾身充盈著裂變的力量,就像一株正揚花抽穗的稻谷,漿汁飽滿,熟稔暗涌,讓她心生歡喜,青春蕩漾。又像走在T型臺上,無數雙眼睛激情滿懷地注視著自己,掌聲與鮮花從四面八方涌來,她是唯一的表演主角,欣慰,怡然,昏眩,真正有明星般的感覺。
為什么在其他地方沒有這種感覺呢,難道又是郁香巷的魔法使然?
其實細女心里知道,這是一條乏善可陳的巷子,人們忘不了這條巷子,很大程度上,因它處于這座小城的中心,南來北往的人,必須穿越它,這叫操近路,走捷徑。細女的人生捷徑在哪里,她不知道,盡管她確信自己真的變漂亮了,變好看了。
一天,黃花神情抑郁地告訴細女,她懷孕了。她想讓細女陪她去醫院做人流。吃驚之余,細女問是誰的?黃花努力地想了一下,木然地搖搖頭。不會不知道吧,細女再次吃了一驚。黃花吞吞吐吐地說,她找過,他們……都不承認,都不想負責——黃花哇地哭了。捂著臉,淚流不止。細女心里很難受,更氣憤,這些臭男人,沒一個好東西。不能便宜他們。細女要帶黃花去找他們,一個一個對質。有了牛兒,順著牛繩不愁找不到母牛。黃花受到驚嚇似的,不自覺退后兩步,不,不去……沒有結果的。他們沒一個好人。細女無奈嘆一口氣,只好帶黃花去了中心醫院,這是這座小城最好的醫院。細女長這么大從未看過婦產科,不知道婦產科到底是干什么的。進去之后,才知道,人流是個小手術,幾十分鐘的事,不必住院。懸著的心才落了地。反過頭來勸慰黃花,不要太擔心,沒事的。聽醫生說,人流就像屙了一泡尿。尿完了,人就輕松了,舒坦了。黃花還是怕,眼里滿是恐懼,手死死地抓住衣角。婦產科很是熱鬧,前來做人流的女人,排成一條長龍。有人掇著茶杯不停地喝水,顯然在憋尿。有人不停地走來走去,像在練體操。黃花冷不丁問細女,為什么要憋尿?細女回答不上來。但不回答不行,想了想說,尿憋急了,憋到一定程度,就像水庫積滿水后,陡然一拉閘,那個東西就會隨著湍急水流一股腦兒帶出來。不會痛的。黃花哦地點點頭,不再吱聲。很快輪到黃花了,人進去后,細女坐在椅子上等了不到十幾分鐘,醫生出來了,手上端著一個盤子,說要找黃花的家屬。細女慌慌張張地站起來,用手指指自己。醫生將盤子中的一只杯子交給她,讓她上五樓的專家診室確診。細女顫抖著,牙齒打架似的問發生了什么事。醫生簡單地說,沒有刮到毛毛,只刮出子宮的一些息肉。怎么會這樣呢。細女不解。醫生顯得不耐煩了,看專家,不是讓你看專家嗎?細女頭腦嗡地一響,心急火燎地找到專家室,專家看了一會兒實物,又看了看黃花的病歷,寫了幾行字,天馬行空的,看不清楚。回到婦產科,黃花已經出來了,臉色慘白地躺在一間病房床上休息。身子下面一片猩紅。觸目驚心。到底是怎么回事?黃花虛弱地說,醫生解釋不是懷孕,目前病因不明,回家好好休息幾天,再來復查。黃花就這樣消失了。這以后,細女再也沒見過黃花。不知道她的病怎樣了。細女為此傷心不已,憔悴不堪,如大病了一場。
再次走進郁香巷,細女腦子里像塞滿了玻璃碎片,一會兒映射出細猴的背影,一會兒疊現出黃花痛苦的表情,一會兒是自己的外貌,時而清晰,時而模糊,交錯出現,變幻莫測。
很快,又來了一位小妹。山背農村的。生澀,靦腆,顯然是剛走出初中學校的大門。天下打工妹的經歷都是相似的。家庭貧困,讀不進書,只好早早地踏上社會,打工掙錢。然后,企望找個好男人,把自己嫁出去。細女也想把自己嫁出去,她年紀不小了。跨過年,實歲二十四,吃二十五歲的飯。父母快急出個病,一個女孩子,年齡越往上走,麻煩越往下來。要是在農村,細女早是兩個孩子的媽了。可現在,細女生活在城里,城市不像農村,城市就像大海中的漩渦,大城市是大漩渦,小城市是小漩渦,人看起來相隔很近,其實彼此相隔十萬八千里。要想找到一位知心愛人,困難重重,稍不留神還有可能被陷入深不見底的漩渦中,永劫不復。
小妹嘴巴很甜,管細女叫細姐,一口一個細姐,叫得親熱,甜蜜,就像在叫自家的細姐。細女順其自然叫她小妹。這個小妹是個聰明的精靈,人長得不算漂亮,但很會來事,看著讓人舒服。男孩子一定會喜歡的。細女在心里說,自己要有小妹一半的機靈勁就好了。
小妹也租住在城北的城中村,只不過不與細女住在一塊。每天下班兩個人一起穿過郁香巷,一個往東,一個往西。各奔東西。
一天傍晚,小妹走遠了,細女不知什么原因卻站住了。她盯著小妹的背影,眼睛直直的,像鐵鉤子一樣轉不過彎。她以前怎么就沒注意到,原來青澀如酸蘋果的小妹,竟也有性感十足的一面,小蠻腰,小屁股,一對馬尾辮,走起路來,像一只可愛的獾豬一拱一拱的,煞是惹眼。細女嘆了一口氣,又嘆了一口氣。身子已經傾出去了,可雙腳卻被磁石吸著一樣,邁不開大步。她鬼使神差地轉過身,出神地凝望著郁香巷。此時,正值黃昏時分,一縷陽光射進郁香巷,映得四周金光閃閃,像一個天上的街市,美不勝收。細女輕輕地呼了一口氣,像回望久違的記憶,親切而溫暖。此時從郁香巷走出來的人,一個個超凡脫俗,似不食人間煙火,男人,一個個英俊瀟灑;女人,一個個柔媚驚艷。那一排排店面,如一座座宮殿,霞光萬道,熠熠生輝。這哪里是凡間塵世,簡直是苑若仙境,人間天堂。細女心里波瀾起伏,胸口怦怦怦跳個不停。真好,她對自己說,話音剛落,腳步已不由自主地走進郁香巷,身子已融入這天上的街市。她真的像一頭迷失的羔羊,闖入了一片綠草地,這里水草豐美,景色宜人,芳香四溢,氣象萬千。她貪婪地呼吸著,張大嘴巴,只覺異香撲鼻,口感生津,渾身充盈著無比喜悅的力量,推動自己不知疲倦地穿行郁香巷。這個傍晚,她從巷子這頭走到那頭,又從巷子那頭走到這頭,仿佛走了一個世紀,走進了洪荒時代。直到天完全黑下來,四周燈火如繁星點點,她才停下腳步,人虛脫得氣若游絲,花枝亂顫。
這以后,穿越郁香巷,成了細女的一個行為習慣。她也確信,穿越郁香巷,真的能使自己變得越來越漂亮。每天上下班自不必說,即使是休息日,她有事無事,也要穿越郁香巷,每次三五個來回。似乎不這樣,她心不安,食不甘,寢不眠。細女不覺得這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覺得這很好,就像有人喜歡打麻將,有人喜歡旅行,有人喜歡唱歌,有人喜歡看電影,還有人喜歡聊天,三五個女人坐在一起,唧唧呱呱半天,不知說了什么。而她,喜歡走郁香巷。每走一次,她都感到精神愉悅,身心俱佳,一種直抵肺腑的幸福通電般觸遍全身,就像母親小時候撫摸自己的身體,安詳,舒適,滿足。
最先發現細女這個怪異嗜好的,是小妹。
開始,小妹以為細女是在逛郁香巷,挑選物品。郁香巷尤其到了深夜,各種打折物品越打越厲害,有的甚至打到七折八折。觀察了幾次,不對勁。細女根本沒有買物品的意思,她來來回回地穿行于郁香巷,像走在一個人的大道上,走得醉心,走得沉實,步態穩健,一搖一擺,沒有半途停下來的肢體動作。小妹很驚訝,繼而很害怕,不敢揭穿這個秘密。好像一觸碰,會有一支利箭朝她兇猛地射來,錐心刺骨。為此,小妹漸漸與細女疏遠了,上下班,也很少一起走。尤其是到了郁香巷,小妹像躲避瘟神一樣,遠遠地與細女拉開了距離。
那天深夜,凌晨一點鐘的樣子。細女輾轉反側睡不著,頭有些隱隱作疼,似著涼的前兆。起來后,喝了一大杯溫水,趿著涼拖鞋出了門,像被神靈牽著鼻子七彎八拐地來到郁香巷。此時的郁香巷,行人已經很少了。偶爾走來一位,也是行色匆匆,步履像逃荒一樣踉蹌。細女緊了緊身子,從容不迫地開始了穿越。夜色如水,很快漫濕了她的全身。有幾家小店,透出昏黃的燈光,映在細女身上,一閃一跳的。走了兩個來回,細女感到有些累了。這幾天,她身體不適,好事來了。全身酸軟得要命。她準備返回,一條黑影突然從胡同里躍出,如一匹矯健的狼,直撲向她。細女驚恐地叫一聲,她感到地動山搖,渾身痙攣不已。黑影一手死死地箍住她的腰,一手嚴嚴實實捂住她的嘴,壓低聲音,兇狠地吼,別叫,叫就捂死你。細女嚇癱了,但意識還算清醒,借著小店折射出來的昏黃燈光,她看清了一張臉。那挑戰似的眼睛在匕首般的眉毛下發出貪欲的光。可那分明又是一張清純且明顯稚氣未脫的臉,大眼睛,高鼻梁,尤其是左嘴唇下那顆亮晶晶的黑痣,如一發子彈,瞬間射進細女的心,疼得她完全昏厥過去。隱隱中,她感到一雙有力的大手,扯開了自己的褲子,還有內衣……好久,耳邊傳來罵罵咧咧聲,如夏日的一陣悶雷滾過,他媽的……惡心,算老子倒霉——也許是細女微弱的呼救聲,驚動了沉寂的郁香巷,聞訊走出來的人,看到地上有血跡,趕緊報警,并將她送到醫院。
很快,色狼落網了。所幸細女沒有受到傷害。地上的血跡,是她的好事留下來的。但警方在色狼的供述中,發現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案情細節:一個女孩子,深更半夜穿行在郁香巷干什么?意欲何為?此疑點警方隨即在小妹處得到證實。小妹詳細筆錄了自己的發現。鐵的事實面前,細女極力解釋,可她解釋不清楚,她真的解釋不了這種自己認為是正常的而在別人眼里是怪異的行為。
出事后的細女被炒了魷魚,鹵菜店老板的理由是,她的精神有問題,或者說,神經出了毛病。
多年以后,人們發現,不再年輕的細女,在小城集貿市場一角擺了一個菜攤,距郁香巷僅一條街之隔。還是操老本行,賣鹵菜,鹵雞鹵鴨鹵蛋鹵花生米。而給她打下手的,是她的男人。打死人也不敢相信,這個男人就是多年前深夜郁香巷的色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