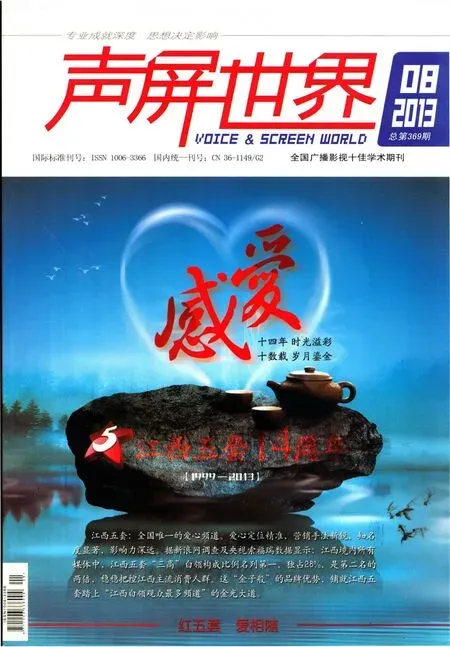從《我是歌手》看電視音樂秀節目的創新
□ 馮資榮
作為2013開年之作,湖南衛視推出了國內首檔歌手音樂對決真人秀《我是歌手》。七位明星同臺飆歌的節目形態,使電視音樂秀節目經歷“七年之癢”的沉默之后,重新點燃了PK烽火。“節目真實、選手真摯、知音聽審團真誠”,這“三味真火”激活與優化了觀眾的體驗,迸發了觀眾對節目的激情,讓《我是歌手》成為2013年春天最“火”的聲音——沒有“毒舌”、杜絕緋聞,以真聲音、真弦律為唯一宗旨。老歌新唱、返璞歸真,懷舊成了吸引眼球的“賣點”。正是這些真實的微妙元素,給《我是歌手》注入了清新宜人之風,讓節目一路飆紅,不僅創下后娛樂時代音樂秀類節目的收視奇跡,讓觀眾收獲了久違的驚喜與感動,也為電視音樂秀節目提供了一條成功的突圍之路。
機制上的獨特創新
一是賽制的創新。《我是歌手》本著公正和創新的原則,首開“知音聽審團”,從眾多的電視觀眾中嚴格篩選出500名具備一定音樂素養的觀眾,以直接投票選出的方式決定選手的排名及去留。知音聽審團確保了評判人群的多樣性與包容性,基本上覆蓋了所有電視觀眾的欣賞眼光。同時也在較大程度上尊重了普通觀眾的喜好,使觀眾能夠成為歌手“知音”參與到節目中來,由此引發“蝴蝶效應”將節目引向不可知的精彩和震撼。
與以往的音樂秀節目不同,《我是歌手》節目中的專家顧問只對競演歌手的表現作出點評,不參與評分和淘汰的流程。“知音聽審團”的設置強化了音樂秀節目的戲劇懸念與藝術張力,顛覆了一以貫之的少數評委投票決定選手去留的選秀模式,規避了江湖傳聞中的選票黑幕。評委不再居高臨下亂點鴛鴦譜,而是用耳尖投票,1000只耳朵的聆聽與辨音,使歌手與評審的關系變得更為平等,互動性更強。
二是懸念與反差的創新。懸念設置是音樂秀節目最重要的敘事元素,《我是歌手》的賽制本身就充滿了懸念與反差。節目較好地把握了觀眾的心理期待,利用和放大這種懸念與反差去提升節目效果。選手的形象、身份與聲音及其所演繹歌曲之間存在著強烈反差,這種反差讓觀眾激動不已。而現場多機位的鏡頭記錄下了歌手比賽前后的忐忑、心理落差,還記錄下了現場觀眾的反應與評委表情之間的反差。這些都被巧妙地揉進了合適的節點,反差和懸念讓節目充滿了驚喜和未知。
為了保證每一集的精彩度,節目對選手幾乎不作任何包裝修飾,這種看似無意的處理實際是節目組的“精心設計”,這些前期的設計與節目需要的反差效果相輔相成。沒有專業主持人,沒有詳細的VCR煽情,把大牌明星一個個瞞得忐忑不安。《我是歌手》將“懸念”一直貫穿節目的始終,成為吸引歌手、評審和觀眾眼球的殺手锏。懸念的設置使之形成合理的敘事結構,其敘事策略的運用恰到好處地吻合好萊塢著名編劇麥基的“鴻溝與反差”論。“宣布評委結果”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敘事符號,已是明星的歌手們在看到其他競爭對手時的不同反應、工作人員宣布歌手名次時的緊張與不安,這些都成為節目的看點。排在前幾名的歌手聽到自己名字時,臉上的表情除了喜悅,還有逃過一劫的放松。而首期暫時排名最后的陳明,雖然嘴上說沒事,但眼淚已經流了下來,讓人頗為動容。
三是以紀錄片式的全景呈現方式做音樂秀節目。以往的音樂秀節目,焦點集中在PK的舞臺,而很少將鏡頭移至舞臺以外。《我是歌手》對此進行了改革創新,設置了歌手各自的專屬休息室,并將休息室、經紀團、彩排、統計選票、宣布名次等通通攝入鏡頭,與PK臺平分秋色。決賽之時的節目直播,47個機位不間歇掃描,以紀錄片式的方式全景呈現,“大片意識”呼之欲出。休息室、彩排等人、事、場景,看似幕后花絮,實則與PK臺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為節目增加了不少橋段和看點。
內容上的求真、趨善、向美
一是節目設計層面的求真。音樂秀,就要回歸音樂層面。只有抓住音樂的本質,才能夠讓節目立起來,彌久不衰。《我是歌手》“不以名氣定選手,唯用聲音打動人”的定位,在對低俗娛樂浪花的揚棄中實現了節目設計的返璞歸真,傳遞了公平、公開、公正以及真、善、美的普世價值:只有社會公平、公開、公正,作為個體的歌手才能擁有實現夢想的機會;只有不斷有個體夢想的實現,社會才能持續健康地發展。觀眾不需要知道歌手背后的故事與經歷,完完全全靠對現場音樂的感受去投票。觀眾感受到了純音樂的力量,感受到音樂秀節目的誠意,而誠意恰恰是電視音樂秀節目贏得觀眾的法寶。
二是節目價值觀層面的趨善。參賽曲目的選擇,不管是《瀏陽河》《燭光里的媽媽》,還是《等待》《海闊天空》等,都扣人心弦。不以“貌”相,唯“聲”是舉。無論是黃貫中憑一曲《海闊天空》激活觀眾對Beyond樂隊的懷念,還是邀請齊秦、黃綺珊、周曉歐、彭佳慧等老歌手再度登臺,抑或羽泉組合重新演繹小虎隊的《愛》,老歌新唱,懷舊成了吸引眼球的“賣點”。濃情與激情、現實與懷舊交融,傳送的不僅是歌聲,更是一種向上的力量,激勵著人們對事業的執著與堅守,盡情抒發對青春、對親情、友情、愛情的美好情懷。透過音樂,觀眾看到的是厚重、豐滿、樸素、可愛的當代中國歌手的形象,以及他們對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歌聲提升了觀眾的內涵,更折射出節目的人文關懷和價值追求。
三是節目形態上的向美。《我是歌手》褪去了華麗的外衣,顯得更加質樸。以往音樂秀節目中選手常見的華麗服裝、炫目造型、激情的伴舞,通通被舍去。LED屏幕的運用、明星級伴奏樂隊的加盟,鏡頭對準的只有歌手傾情的投入和觀眾如癡如醉的神情,耳畔回響著天籟之音。節目獨具特色的品格魅力,在潛移默化地滋養著觀眾,在享受視聽愉悅的同時,感覺到精神上的陶冶,提升了觀眾的品位,滿足了公眾對于精神產品的審美需求,突顯弘揚民族情懷的文化內核。
對電視真人秀節目的三點啟示
一是國際視野與民族情懷的融合。《我是歌手》源自韓國同名節目,中國與韓國有著不同的國情特點、文化觀念與民族情結。我們的電視內容產品應當在外為中用的過程中實現本土化的推陳出新,把價值觀念與藝術審美融合其間,凸顯中華民族的特色,調和外國文化基因與中國母體文化之間的矛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是歌手》做到了這一點,找到了一個既吸引觀眾又與國情適應、與本土文化結合的獨到新賣點,在收視率與倫理性、娛樂性與社會責任之間尋求到一種文化的平衡。這就是 《我是歌手》的中國本土化過程。
二是堅守主流價值觀與創新藝術形態的結合。近年來許多電視選秀節目注重節目的娛樂性,致使主流價值觀缺失。電視工作者要提高節目的創意水平,必須要有鮮明的與時代相呼應的核心理念作支撐,不斷創新節目形態,在滿足受眾日益增長的文化藝術審美需求的同時,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社會主義的主流文化意識。《我是歌手》呈現的“真實娛樂”和“民生娛樂”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回歸主流,把最清澈、最質樸、最真誠的元素還給老百姓,注重以聲動人、以情感人。從歌手的好聲音中我們看到了當今社會最稀缺的價值觀元素——真、善、美以及愛與希望,這就是它的成功之處。
三是提高教化功能與優化文化產業經營的結合。電視媒體既要成為廣大觀眾的精神家園,又要在文化產業的激烈競爭中生存發展。因此,必須把精神文化的發展規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有機結合起來,不能唯收視率是舉。《我是歌手》把健康的文化品位與獨特的產業經營策略相結合,以提升節目質量為基礎,通過粉絲營銷、微博營銷、話題炒作等手段,提升其品牌價值及良性盈利模式。以微博為例,“快樂大本營”幾個主持人除謝娜外,都是《我是歌手》的經紀人,每個經紀人都是一個微博傳播的“中心節點”,加上知音聽審團的微博、歌手的微博、好友的微博、粉絲團的微博,借助微博這個無限大的“話筒”將《我是歌手》傳遍中國。全景式的手法把很多鏡頭給了“很給力”的職業粉絲,這些粉絲的情緒有很強的“帶入感”,感染了電視機前的每一個人,也把觀眾帶入到節目精心營造的情緒和氛圍之中,使《我是歌手》在傳遞主流文化價值、實現精神道德引導、對觀眾特別是青少年的教育、實踐、審美、娛樂等多方面發揮積極社會功能的同時,也獲得大量廣告投入。
當然,《我是歌手》也還有值得商榷之處。如主持人充當經紀人的環節可有可無。經紀人的存在與歌手的同臺PK究竟有何關聯?主持人真能代表臺長與勝出的歌手簽約嗎?經紀人與歌手一起選歌,結合上一場比賽分析對手情況,或者充當“間諜”去打探對手底細等噱頭,導致節奏的拖沓,有畫蛇添足之嫌。某些主持人并不專業的點評,暴露出主持人的無知。此外,作為版權引進的舶來品,《我是歌手》從節目形式、歌手設置以及專屬休息室等都全盤引進,未做任何修改,似乎不妥。引進節目模式既不能全盤照收,更不能削足適履,而應在“拿”來之后進行本土化的改造。韓國版的流程設置本是安排笑星充當經紀人的,而湖南版卻改為主持人充當經紀人,沒有了“笑”果,顯然不如原汁原味的韓國版。
但總體而言,《我是歌手》為音樂秀節目注入了清新之風,我們期待節目能在后續的表現中帶給中國電視更多的靈感與啟示。